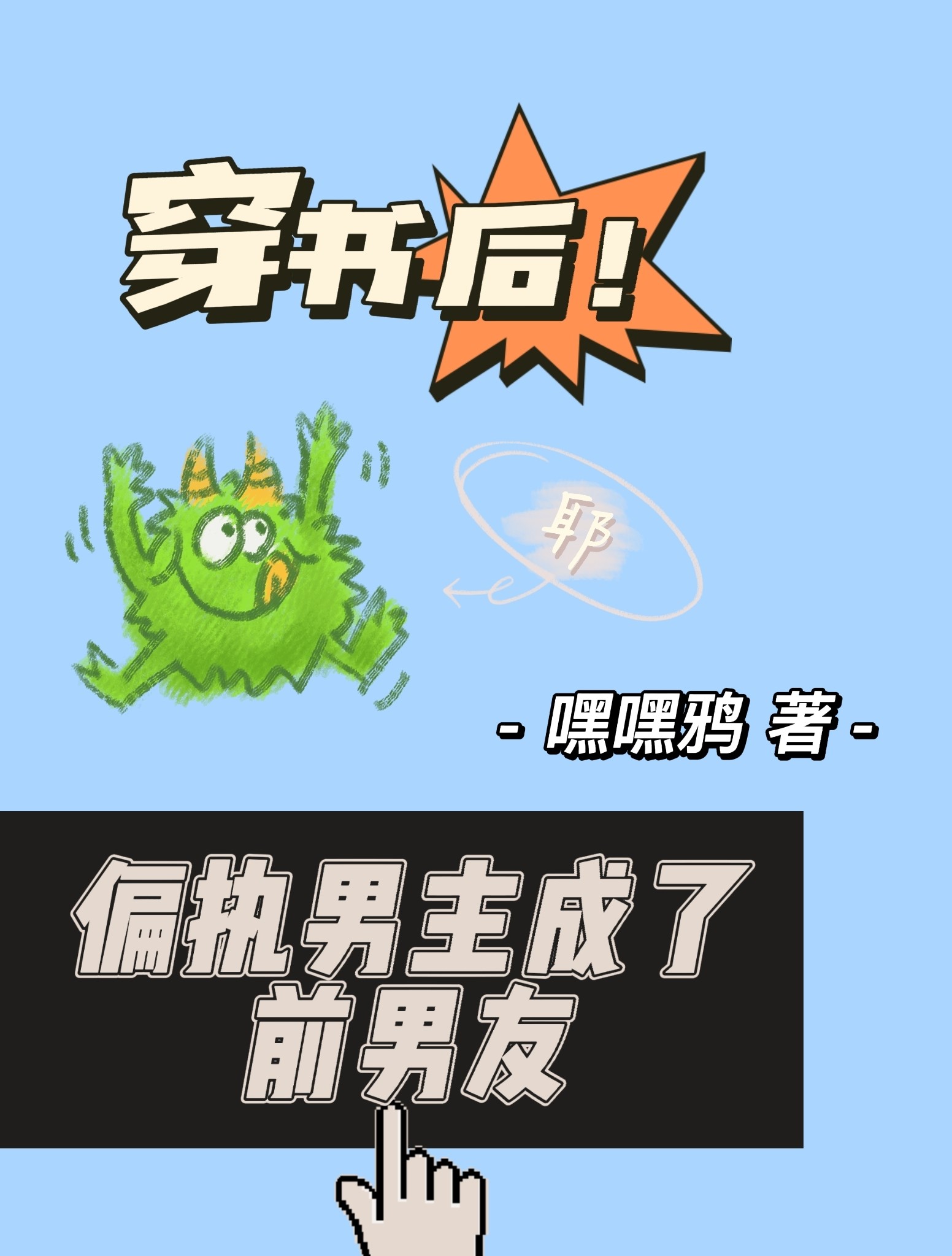令阳城东门,枯树断枝,草木含悲,一群老鸦从空中掠过,落在不远处的乱葬岗,啃食着这片褐红色的土壤。
十多年前,余国大军溃败,从东城落荒而逃,投降的五万皇家亲卫,与此处被边城军鬼屠军师坑杀。如今,腐臭冲天,尽是野畜刨食的坑窝。
官道上一麻衣夫子拎着二十多斤重的酒坛子,晃晃悠悠从城门走过这边土地,口中怨怨有词:“人真是年龄越大,愈是抠门,老子都这把年纪了,还不给我配匹劣马。”
抱怨归抱怨,可事情还要做的,老夫子抬起酒缸就是一口,黄酒溢落在地,自然洒的比喝的多。
没走几步他便有些见醉了,横倒在官道中央,呼呼大睡了起来。
没过会儿,一辕马车被二十多位轻甲家丁护卫而来,在大道上浩浩荡荡,摆出了一副无人可当的阵势。
为首的家丁见道途有醉汉阻拦,便恶语相向:“小子,速速去开!”
麻衣夫子疲倦的撑起上身,朦胧着眸子,一身酒气,眼看四下无人,便破骂道:“狗娘养的大畜生,老子都这把年纪了,称呼谁小子呢!”
家丁见是无理莽夫,便不再多言,拔剑就要冲杀。
“等等…”
马车厢内的主人,听闻这汉子声音熟络,便撩起帘子。
这不看还不要紧,好嘛,果真是曾卸甲吕万十三京的生将刀奎。
不过他不是战死在令阳之役了吗?难道是自己眼睛花了?主人揉净了眸子,瞪圆了瞳子,爹爹,真的是他!
这可是林国上将军左公权的副将,边城军资历最老的前辈,首掌两万狮鹫营的不败之神!
不过,他怎么会还活着?如今遇见,可不是一件好事。
“先生可是昔日边城军狮鹫营主帅?”
刀奎见余国华服老人起帘出驾,行礼问道。
可是等到了余国上卿,余皇太后的亲弟弟,刀奎见喜。
用酒缸支撑起身子,晃晃悠悠的抱手行礼,道:“刀奎见过上卿常大人,乖乖,您可是让我好等。”
常梦疑惑问道:“刀奎将军等我为何?”
刀奎只手伸进酒缸,舀起一捧酒,倒入唇中,回道:“我家老将军那小子,让我在此处截杀先生!”
说罢他便单手拎起酒缸,奋力扔向那拔刀出鞘的轻甲家丁,随后飞身跃起。
“借剑一用!”
酒缸顺直砸向那持剑的家丁,他来不及反应,长剑便被飞来的刀奎所夺。
啪---
酒缸破碎,刀奎的剑,已然划破了他的脖颈。
二十护卫紧拢马车,宝剑出鞘,势必保护主人。
不过在刀奎看来,无疑是排队送死。
久战而后,二十家丁暴尸与此,常梦恐慌,掏出手书:“我有贵国丞相赖桴源亲笔手书…”
刀奎并不听他废话,刀身插入常梦胸膛…
随后刀奎跳下马案,冲着死透了的为首家丁猛踹了两脚,一边踢一边破骂:“就你还敢叫老夫小子,去你二大娘的!”
刀奎反身跳上家丁的黑马,快马加鞭地驶入东城门,穿过城央,与北门外追上了左郎的车驾。
陆无为见他,弓手行礼到:“见过刀奎老将军。”
他靠拢车厢说道:“少将军,那柄余剑,仍在常梦胸膛。”
左郎起帘谢道:“叔叔辛苦了。”
而后不远,前方一怒马少年加鞭而来,近些也靠拢马车,随即调转马头,行礼道:“二十甲骑已至泽屿塞,可保将军回途无忧。”
与此同时,大地抖动,身后传来重甲马踏之音!
左郎起身出来,道:“余国上卿出京,车驾之后定有重军随护,想是看到常梦的尸首了。”
刀奎见状,随即调转马头:“我去拦杀!”
“不!”左郎看着鲜衣怒马的少年:“还没到将叔叔公之于众的时候,都匀你去。”
都匀不做犹豫,即刻拔出马背上的亢狼刀,逆袭而奔。
想来也是,千骑重甲即使刀奎神仙本领,也不可能全部斩杀,如果看清刀奎的容貌,边城军所有的辛劳都将毁于一旦。
陆无为驶快了马车,很快就入了林境。
天色渐晚,轮月当空,冷风吹的人凉飕飕地,高傲的城墙俯视着这片境外的土地,左郎起身下来,望向身后,这里,是他们征战了数年故土。
他与两人说道,满是忧感:“若那场仗,打不完,我们会不会还在此处扎营。又或者…先帝犹在…我们的旗,已经插在了余国上都…”
泽屿塞已是必关,驻守的将士观望城下有人,便高声吼道:“来者何人!”
左郎回身,冲着小将回道:“我是左郎,速开城门!”
城楼又道:“可有证实?”
左郎示意陆无为。
陆无为随即掏出怀中令牌,奋力扔上城楼:“此乃我家大人令牌!”
小将拾起满是龙纹标刻的公执司令牌,反过来一看竟是“指挥使”三字。
这正刻“公执司”,反刻“指挥使”的龙纹令牌,无疑是证实了左郎的身份。
小将知晓其真实身份后,任然故意不开城门:“小人官阶低微,不敢擅作主张,待我秉明主将后,由主将再做定夺!”
这叫什么事?自己率将打下来的城池,如今却被拒之城外。要是搁早些年,定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不久后,一甲胄将军身披紫袍站立城头,手把着左郎的令牌。
在拢总的火把的照耀下,左郎看清了他的容貌。
是二十军虎头营总兵的大儿子陈大年,他礼貌的回话:“左郎大人,家父未在关内,小侄不敢擅开城门呐!除非您有陛下圣令或者丞相手书!”
刀奎入车厢后,左郎回道:“陛下圣令后续补上!”
陈大年继续推脱道:“明日鸡鸣之时,大门自会敞开,届时,侄儿必将亲自赔罪!”
此话道完,泽屿塞城关内传出铁甲马踏之声,陈大年回首打眼一看,乌泱泱地一片,二十铁骑全系轻甲,着黑服,狼形头盔将颅面遮挡的严实,手持坚韧的狼刀,肩别强弓,马身一侧悬射箭,一侧锁铁链,他们所骑之马,皆高于普通军骑,即使有生铁面护,也能看出此马顽劣,非常人所能驾驭!
甲骑们手舞狼刀,冲向城门。好嘛,胆小的将士哪里见过如此的阵仗,腿脚松软直接就跪在了地上,即使他们只有二十人。
陈大年眸色慌张,这可是令天下诸侯帝王闻风丧胆的前军铁骑。
一只快箭射掉了城墙最高处的军旗,陈大年惊慌失措:“左郎大人莫不是要闯关!”
突然身后一脚踢开了陈大年,好一个狗吃屎的模样,他抬头一看,是陈杜康,他失措了:“爹…”
陈总兵怒斥了儿子,下令撤开了城门关卡,行欠礼,向城下喊话:“小儿不知军中规矩,还望左郎大人原谅!”
总兵陈杜康可是亲自接道了丞相赖桴源的命令,阻止左郎入关。若不是意料之外的前军铁骑,说什么他也是不会露面的。
与前军铁骑厮杀即使有十足赢的胜算,也会损伤严重,自食其果。这个道理,早在十多年前的漠北战场,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快开城门!”陈杜康怒斥道。
随后他有从儿子手中夺过公执司令牌,陈大年自然满是怨气,道:“爹,他们只有十几人,我们全城军马,怎会惧怕!”
陈杜康看着眼前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愤愤的丢下了一句话,便下城赔罪去了:“他们不是人,是一群狼!”
陈大年不服气的站起身子,夺过弓手的大弓,搭上一只利箭,瞄向城楼外的左郎:“就是狼,招惹了小爷,小爷也要嗝掉他的大牙!”
嗖---
快箭射出,锋利的尖子在月光的照耀下格外的刺眼。
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下的陆无为,见杀气腾空而来,他来不及把刀,便飞身跃起,与空中截下那只箭。
待他落地,眸子狠狠地盯着陈大年。
那似狼瞳的眸子,着实让人心中打颤。
谁能想到,这座城的守备将士,会对自己下死手。
这里可是自己兄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领土。
他也曾是站在城墙最高处,傲视天鹰的披甲将军。
若不是左郎制止…
他恨不得用这只暗箭,穿透陈大年的身体。
城门已开,陈杜康疾跑过来,看见陆无为手中的利箭,心中顿时沟壑连连,在仰头看向那不争气的大儿。
儿子惊慌失措的样子,陈杜康恨不得当时就下令,杀了他给左郎谢罪。
可虎毒还不食子呢,毕竟血肉相连,他指着儿子,怒吼命令小卒道,:“把他给我绑了!”
后再行礼致歉,已是卑躬屈膝,:“小孩子不懂事,好在没伤到大人。城门以开,请入城。”
本来他还有借口,搜查左郎的马架,若是搜出什么危害国家的东西,也好在丞相府交差,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也要给他挑出个所以然来。
可被儿子搞出这么一出,他自然是不好意思再冒犯了。
左郎入城后,二十铁骑也带来了两匹战马。
兵法大家月栗曾言:天下精湛马匹,可分其三
圈养之驹,最为普通,百姓驮畜或富人乘骑。
有魁梧之骥,可供给军士,装带甲护,上阵杀敌,运粮载辎重,是为军马。
天下飞黄扩有万千,山野之外更有神驹,驯化者其百战不死,安时依靠精料马草,战时会饮血食肉,是为战马。
陈杜康行至左郎面前,点首至歉,双掌奉上令牌道:“左郎大人慢行。”
左郎捻起令牌的吊坠,反手就扔给了陆无为,随后翻身上马,大吼道:“回京!”
陆无为依旧驾着马车,二十铁骑道开两侧,待左郎,陆无为行至最前方,合拢了队列。
快马扬鞭而去,城中就像是打雷了一般,不知情的百姓还以为是敌国军队偷袭,纷纷推开窗户察看,有些甚至开始打包家用,准备逃命。刻后却又一切犹如平常,可见其速度之疾。
陈杜康回到营帐,为儿子解开了麻绳,收回了刚才的那股子怒气,低声自语。
陈大年不解问道:“我日夜守着四个城门,就是泽屿塞钻进来一只蚊子,我都是男是女,这铁骑是从天上飞来的不成?”
“这里本就是“左”字旗打下来的,城关之中安插内线输送些人马也不奇怪。”
只是如此明显的阻挠左郎回京,会不会留下什么隐患。这些年公执司行事雷厉风行,抓了不少通敌的大官。
若是左郎使个绊子,不说污蔑,就是细查他的家底,也经不住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