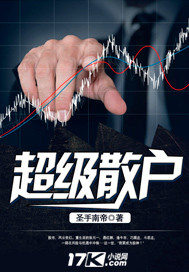耿边云继续留在娘家干农活。
耿早南除种了六亩花生,在靠近西河的洼地还种了三亩玉米,今年雨水大,都泡了。
天不停的下雨,水又排不出去,三亩玉米田里的积水有膝盖那么深。用联合收割机是不行了。瞅了个放晴的日子,父亲耿早南就说:“下水去掰玉米吧。玉米早就枯死了,有的玉米棒子在棵上就生芽芽了。耽误不得了。”
耿边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受到了争秋夺麦的紧迫性。
父亲驾驶电动三轮车拉着大塑料盆往西河那边地里去了。
耿边云随后也到了。耿边云一看,却差一点笑出来。那玉米秸就活像苇塘里的芦苇站在水里。这是啥年头啊。
父亲挽起裤腿下到水里,推着大塑料盆就进了玉米地。掰下棒子来放大盆里,满了就推回岸边,把盆里的玉米棒子穗扔岸上。
父亲说:“跟小时候下河摸鱼一样。”
耿边云挽起裤腿也要下到田里去,父亲不让,说:“你把掰上来的玉米棒子装车上,往家运。这样两不耽误。”
耿边云觉得有道理,就照着做了。近来她老是觉得身子骨怕寒,怕冷雨和凉水。她感到虚了,身体出了问题。她心里想,快点把父亲田里的农活干完,好回到城里叫孟惜桥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
耿边云不是怕死,是她舍不得离开丈夫,和那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
那一年她走失了,她是有一些意识的。她是想找回家的路,可就是找不着。越着急,就越乱走。没了方向。一会儿太阳落下去,一会儿又升上来。她几乎没了时间的概念,一心想回家,就是回不了。那种想家和亲人的撕心裂肺的痛,是没有这样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的。
自那以后,她再不想失去亲人和家。她爱他们,不愿离开他们。
有闺女在家帮忙,耿早南倒是心满意足,像个老小孩似的。仿佛又回到他年轻那会儿,他在田里干活,孩子跟在后面跟脚。除草,孩子拾草,刨红薯,孩子跟着拾红薯。多么温馨的家庭劳动的画面啊,但再也回不到从前。
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耿边云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老是觉得累,腿脚像绑了铅块似的沉重。再也不是从前跟在父亲后面不知道疲倦的小姑娘了。
免强收完了玉米棒子。耿边云觉得好像就不行了。那六亩花生收了一大半。父亲耿早南还是急着收花生。连日的阴雨,花生果都散地里了。费老工了。人得一粒一粒从湿乎乎的地里拣拾花生。很多都生芽子了。
每天耿边云就提着竹篮拿着口袋,随父亲去地里收花生。过去每到晌午都是耿边云回家来拿午饭,现在换成父亲了。
耿边云说:“爹,你用电动三轮车把收的花生拉回家,顺便给我拿口饭来吃。你老了手慢,我在地里好多收点。”
其实耿边云是累得不愿动弹。父亲走了,她就一个人坐在桃树的垄上,在小树的阴影里喘一会儿。有时候她望着县城的方向就想:惜桥啊,你啥时候来接我啊。我实在是不行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你也不来问问。
想着想着就流下眼泪来。耿边云觉得这辈子苦透了。嫁了前夫出了车祸,带着俩娃嫁给了孟惜桥,自己又因为想为他生个亲生的娃,得了精神上的病,差一点就走没了。刚说好点了,自己又觉得身体不行了。凭她的感觉,这回病得不轻。也许就此走完了人生路。
想到这悲惨的结局,她眼泪刷刷流下来,伤心欲绝。
后来父亲耿早南也看出了问题,就问耿边云:“闺女,你这是怎么了?咋这么没劲?”
耿边云强打精神,安慰父亲:“爹,我没事。在城里呆了几年,回乡下来干活没力气了。你不用担心。”
“不对,我看你的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耿早南说:“边云呢,要不叫惜桥来接你回城去看看医生。我觉得你是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没事的。我好像感冒没好利索,发低烧吧。晚上叫我娘给搓搓背出出火就好了。”耿边云坚持这么说。
耿早南就想着孟惜桥再回来,就叫他把耿边云驮走。去城里住医院。
孟惜桥由于这段时间忙鞋厂改造工程,还脱不开身了。
不是鞋厂改造工程方案已经敲定了嘛?咋还有事呢?其实在纸上画画图是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鞋厂因为是改造扩建,就涉及到占用民房拆迁等诸多事情。有一些事确实还是很棘手的。
鞋厂负责人迎春和镇上的姜海起,是整日忙着做群众工作,协调矛盾,处理问题。有些实在过不去的坎就得调整一下方案。
投资人对工程方案不断的修改调整还表示出不满。埋怨镇上领导和鞋厂没有力度。工作不利。
在这种困局下,无形中孟惜桥成了中间调解人。但是孟惜桥却很烦,不愿担当这角色。虽然祁路华很愿意他介入,并且很尊重他提出的建议。
孟惜桥却感觉,是祁路华故意借此机会接近他。设的套。
这一天上午,祁路华又来找他,说一个小问题。是厂房改建后设备安装的事。是从德国进口的全自动流水线设备,对厂房要求比较高。但是这是和鞋厂负责人迎春商议的事,不属他这个设计者管。可祁路华就是赖着找他。他好像是她手里的一把钥匙,到那里都要他去开锁。
孟惜桥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祁路华一改过去的脾气,不急不躁,就是缠住他不停的说。后来孟惜桥就被她这种韧性给征服了,没一点脾气了。就活像一拳打在棉花团上,懈完了你的气力自然你就束手就擒了。
这天上午在孟惜桥办工室里讨论完事,祁路华忽然提出要请他吃午饭,说占用的他时间太多,以此表示道歉。孟惜桥说在食堂吃就行。
她却拉拉扯扯,说:“老同学了,一起吃顿饭怕啥?”
孟惜桥怕纠缠过久,被同事看见不好,就随她出去了。
说来奇怪,祁路华不找豪华的酒店和有名的饭馆,却带着孟惜桥往老街小巷子里钻。找了一家在普通不过的老掉了牙的果子老豆腐店。
这家就两间老旧的瓦房,里屋住人,外屋坐客,父女俩就是炸油条卖老豆腐。大概干了有三十年了吧。门头依旧。
祁路华是带着孟惜桥来寻找过去的一种记忆和情怀吧。孟惜桥记得这儿,早年来喝过老豆腐。那时老爷子还年轻,闺女还未出嫁,正是豆蔻年华,长得特别漂亮。
孟惜桥就是冲着这漂亮的小妮子来的。她头发挽在脑后成一个扫把,露出半截白皙的脖颈,还有被那油锅里升腾起的热气熏红的红苹果一样的脸蛋。孟惜桥看见心就按纳不住突突跳,恨不得上去咬一口。在孟惜桥少年心里,那女孩是他一个追求的目标。
现在女孩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见了孟惜桥好像似曾相识,就热情招呼。
孟惜桥问祁路华:“咋记得这里?”
祁路华说:“来过。”
孟惜桥不敢再接下去问,怕扯远了,回到过去。
他们一人要了一碗老豆腐,要了一盘刚出锅的油条共用。埋头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