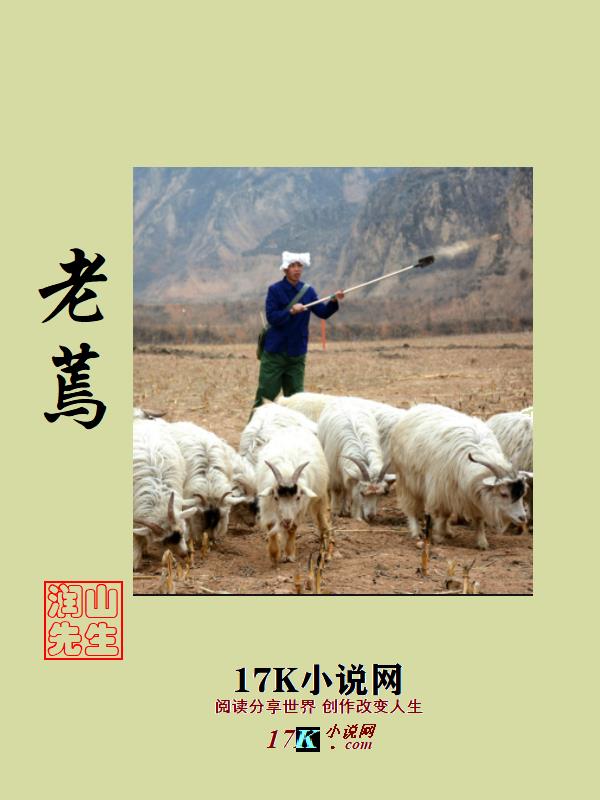我奶奶也是听别人说,从来到漠北的第一天起,那新媳妇别说洞房夜还是什么夜,白天黑夜都穿着衣服。只要张老倔动她一下,她就豁着命地嚎。第三天夜间,这个新媳妇竟趁着张老倔喝多了酒睡着之机,跑走了。等张老倔醒来一看人没了,附近村子里,连大漠边上都找不见个人影儿。张老倔就去了赤岭街里,拿着复员军人证找到相关部门,他说他怀疑这女人是个特务,他好像听到这个女人不知跟谁说了一句洋话。
于是,各级部门立刻布下天罗地网。
漠北村邻近的村子,小腾格里沙漠中的道路都撒下人去进行拉网式地搜寻。最后,在赤岭街的一家旅店里将这个女人捉拿归案。经过审查,哪里是什么特务,这女人学过英文,又信奉某洋教,只是用英语说了一句悲苦的话,大概求保佑逃出苦海的意思,恰好让张老倔听到了。张老倔在战场上听到过米国大兵说过话,所以一下子就联系上了,能说洋话的那肯定就是特务。这也着实让辽河上下紧张了一阵子,忙活了一阵子。审查清楚后,将人押送回漠北村,又送回张老倔家那土房土院中。
这张老倔气不打一处来,人跑了,还整这么大的动静,丢人现眼呐,他这兵当的窝囊啊。再一看那新媳妇,这些天不描眉,不擦粉,脸蛋儿也不那么好看了,披头散发的,灯芯绒袄浅绿裤子也都揉搓得抹布似的,皮鞋也没了亮色还碰破了皮面,看着也挺可怜人的。
张老倔的倔劲上来了,不由分说,把新媳妇拿绳子捆上吊到梁柁上,用马鞭蘸上凉水就抽起来。新媳妇一声一声地惨叫着,但问她“从不从”时,她却咬紧牙关,视死如归,就是不说一个“从”字,张老倔打累了,心也让那女人凄惨的哭叫声震碎了。他最后把马鞭子扔到院子里,上前把那女人从梁柁上卸下来解开绳子,低声说:“你走吧。”女人跪在地上给他连磕了三个头。那女人走了,张老倔不放心,又打发他的一位叔叔,交给他一沓子钱说:“你骑驴追上她,把她送到赤岭街里,把钱给她,让她寻条生路去吧!”张老倔的叔叔照着张老倔的嘱咐,把那女人送到赤岭街里,把钱交给她,打发她坐上汽车走了。
我奶奶说,她听说那个女人实际在张家口那边有头儿,本就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回去就结婚了,还给张老倔寄来了一封信和人家两个人的结婚照,并把张老倔给拿的钱,按数寄了过来。张老倔把钱揣了起来,把照片扔进灶火膛里烧了。打这以后,张老倔始终认为,这桩婚事从头到尾对他都是奇耻大辱。他,作为漠北的男子汉,不该有这样的结果,也就再没说媳妇。
这次大会战,他推着一台推车子,脚步一点儿也不比年轻人跑得慢,装的土也一点儿不比年轻人装得少。从上面来的记者到工地采访,问张老倔:“大叔,您老人家大会战这么出力干,是什么精神什么思想受到什么鼓舞这么干的?”张老倔抹一把脸上的汗水,“嘿嘿”一笑说:“我就这么个实在人,当兵这么干,当庄稼人也这么干,当年种大烟那工夫也这么干,给扛活也这么干,现在还这么干。这孩子,一个干活还问啥精神啥思想的,难道你爹你妈不这么干?”一顿话把个记者闹得脸红脖子粗的,把本来调好镜头的照相机一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小年轻的上来闹劲儿,没正形地撒欢尥蹶子地干活儿。正干得兴头儿上,有个外号叫“六股镩子”的小青年把棉裤的裤裆挣开了,冷风直往裤裆里边钻。大家都知道孙大裤裆一出门总带针线,以防随时裤裆出了问题好缝一缝。这六股镩子就说:“老五哥把你针线借我用一下,赶明儿还你。”漠北人编席子,用的是芦苇篾子。把芦苇破成篾子时,用一种工具叫镩子,有四股的、五股的、六股的。六股的是极细的那种,常常把心细或小心眼的人叫做“六股镩子”。六股镩子眼瞅着把自己的裤裆要缝上了,结果一使劲把针鼻儿拽豁了。夜里,人们都躺在老乡家的炕上裹上被子准备睡觉,那工夫漠北地区没有电,点着煤油灯照亮,人一睡下也就把灯熄了。六股镩子摸着黑把针给孙大裤裆递了过去,说:“老五哥,我使完了,把针线还给你。”孙大裤裆从被窝里伸出只胳膊把针接过去。没一会儿,孙大裤裆就叫了起来,“六股镩子,你咋还给我个没眯儿的针?”六股镩子说:“没有啊,五哥,我还能赖上你?”孙大裤裆不依不饶,起身穿上衣服,拽着六股镩子就去找赵大嚷嚷。赵大嚷嚷原本好兴致,让这两人一闹,气也就来了。“他妈的,你们这整的啥事儿。咱漠北大队人的脸都让你们给丢了。一包针才一角钱,你们穷死了?睡不着,你们俩给我挖土去,一人二十车!”两个人噘着嘴去推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