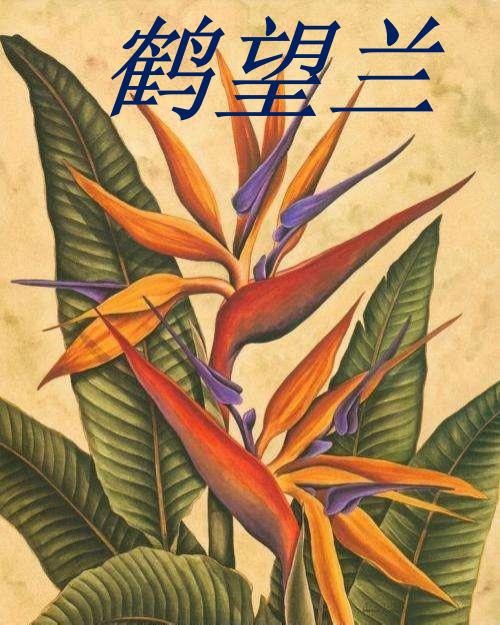2021年的陈七月一直把头靠在玻璃上,传来了一丝生硬的酸痛。这才让她从回忆——还有后来蒋士颖对她说起的过去中抽离出来。
叶九思躺在病床上,被医生推了出来。医生对着走廊喊道:“谁是叶九思的家属?!”
陈七月和叶父叶母神色凝重地抬起头,匆忙地回应着医生。医生对他们说:“现在病人暂时抢救过来,但是情况仍然十分危险,要转入ICU病房观察。请各位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叶母听完,两眼昏花,双腿失去力气。叶先生和陈七月连忙搀扶着叶夫人,坐在抢救室旁边的椅子上。陈七月掏出手机,正准备给蒋士颖打电话,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她手机的来电显示中。
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些焦灼:“七月,我刚刚才看到新闻,说九思昏了过去,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陈七月说,“你现在那边能走开吗?我建议你还是快点赶过来。”
蒋士颖也没多问,挂了电话。
他们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之前他们还能佯装冷静,但这一次叶夫人听到陈七月说的话之后,心理防线猛然被击溃,她仰起头,像个孩子一样哇哇大哭起来。哭腔模糊了她想说的话,大意是自己做母亲为什么这么失败,居然让女儿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我们从小也没亏待她啊!她想要什么,我们都给她;她想做什么,我们用尽全力支持她。我们只是想让她简单快乐地生活着,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叶夫人的声声哀嚎,犹如潜入海中的血迹,吸引了潜伏在周围犹如鲨鱼般的记者们的注意。头条新闻的血腥味,让这些记者不再忌惮医院里的规矩。他们马上举着长枪短炮,对着他们三个就是狂轰滥炸。
他们高清的相机里,已经存下了叶夫人花白的头发凌乱的蓬起、极度张大的嘴挤得她的皱纹更纵横沟壑、眼珠子也被眼皮给掩盖住,导致泪水决堤而下的样子。在镜头下,她已经褪去了由金钱编织而成的文明和从容,只剩下原始动物失去孩子后的哀嚎。这野兽一般的面容,截成特写,放在新闻APP头版头条,放在微信推送第一条。从喜马拉雅山顶到马里亚纳海沟一般的落差,一定能转换成一篇篇“10w ”的爆款。
陈七月很清楚,叶夫人所悲恸的对象,和自己这二十年的经历息息相关。她这些年鲜活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据,然后是一场狂欢。一想到这个,陈七月的胸口也堵得紧,她连忙扶起叶夫人,匆匆带她离开现场。
医院的保安操着硬硅胶棍棒,吹着口哨,往这群记者冲过去。棍棒一根根地往下敲打,有好些镜头玻璃都被敲出了裂缝。
这些记者才散去。
医院这才回归到原有的肃静。
在医院门外的小轿车已经停好,司机搀扶着叶夫人就坐之后,她和丈夫先行离开医院。陈七月转身,带着风又往医院里走回去。这时她的眼角才划过一道泪痕。嘴角也未曾抽动过一丝一毫。她也没抬手去抹眼泪。
蒋士颖打了出租车赶来了医院,在大堂和陈七月汇合。他们没多说什么,马上上楼走进ICU病房里。
整个病房灯光灰暗,呈现一片灰蓝色。呼吸监测器缓缓地发出“嘟——嘟——”的声音,叶九思的脸上盖上了氧气罩,手背插着针,正在输液。
陈七月握住了叶九思没有插上针管的另一边手——这二十年的悲欢离合,全化在了她的掌心手背上。真的比二十年前她第一次握住叶九思的手掌时的手感,要纤薄很多,也粗糙很多。
叶九思睁开了眼睛。眼皮撑开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珠就开始转,直到聚焦在陈七月的脸上,然后久久地凝望着。叶九思是个作家,她有千言万语想对陈七月说,想对蒋士颖说。但是她还是太虚弱,根本没力气动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把玩了二三十年的文字,其实到生死攸关的节点,她想说的话用一个眼神就能和盘托出了。
“九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陈七月俯下身,抬起手,把掌心放在叶九思的头顶上,轻轻地摸了一阵。
恰逢护士来查房,她简单检查了一下叶九思的情况后,用眼神示意陈七月和蒋士颖。陈七月先是看了看手机的锁屏,发现已经快到下午五点了。她对叶九思说:“九思,我要去接孩子放学了。你好好休息,别担心她们。士颖今晚陪着你。”
然后她转身匆匆走出病房。这时护士对她说:“目前病人的情况暂时稳定,但是不排除会有恶化的可能。如果情况危急,还是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陈七月沉重地点头。护士继续说:“我们和她的医生一定会尽全力保住她的生命的。”
“护士小姐,谢谢你。”陈七月说完之后,回头凝望一眼躺在病床上的叶九思,然后匆匆离开。
这次她再也控制不住想要抽搐的嘴唇。眼泪一颗颗地滑落下来。她一边往医院外走,一边拿起手机打开叫车软件。等她走到大门口时,预约好的车已经停好等她了。
她的目的地填的是东山培正小学。
——对面就是她和叶九思认识的学校广州市第七中学。刚上车的时候,汽车音响一直播放着节奏密集而乐器嘈杂的电子音乐。那急促的鼓点一直急促地敲打着陈七月的额头。她先是插上耳机,播放点舒缓音乐。
然后她的音乐被音响的声音给吞噬掉。她只好有些虚弱无力地说:“师傅,麻烦你关一下音响吧。”
车厢内只剩下换气口的呼呼声。进入了学校附近的地方之后,车道变窄,里面挤满了一辆辆缓缓前行的汽车。喇叭声、人类的嘈杂声、尾气的味道……一切都被隔绝在金属和玻璃构造的罩子之外,让她对这个世界的感触少了几分真实。
她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东山口——那时候柏油马路上鲜少有车,大家的代步工具基本都是自行车。学校门前的马路是一条下坡路,一个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少女双手握着车把手,双脚站在脚踏板上往下俯冲——扑面而来的欢笑声和他们扬起的风,给了他们深切的生活真实感——他们确实是活在这个地球上。
但陈七月印象里,叶九思很晚很晚才真切地明白自己说的“生活真实感”是什么。她曾经渴求叶九思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但现在她宁愿叶九思一直活在那人类精心构造的金属保护罩里,或许她如今就不用躺在医院冰冷的金属器械之下。
陈七月下车之后,在小学门口张望一阵,看见自己的两个女儿走出来之后,大幅度地向她们招手。
读五年级的大女儿陈知衡看见大妈妈招手之后,拉着刚上一年级的妹妹叶明斐走出去。陈知衡已经接近青春期了,自诩小大人,不愿意跟妈妈太过亲密。陈七月也很明白这点,所以她只牵着叶明斐的手,和大女儿并肩走到少人一点的街角。
“今天妈妈的车停在了法院,没开回来,所以我们得打车回家。”陈七月又打开手机的网约车软件。
“小妈妈今天怎么没有来呀?”叶明斐用手指前端捏住陈七月的衣袖,轻轻摇了一下,一双汪汪大眼仰望着陈七月,奶声奶气地问道。
“她的案子还顺利吗?”陈知衡听见妹妹问起小妈妈叶九思,也跟着问。
“法官说案子还要择日再开庭。因为小妈妈现在在医院。”
叶明斐叫了起来,惶恐地问道:“小妈妈她没事吧?”
陈七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强忍着内心的酸楚,倒也不想把自己的情绪传染到女儿们的心中:“小妈妈现在暂时没事。”
叶明斐嘟着嘴,垂下头。她胸前的红领巾更衬托得她的低沉和担忧。陈知衡走到叶明斐身后,把双手放在叶明斐的肩膀上,又轻抚她的头,让她安心一些。叶明斐对陈七月说:“妈妈,我今晚想去医院看看小妈妈!”
“小妈妈在睡觉呢!”陈七月说,“小妈妈托梦告诉我,叫我让你在家里乖乖地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记得看她给你准备的《红楼梦》绘本。听话啊!”
这里的交通状况确实不好,网约车还没到。陈知衡已经开始焦躁了,她干脆翻出书包,从里面拿出英语课本,低着头默默地背单词,想着跑赢遗忘曲线,夯实今天在学校学的内容,预习好明天去补习班要学的内容。
但其实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效率并不高——陈知衡还是盖不住心里泛起的酸楚。在听说了叶九思案件不顺利、她还进了医院等事情之后,最让她揪心的竟然是看不见妹妹肉嘟嘟的脸上的笑。其次还有一些新萌生的愧疚感——一直以来,妈妈的这位伴侣的喜怒哀乐就如阿拉斯加的鲸跃起又落下之后在海面上激起的浪花一样,高耸又猛烈。但她的心却垂钓于东南沿海的沙滩上,对万里之外的浪花无所感触。其实妈妈和小妈妈都没做错什么,但是她始终没办法像妹妹一样如此共情于小妈妈。
可能是几年前的事情,给她幼小却已经建立起基本世界观的内心以剧烈的冲击。
彼时是深秋之际,天空又不明朗,所以在这个钟数天色已经暗沉了下来。陈七月发现陈知衡在这样光线底下看书,于是制止了她,说:“别现在看书!会弄伤眼睛的。”
“车怎么这么久还不到?再等下去我就不够时间复习了……”陈知衡冠冕堂皇地搬出了叫“学习”的闪光灿灿的免死金牌。
陈七月愣了一下,隐约之中看见了学生时期的自己,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自己的影子居然这么完美无缺地投射到陈知衡身上,不愧是血肉相承的亲女儿。但是她当年拼尽全力,读书读得头破血流的,生活似乎也没什么质的飞跃。可是女儿的眼神里却充满了对未来最纯洁的憧憬,她不忍心打破。
好不容易她们预约的车停在了他们面前。
陈七月坐在了前排,还在系安全带的时候,放在大腿上的手机不断地在震动。她手忙脚乱地系好安全带之后,拿起手机,一看来电显示,下意识地头皮开始发麻,一直延展到她的脖颈、后背直至胸口。
她不想接这通电话,但是有人想见他,所以她不能挂电话。可是今天发生太多事情了,她实在是疲于应付这个早就不应该再出现在她生命里的人。
她把手机塞进手提包里,当作没听见这通电话。心思细腻的陈知衡发现了什么,于是把头往副驾驶位探过去,问道:“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吗?”
还没等陈七月想到该怎么搭话,叶明斐先尖叫起来:“姐姐!我们没有爸爸!”
陈知衡用力拧了一下叶明斐的胳膊,说:“你清醒一点!他也是你爸爸!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你怎么可以不承认他?”
陈七月转头对着后面两个女孩子喝道:“司机叔叔在开车呢!都给我安静点!”
这时候,两姐妹才安静下来,但是她们还是大眼瞪小眼地、用力睁大眼睛地盯着对方。陈七月透过驾驶位和副驾驶位的后视镜看到两个女儿的眼神战斗,只觉得烦躁得头发都要炸起来了,变得分叉、毛糙。
只有她一个人开着马力不足的破冰船,在偌大的南极洲打破名为“嫌隙”的冰川。一片茫茫,她埋没在一大片一大片的白色反光里,没有了任何颜色。可能全部冰川化作水,她才能修正以前走错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