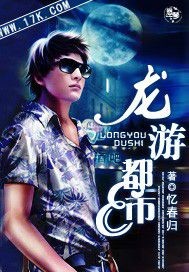又是那种莫名其妙却如影随形的熟悉感。
头像是被人用针扎过一般,不,是正在扎,疼得“我”几乎打滚,大脑越来越混乱。
雨夜……窗户……树影……
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凶神恶煞的男人的脸……苦苦哀求的小女孩……
“吴玥?”
突然听见有人叫自己的本名,习惯了在梦里被人叫作“三妮”的我有些反应迟钝地应了声,然后便感觉额头上被人敷了块什么,凉凉的,还有点舒服。
想要睁眼,却觉得眼皮似有千斤重,想问“我这是怎么了?”才发现喉咙连吞咽口水都困难。
“别动。”有人说。
我不确定那声音是不是在跟我说话,因为听着挺陌生的,不像是我认识的人,又急于知道自己怎么了,我于是并不理她。
可眼皮上像是附了一层什么东西似的,眼睛怎么都睁不开,还稍微用点力就痛。我于是下意识地伸手想去摸,却被人一把抓住了手腕。
仔细感觉,抓我的那人的手似乎还带着手套,或者和手套类似的东西。
什么病需要这样?我心说,于是甚至还没来得及想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怎么得的就在心里给自己写好了遗书。
又心说你死就死,就别嚯嚯人家医务人员了,可又说不了话,于是便一双手到处挥,想找到她的位置把她推出去……
然后,我就被注射了一支镇静剂。
事后才知道我应该是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诱发了荨麻疹,极有可能是被蚊虫叮咬了,而且这种病找不到诱因就无法根治,即使根治了也极有可能复发,不出意外的话会跟我一辈子。
我就……
日常思念小哥中……
总而言之,那件事之后我在驻地里算是出名了,连王教授都知道了我。。。
老实说作为一个有痔,啊不是,有志青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也曾幻想过自己的名字被行业内的大佬熟知……可是,为什么会是以这种方式啊哥哥?
那个小护士后来也跟我们玩得挺好的,当然,特别是我。
说起给我打镇静剂的事儿的时候她总笑:“你都不知道你那时候有多吓人,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皮,连脸都成猪头了,两只手还张牙舞爪的,动作明显就是在针对我。”
“而且,”她说:“谁知道你那时候得的是什么,虽说有可能是荨麻疹,但有的荨麻疹也是会传染的好吧!我那时候还以为你是不想活了,想把我防护服扒了让我陪你一起死呢!”
我就???
心说我是那样的人吗?
不过那场荨麻疹确实来得诡异。
蚊虫叮咬?那天晚上我们帐篷不是烘了灵香草吗?
又,被咬了的话我应该会有感觉的吧,可那天晚上我睡得很熟,虽然做了噩梦。
且一夜之间遍布全身,到睁不开眼,说不了话的程度,一夜之间又突然毫无征兆地好了。
虽说荨麻疹的发病期普遍是二到八个钟,二十四小时内会自行消退,但这程度也太严重了些。
于是当天,我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与挖掘,甚至住宿条件都好了很多——由原来的大通铺换到了现如今的连王教授这样的级别都还没资格住的小单间。
王教授:我不羡慕谢谢,这待遇我并不想要。
早午餐都没吃,对,因为我他娘的被人打了镇静剂。
结果晚上吃的还是据说是早上煮的粥,我于是一赌气不吃了,睡觉!
专家说的,新鲜饭菜超过六个钟就属于是剩菜了,不能吃,我还是个病号啊!
她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然而因为一支镇静剂,我几乎睡了一整个白天。所以,原本一直自诩睡眠质量极佳的我今天破天荒地,失眠了。
可因为不能说话,不能动,甚至连眼睛都睁不了,我此时唯一的消遣也就只剩下思考人生了。
于是,莫名其妙地,我想起了我最近的这两个梦。
第一个梦我在悬崖下面被雨淋,第二个梦……
诶!我灵光一现,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两个梦之间会不会是有联系的?
第一个梦我在悬崖下淋雨,第二个梦里的“我”失忆了,而且貌似这忆失得还有隐情,会不会……
可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平时吃了睡睡了吃,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看小说,也并不联想,更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幻想,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呢?
再次因为得不到答案而烦躁的我又一次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反客为主的机会拱手让了出去。
不知不觉进入了睡眠,不出所料的,我又陷入了一个梦境。
梦里,尸山血海,遍地残骸。
这次的主人公叫秦紫,和大家一样,也是一个时刻可能成为残骸中的一部分的人。
提着仅存的一口气,她们一行人在往前走。
后面,代表不详的乌鸦和秃鹫紧跟着,似乎在为饱餐一顿做准备。
我无法得知这是哪个年代,在什么地方,更奇怪的是,对于秦紫这个人我居然没有任何的归属感。
就,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在昨天的噩梦里,对于“三妮”这个名字我是有归属感的,虽然现实里我并不认识她。
可在梦里,没有理由的,我就觉得我是她。
所以,我可以完全带入她的视角,想她所想,看她所看,还能跟她产生共鸣,因而这个梦做的更像是在回忆。
但今天对于秦紫这个名字我却是完全陌生的,也没法代入,于是这梦做的就更像是借她的眼睛看了一场3D电影。
电影的开头就是这样一副万物凋零,毫无生机的悲凉画面。
紧接着镜头一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万物复苏,一个个红瓦黄墙的院子已经建起来了;屋檐下挂着的是旧年的苞米,大蒜,辣椒和新腌的腊肉……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镇上,酒楼林立,而且进出的人络绎不绝,看样子似乎生意还不错;小商小贩们也都争相向路人推荐着自己的东西,街道上,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
快到饭点了,几家一向吃饭比较早的人家的烟囱里已经升起了炊烟,胡同里还有正在打闹的小孩子……
说到小孩子,包子铺门口,一个看着已经有四五岁了的小女孩正在吃包子,而且是一手一个的那种吃。
小女孩旁边,一个挺着个大肚子,手里还拿着三串糖葫芦的妇女脸上带着笑,眼睛都快长到那个小女孩身上了——看样子应该是那个小女孩的母亲或者家里的长辈。
“娘!”隔壁的巷子突然又跑出来一男一女两个岁数看着似乎相差不大的孩子,两人在巷口站定,叫了声“娘”后便奔向了那个手里拿着糖葫芦的妇女。
“你们慢点跑,别摔了!”妇女和落在小孩身后,手里拿着个小包裹的男人齐声开口道,说完两人也觉得好笑,于是相视一笑。
这时两个孩子已经都到了妇女跟前。妇女貌似怀了孕,肚子已经很大了,因而只是微微弯腰虚搂住了他们。
微笑着听着两个孩子争先恐后地跟自己说着他们刚刚的见闻和战利品,抬头又看见自己的丈夫正带着阳光慢慢走向自己,徐柳氏,也就是那个妇女突然觉得生活美好的像是在做梦。
她何出此言呢?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镜头?如果你记得,又恰好眼力还算不错的话你就会发现:
这几个人就是第一个镜头里和秃鹫赛跑的那群人里的其中几个。
而那个一手一个包子的小女孩,她叫秦紫,当然那时候的她还叫“二丫”。
镜头又开始转动。
这是一张告示,衙门贴出来的。
秦紫好像是不认字的,我对于古文也无能为力……可是,从围观人群的只言片语里,我和秦紫都轻而易举的拼凑出了一个真相:
又要打仗了。
不过那时候的秦紫还不知道又要打仗了意味着什么。
她虽然生在战乱,但当年逃亡的时候她尚不记事。因而,只是越来越觉得家里的气氛和人都很诡异而已,对其他的倒没感觉。
特别是徐柳氏,也就是自己的娘亲——事实上秦紫并不姓秦。
之前就有说过,她那时候还叫“二丫”,具体名字忘了,改名是很后来的事儿了。
她爸姓徐,打的一手的好首饰。
可自从那据说象征着“又要打仗了”的告示贴出来以后她爸就不出去了,天天躲在家里,时不时地就叹气,而且格外关注外面的动静。
徐柳氏也是,总是时不时地就抱着秦紫哭。
徐帆和徐佳,也就是秦紫的哥哥姐姐也被徐柳氏拘在了家里……
就在这样压抑,或者说愁云惨淡的氛围下又过了几天:那天半夜,秦紫家突然来了几个不知道是捕快还是官兵的人,事实上这对那个时候的秦紫来说没分别。
总而言之,她的爹爹没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徐柳氏告诉秦紫说她的爹爹是去当大英雄去了,但秦紫知道不是:因为,她发现那天走的人不止她爹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