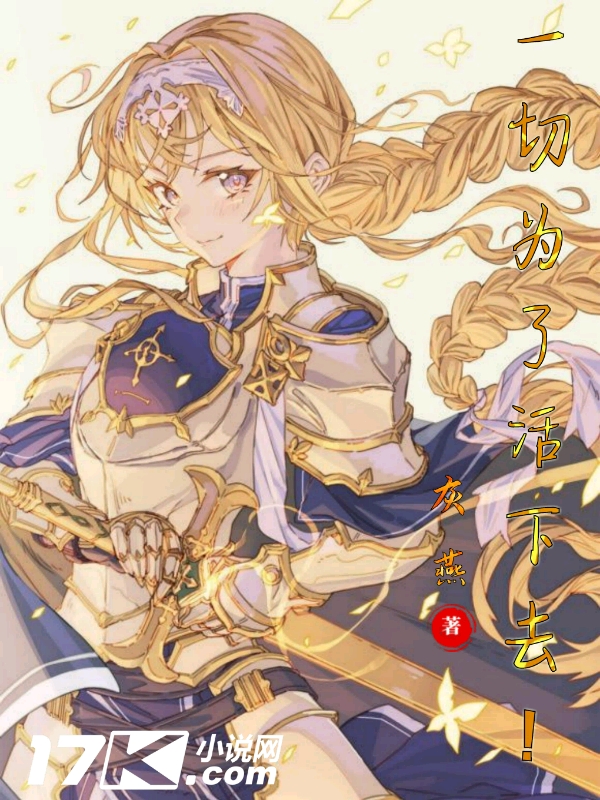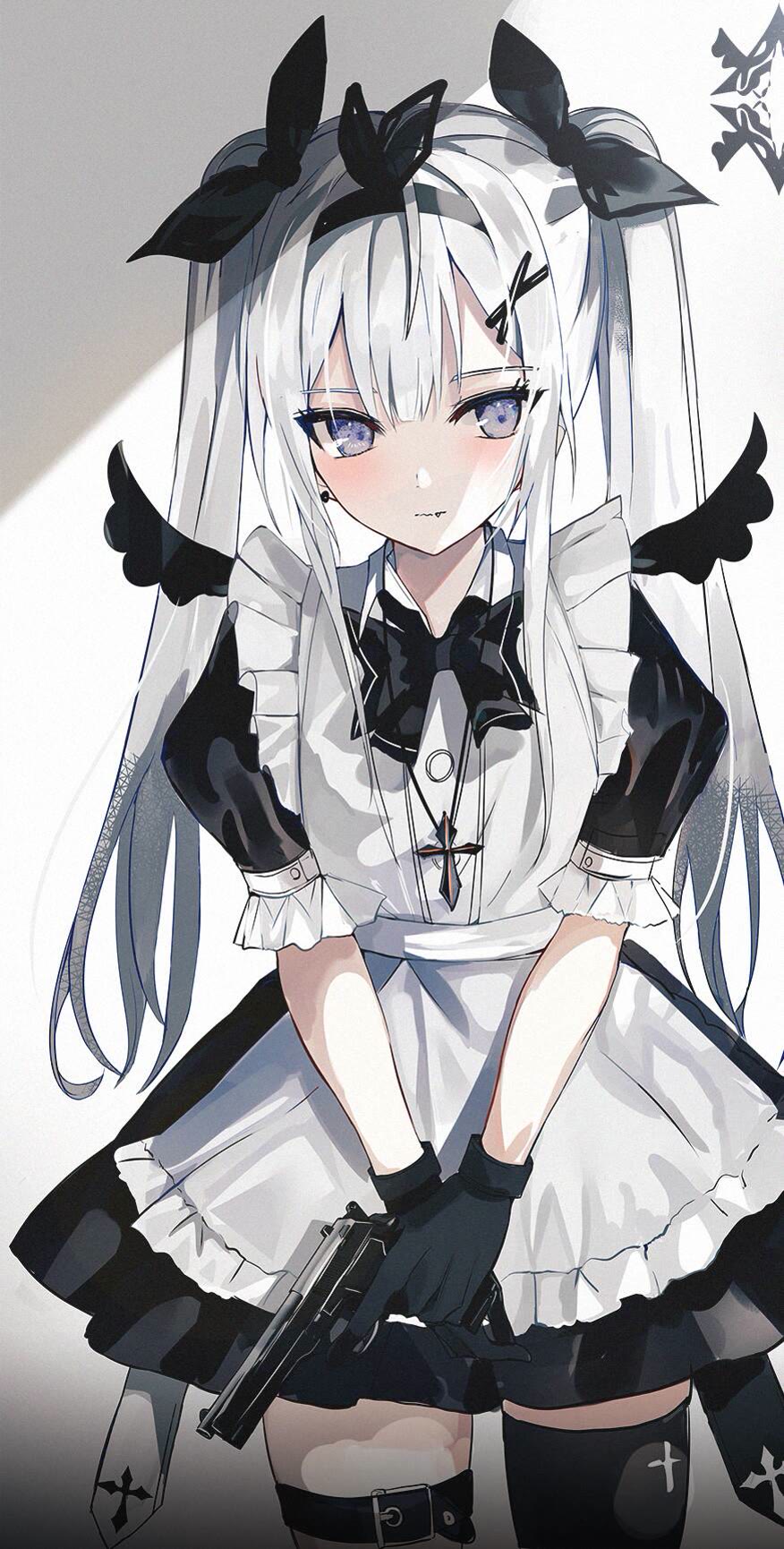二十多年前,醉芬芳的掌管者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女人,镇上的居民称之为“花濛第一美人”,听说就连现如今那花满楼的花魁的绝世容颜都不及她半分。她自己倒也是喜欢这的外号,于是在及笄时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其他的名字,唤作花娘。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只知道她孤身一人凭空出现在了花濛镇。她凭借着出色的能力与过人的智慧很快就获得了众人的赏识,后来她没有再在其他院子里挣钱。于是她就开办了醉芬芳,并成为了成为了第一任掌家。
很快,不想而知,她一个人久了,被别人催嫁了。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可她一个也瞧不上。媒婆上门来强说理,让她还是趁还年轻嫁了,免得孤独终身。花娘却不以为然,她反问道:“此话不妥,本姑娘一人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醉芬芳生意做大了,根基尚且不稳,就让我嫁人。倘若我嫁了个浑球,那我岂不是一面照顾他,还要一面照顾生意。可不要累死我了!”花娘没好脸色地说着,直接漠视媒婆。媒婆顿时傻了眼,自己那么说媒多年,第一次竟被一个老姑娘这么无视。到也不怨她,那往日的姻缘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就算姑娘有再多的不如愿,也得嫁!可面前这人不同,似乎她的红线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别人压根就管不了!可既收了人家的钱财,就得替人办事!
“姑娘,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可是老身亲自给你挑选的,必然是如意郎君啊!”媒婆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和气地说道。花娘笑了笑,说什么如意郎君,不过是财大气粗的人罢了。“本姑娘非嫁不可吗?或者说是非他不可吗?”花娘挑眉直视着媒婆,媒婆下意识回避她那犹如银针的目光,讨好地说着:“姑娘若是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不过那钱家的公子也是玉树临风,你们若是能成一对儿,那必然是不愁吃喝,佳偶天成了。”花娘早就见过了那个钱首名,他早已有了家事,他的发妻陈香贤惠温顺,可就是四年还未诞下一子。这钱家也遭受了不少的流言蜚语,此次前来,想必也是这个缘故了。
“我虽不懂什么诗才,但也是清楚比翼鸟的,还有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倘若那人真的疼爱我,那还娶别的女子作甚呢!见一个爱一个的,我可不想嫁,免得成为下一个!”花娘话语刚落,媒婆瞪大了双眼,显然是被气得不轻。“说得好,说得妙啊!”花娘四处望去,却不见那带着笑意的声音从何而来。过了片刻,只见一位身着深灰长袍的男子从自己身后悠闲走来。那人英隽玉貌,身姿挺拔,眉宇之间流露的是难掩的锋芒。“依我之见,今日这姑娘是不予致同的,你还是先回去吧!”此人开口说着。媒婆也懒得争论了,那钱不要也罢!
看着那媒婆逐渐走远的身影,花娘会心一笑,但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男子,有些疑惑:“这位公子...你是?”那人面带微笑地说了句:“在下刘远道。”花娘心想,这名字怎么没听过,姓刘。这整个花濛镇就只有两处刘姓人家,看这人手足举止之间都透露出斯文二字,听闻镇西那处有位秀才,准备进京赶考,莫非就是他了!这人应是极少出门,所以才没怎么见过。
“原来是刘公子,听闻刘公子极少出门,此次前来,想必不是来看戏的吧!”花娘这几日被那些提亲的人弄得头昏眼花的,一说不允,就翻脸不认人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讲理的,心里可兴奋坏了,可身为女子,还是要矜持一些。
“在下,若是说自己是来买酒喝的,姑娘那么聪慧,怕是不信了。开门见山地说,在下是来提亲的。但此事非在下意愿,家中所迫。鄙人家中清贫,故姑娘无意,在下也定当不会强求。”刘远道原以为对方是个寻常女子,可听闻她的所作所为以及方才的话术,断定是为奇女子了。
花娘心想,这整日催催催的,何时是个头?比起那些不讲理的,她更钟意于眼前这个秀才。倘若非要嫁,那就他了。她一直打量着这人,高傲地说道:“也不是不可,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先发誓,然后再谈婚论嫁。”刘远道一惊,原以为自己就是来打酱油的,没想到真的要谈婚论嫁了。但既然人家说了,那自己就当负起责任来:“鄙人刘远道今日对天起誓,来日定娶花娘为妻,不负所望!天地为证,山河为鉴!若违背誓言,众叛亲离,形神俱灭!”不知往后如何,只道是今时今日,一对佳人成双对。一旁梨树的清香环绕着他们二人,见证着他们意料不到的情爱。
......
与此同时,钱家来了位媒婆,她急着想将那钱财还回去,那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再也不想碰了!钱首名刚从外地经商回来,不料撞见了这场景。他本想勃然大怒,呵斥父母的丢人行为,但一听到是陈香的意愿,不免心中有愧。他忽的想起大婚那日自己说好了要给她荣华富贵,可也不知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四年未有一男半女的。这让她受尽了委屈,而他自己也多次遭下人非议。
房间里,一位妇人听闻事情失败后,垂眉叹气,无力地坐在梳妆台上。窗边吹进了些许桃花的碎瓣儿,落在了镜前的木梳上,散发着沁人心扉的芬芳。
“香儿,香儿,你告诉我,到底是哪个王八秃子的?说了你的坏话!”陈香见他回来高兴地立即走到他身边,摇了摇头,轻声说道:“夫君,莫怪他人。”陈香深情地对他笑了笑,可却掩饰不了眼底的哀伤。“四年了,或许...我就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钱首名只觉得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出的滋味。但他不会放弃的,爱或不爱都是一辈子的事,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一把将陈香拥入怀中,紧紧地抱着,怜惜地将下颚抵在她的头上,柔情蜜意道:“香儿,不要在意他们怎么说!别脏了你的耳。我曾发过誓,此生只许你一人白头偕老。不管那人长得沉鱼落雁也好,倾国倾城也罢,我都不会娶的。此生有你,一生足矣!”陈香听到此话,心中也有了定数,依偎在他宽阔的胸怀里。可一想到,自己有一天人老珠黄、面若枯叶,那是不是就改变了心意,她不安地问道:“都说母凭子贵,可再过个二三十年的,还未有子嗣!我也人老珠黄了,到那时,夫君还会带我如初吗?”钱首名听后笑道:“香儿会人老珠黄,那我难不成...永葆青春?”他还是沉默了一会儿,开口低语道:“孩子的事,我此后每月都陪你去山庙那祈福求子,我不会抛下你不管的。”钱首名牵起陈香的手,发觉她的手还是那样异常的冰冷,可他现在只想给她一些温暖。
花娘和刘远道大婚后,花娘依旧管理着醉芬芳,有时,刘远道的二弟刘申和其妻子喜娘会帮忙一同打理。而刘远道继续勤读诗书,报考功名。此后一年之内,钱首名每月都陪同陈香前往山庙祈福,并且,他对待下人以及干活的农民都极为友善。
“后来呢?”吴铭见阿雪停了一会儿没说话,便好奇地问了句。
“后来,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阿雪有些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
三年后,花娘在春日里诞下了一名女婴。本该高兴地事,可刘远道却是力不从心地笑了笑。他这次进城赶考,又战败而归。他志在仕途官场,也许以后会极少归家。刘远道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只想到了一个“离”字,于是就想着将其取名为“刘离”。可花娘不乐意,嫌那名字晦气,又想到自己最爱的梨花,就将她取名为“刘梨”。
花娘知道他志在仕途,也支持他,从没怎么埋怨过。同年十一月,花娘忽然听见门外有敲门声,便开门一看,发现没有人。但正准备关门时,却看到了地上有个婴儿装在了一个竹篮里。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真是可怜。花娘与刘远道商议后,就将其领养了。由于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捡到的,就将她取名为“刘雪”。
......
那年钱首名可高兴坏了,因为陈香怀了身孕。整个院子里都洋溢着喜气,每一个人都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大夫说陈香天生体寒,怀孕生子怕会危及性命,所以钱首名那年极少外出做生意,几乎整日都陪着陈香。而陈香也不怎么走动了,在家里安心养胎。她还给自己的孩子绣了不少的小衣物,想着等孩子出生后,给它穿上。那时的钱首名深陷极致的喜悦中,也没怎么预料到后来的结局。那晚他焦急地等待着,大步流星地在屋外走着,已经过了一个时辰了,怎么还没好呢?“列祖列宗保佑,千万不要有事!”他双手作揖,紧闭双目,双手作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滑落,手心里也因高度紧张而冒出来手汗。
“咿呀~哇~”婴儿的哭啼声打破了他的祷告,他笑逐颜开,一溜烟地跑了进去。他看见床上的陈香大汗淋漓的样子和奶娘递过来的哭哭啼啼的孩子,大喜过望,原本以为可能其中一个会出事,没想到母女平安。陈香欣慰地朝着他笑了笑,可她霎时觉得下腹一阵又一阵的剧痛,腿间也再次流出了大量血块。没想到,还是来了。她顿时肝肠寸断,欲哭无泪。她拧紧了眉心,强迫自己伸出颤抖着手,要看一眼,最后一眼。在逗孩子笑的钱首名下意识看了眼陈香痛苦万分的神情,瞳孔骤然一缩,立马大步跨过去,微颤着嗓子问着:“香儿,怎么了?你别吓我!香儿!香儿!”陈香看了一眼孩子,便撒手人寰了。她本想着得要和他说些什么,可颤抖的身子告诉她,自己已经油尽灯枯了。随着她的手,瞬间落下,钱首名双膝一软,直戳戳地跪在了地上。悲痛欲绝的心顷刻间被撕成了碎片,他带着哭腔大喊着“香儿!”可陈香已不再回应他,此时此刻的她犹如一炉已被烧尽的沉香,只剩下了灰烬。刚才还喜笑颜开的人现已热泪满面,乐极生悲,突如其来的伤痛几乎要了他的半条命!从那以后,他像是变了个人,对待下人总是喜怒无常,或许是那个经常在他身边劝他的人离开了的缘故吧!
......
像往常一样,刘远道进城赶考,花娘在醉芬芳打理和带孩子。可这次等待的时间比往日的要长许多,花娘一开始以为是路上出了什么事耽搁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花娘觉得心里头有些慌了,但依旧坚信着他不会有事!忽的,她忆起前几次他回来时,说什么大清巨变,国难当头的,科举怕是会受影响!已经数月不见,花娘拜托刘申他们照顾醉芬芳和两个孩子,然后自己去找他。说好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不能耍赖!可刚准备出镇,她就看见了与他同窗的王秀才倒在地上,衣衫褴褛的,身上还留下了多处血肉模糊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