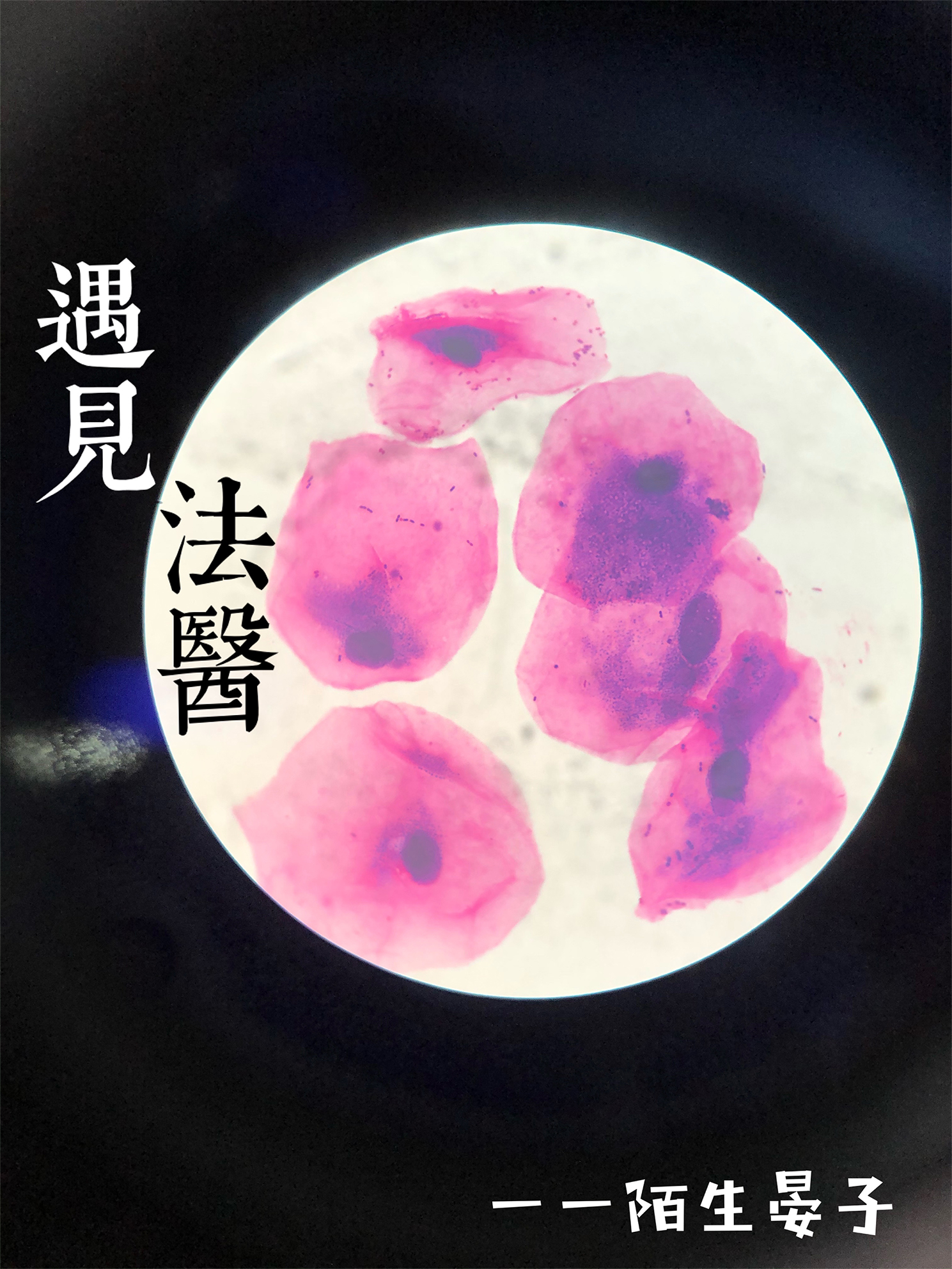北卫公步步逼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酒窖内低沉回荡。
神秘人稳操胜券的表情僵持在了没有人能看得到的脸上。
北卫公的拒绝显然出乎了神秘人的意料,以至于他勾起的嘴角甚至还未来得及放下。
北卫公悠闲地踱着步子,想象着神秘人脸上此刻无比惊诧与恐慌的神情,不由得心头大快。
他亦步亦趋地向前走着,脚步不疾不徐。
沉默中,神秘人终于意识到眼下的局势发生了逆转,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也是双方从接触到交锋以来,对方第一次占据了主动。
与其说北卫公喜欢占据主动,倒不如说他厌恶被别人当做可以随意摆布,任加利用的棋子。
当年拉拢穹隆山,稳固自己在戍北的地位时,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辰氏只是自己用来坐稳北卫公宝座的筹码。
可后来,当穹隆山凭借着他的关系,在戍北境内日益壮大时,他又觉得,对方这反而是利用了他。
这恰恰是北卫公所不能容忍的,由此,他对穹隆山的不满与忌惮与日俱增。
而此刻,神秘人甫一开始便表现出了一副有恃无恐,丝毫不给自己留选择余地的跋扈姿态,更将自己当成了予取予求,任凭拿捏的小人物。
这简直令他忍无可忍。
当一句话拒绝了神秘人,将对方苦心孤诣的谋划给尽数打乱之后,北卫公心里那一口恶气,终于是狠狠地撒了出来。
但他的拒绝却绝对不是意气用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或许可以说北卫公是个心机深沉,睚眦必报,甚至小肚鸡肠,锱铢必较的人。
但却无法否认,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为了一时意气,而被羞辱与报复蒙蔽心智,从而不管不顾做出一些令自己无法承担后果的人。
神秘人也深深了解着这一点,在经过了短暂的诧异与不解后,他很快平复了情绪,开始思索北卫公做此选择的原因。
可时间上,应该是已经来不及了。
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肩上。
一抹蔑笑,昭示了北卫公此刻的心境。
神秘人从他上扬的嘴角,读到了一丝猫戏耗子的戏谑。
“若有话,不妨现在说,孤给你这个机会,”北卫公戏谑道:“往日死在孤刀下的人,可没这个待遇,你可将此视为恩典,九泉之下,也足以做你吹嘘的资本。”
北卫公并不急于杀他,他想让这个蔑视自己,轻慢自己,羞辱自己的人,充分体会到生命脱离自己掌控的恐惧感、挫败感、无力感。
但北卫公终究未能从神秘人这里,等到他想要的求饶、服软与悔恨。
“北卫公怕是又要重蹈覆辙,想要仰仗穹隆山了吧。”
神秘人语气悠然,丝毫没有生命尽被他人掌控时所该有的恐慌。
北卫公闻言,持刀的手不由一僵。
果不其然!
以神秘人对北卫公的了解,他此刻的反应,便跟亲口承认无异。
“唉,你这北卫公当的......”
神秘人叹息一声,话未说完却是连连摇头,语气中满是失望。
“与你何干!”
北卫公色厉内荏,手中的刀向神秘人的脖颈又递了一寸。
“是与我无关。”
神秘人对逼近脖子的刀锋毫不在意,语气依然平淡:“但你若以为仅凭一柄濯日,便可号令穹隆山,甚至掌控整个戍北百家宗门,那我对你的观感,可不仅是失望二字可以表述的了。”
北卫公听闻此话,眉头一皱,不得其解。
濯日是穹隆山至高无上的镇山之宝,在北卫公的心中,其地位对于辰氏宗门来说,便相当于军中用于调兵的虎符,大兆人皇手中的玉玺。
持剑者,可号令山门,莫敢不从,这是他对濯日的定义。
“我问你,江湖规矩,可与庙堂律法一般无二?”神秘人见他皱眉,便知他不解,于是问道。
此话听在北卫公耳中,直如焦雷灌耳。
是了!
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信物,自古以来,兵将便是朝廷手中的双刃剑。
用时,是保卫边疆,维护皇权的无上利器。
不用时,又是令朝廷寝食难安,辗转反侧的心头隐患。
是以,拥兵自重者不可不防,是历朝历代掌权者所达成共识。
于是将虎符分为两半,一半由人皇亲掌,一半由军营最高统帅保管,虎符不全,则不可调兵。
而玉玺,则更为紧要,朝中有律,凡假传圣旨,伪造玉玺者,九族之内生者株连,死者鞭尸,由此可见一斑。
但江湖不同,要说与庙堂的区别,简而言之,江湖是看人看实力的,而不是看你手中拿到的是什么东西的。
否则,若有朝一日,因武林盟主心血来潮或脑子抽筋,突然决定将号令群雄的信物交给了一个鼻子下永远撇着两挂鼻涕的呆傻小儿,那整个武林的英雄豪杰难不成还都要听令于这个傻小子?
届时这蠢小孩来一句,俺要住最豪华的狗窝,于是整个武林震动,大张旗鼓地满八荒撵着狗跑,你让群雄情何以堪?
但朝廷不一样,虎符与玉玺分别代表着军权与皇权,即便持有者残暴也好,昏庸也罢,但凡他还在那个位置上,拥有着这么两个物件,那么王土之内,所有人都得听他的。
即使他的行为会导致国之不国,王朝覆灭,那也得听他的。
听起来虽然荒唐,但纵观历史,这样的例子还少么?
所以,这是两者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
但北卫公的身份毕竟不是无足轻重的黄口小儿可以比拟的,但他持有濯日,也只不过是拥有了话语权,真正的决定权,却不在他的手中。
结合眼下的情况来讲,自今日起,他北卫公落稷是拿到了濯日不假,但他不是江湖中人,即便他位高权重,却也不能直接向着百家宗门发号施令。
倘若他要发号施令,必须得通过穹隆山。
那么穹隆山,乃至于北境江湖真正的掌权者是谁?
辰昼!
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北卫公说,即日起,须把戍北国所有宗门世家全部收编在穹隆山门下,不从者灭之。
相信辰昼会欣然领命,因为这恰合他壮大宗门的志向。
但如果自己说,穹隆山上下听令,立即广召群雄,跟我共抗魔族。
那么辰昼八成会当做耳旁风,或者阳奉阴违敷衍于他。
为什么?
因为一来,此举对宗门壮大毫无裨益,即使抗魔成功,穹隆山也落不到什么好处。
二来,戍卫边境是他北卫公与大兆朝廷的事,大兆尚且坐视不理,穹隆山一个江湖门派,凭什么要身先士卒?
若是宗门因此覆灭,或一蹶不振,他辰昼有何颜面去面对列祖列宗,毕竟宗门最重视的便是传承。
经神秘人提点,北卫公想明了此节,眼神不由得黯了下来。
“看来你还不算太过愚钝。”
局势再次逆转,胸有成竹的微笑又重新回到了神秘人隐藏于兜帽下的嘴角:“既然如此,我不防再告诉你一件八荒之内无人知晓的隐秘,关于穹隆山至宝的秘密。”
北卫公霍然抬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神秘人那张隐在兜帽下的脸。
“濯日、染月、缀星,这三把神兵八荒之内人人垂涎。”
神秘人一顿,对北卫公渴求的眼神十分满意,他也没卖关子,道:“只是没有人知道,除了辰氏血脉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驱使,你自然也不行!”
又一道焦雷劈入脑海,北卫公身形一晃,险些站立不稳。
控制不住言行,暴露自己的弱点,乃是谈判中的大忌,但也不能怪他在敌人面前如此失态,实是对方的言论太过匪夷所思。
这句话若是丢入中荒之内,必会引起轩然大波,也难怪北卫公会做此反应。
“在明知濯日于我而言,一不能号令山门,二不能任凭驱使的情况下,却仍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将濯日赠予我,且还宣称穹隆山上下唯我马首是瞻,这是在图谋什么?穹隆山到底在图谋什么?他们又想利用我!”
北卫公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方的圈套,坠入了无法自拔的揣测中。
不对!
他有辰月,辰月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辰昼血脉至亲的独女。
即使一切都是假的,难道怀了我的孩子是假?与我朝夕与共,共同患难还能是假?三年,整整三年,这千余个共度的日日夜夜也能是假?
“你在挑拨离间?”
北卫公眯起了狭长的双眼。
“呵!何需挑拨离间。”
神秘人冷冷一笑,不屑道:“如此拙劣的谎言,一戳便穿。如今濯日已落入你手,你若不信,回头一试便知。”
“我若信了你的话,返回殿内,你不正好脱身,免于一死?”北卫公冷笑。
“你也可以现在就将我杀了,随后再去验明真假,只是代价......”神秘人主动将脖子凑近刀锋。
北卫公迟疑了。
他又忍不住陷入了怀疑之中。
辰月不日将诞下他的骨肉,那无疑是他的血脉,但同时也是辰氏的血脉。
唯辰氏血脉不可驱使!
也便是说,将来他的孩子,是可以驾驭濯日的。
这么一想,他落稷的孩子,终究还是落家的血脉,这是不争的事实,假以时日,当他的孩子世袭北卫公的爵位后,北境军方与江湖的势力,终归没有旁落。
即便自己不是直接受益者,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对!
辰星!
还有辰星!
他漏算了辰星!
濯日历来便是穹隆山历任宗主的傍身之物,从无例外。
而辰星作为穹隆山将来毋庸置疑的宗主,此番前来,竟然如此大度的将他未来自证身份的至宝送给了自己,甘心成为一个穹隆山自开宗立派以来,首个没有濯日的宗主,这本身就极不合理。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是想借此麻痹我,进一步壮大穹隆山的声势。
等吾儿上位,根基未稳之时,取回濯日,并将其架空,做个徒有虚名的傀儡,自己则成为戍北真正的掌权者!
唯有如此,才说得通!
届时这北境究竟是姓落,还是姓辰,那可就两说了。
这便是穹隆山的图谋么?!
穹隆山其心可诛!
有冷汗自北卫公的额角淌下。
神秘人见他表情连番变幻,连持刀的手都不自觉得松懈了下来,脸上笑容更深。
可即便自己深信着穹隆山有此图谋,北卫公却依然下定不了决心。
此事事关重大,一旦事情败露,那便会落得个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且会背上千古骂名。
于是,他又犹豫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若是担心背负上勾结异族,造反谋逆的骂名,却是大可不必,成王败寇,历来如此。”
神秘人一语中的,道出了北卫公的顾虑:“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写就的。前朝如此,当朝如此,后世也一般无二。”
北卫公不语,他心头急转,权衡着利弊。
“莫非堂堂北卫公是个畏首畏尾的鼠辈?”
见他游移,神秘人暗道有戏,激道。
北卫公仍在沉默,似若惘闻。
“我问你,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未来的抱负又是什么?难不成是立志于躲在穹隆山的庇护下狐假虎威,当个中荒家喻户晓的笑话么?”
神秘人将手中的酒觥一抛,讥笑着问道。
“你他妈的,真当孤不敢杀你么!”
北卫公借助穹隆山的威名,在国中肃清异己,整理朝纲之事,在中荒之内早就沦为了笑谈。如今被他屡触逆鳞,北卫公终于忍无可忍。
刀锋刺入神秘人的脖颈,有殷红的鲜血渗出。
“人族五州四国,唯有这戍北贫瘠荒凉。
你却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自以为傍上了辰家这座靠山,便可以安枕无忧,甘愿偏居僻里当个为人耻笑的山野诸侯。
我问你!
你可曾见过怀南国的盛景,那里花香袭人,四季如春;
你可曾见过踞央城的壮丽,那里高楼广厦,鳞次栉比;
你可曾见过延西国的富庶,那里满目金银,珠光宝气。
不!
你不曾见过!你当然不曾见过!
若无人皇召见,你连这国境也出不得半步,这不是你的封土,这是人皇用来囚禁你的牢笼!
你却尚不自知,甚至沾沾自喜。
在这牢笼里,你把你的子民一次次送上战场,每当有魔族入侵,你便要拿他们的命去相抵,你的子民笼罩在魔族的阴影下,深陷在苦寒中,你却对他们的生死疾苦置若罔闻。
人皇把这封土,把这爵位当做链子拴在了你的颈子上,你便甘之如饴地替他守护北方门户,谁进来,你便咬谁!
你就情愿顶着北卫公的称号,做一条寰家的看门狗么!”
身影突然颜辞俱厉,怒声呵斥,在北卫公心头又加了一把火。。
“放屁!放屁!放屁!”
北卫公被他说得面红耳赤,羞愤难当,长刀在神秘人的脖子旁虚张声势地来回比划,但却不敢当真斩下。
他想反驳,但却找不出反驳的话语。
“我放屁?那你倒说说,我哪句话说得不实?”
神秘人恢复了平缓的语调,只是那声音中透着彻骨的冰寒。
“你当这些我都不知么?我戍北毗邻北荒,气候苦寒,土地贫瘠。
空守着夜暮山这么一座宝山,却碍于你们魔族的滋扰而无法充分利用。
国中子民只敢在林子边缘伐木打猎,以此糊口。
每当荒北南下的朔风刮来,大雪便封了山,子民们若没有备足木炭肉干,绝难挨过凛冬的严寒。
这还不算!
戍北边境绵长,难以防范,你们这些畜生还时不时的有那么零星几股,三五成群,翻山越岭穿过夜暮林,流窜到猎户樵夫们的村子里好一通烧杀掳掠。
每当边防的将士们闻讯赶至,却只能望着满目疮痍,站在尸横遍野的废墟里颓然长叹。
但当意图追击之时,却发现你们那些畜生们早已一头扎进了苍莽的密林,扬长而去,守军只能跟在后边吃屁!
我国子民陷于水深火热,苦不堪言,生怕下一个在睡梦中丢掉性命的人便是自己。
决心逃离戍北者多如牛毛,纵使穿国越境的行牒无比难签,他们仍是削尖了脑袋去争去抢。
在他们心里,即使是逃往南方诸国去当个遭人唾弃的乞丐,也强过于在这戍北国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偷渡者死!
我唯一能想到保住戍北人丁的便是这么一个畜生不如的手段!
这我知道!
全部都知道!
可我有什么办法!当初被封为北卫公的又不是我!接受世袭爵位的也不是我!
是落仪!是落仪!
是我那明明推翻前朝统治,功劳比当今人皇还高的祖父——落仪!
是在无数人的拥戴下,竟甘愿舍弃人皇宝座,毅然决然投身至这片荒凉土地的落仪!
他好大的度量!好大的气魄!
可凭什么?
凭什么把这一切算在我的头上!当狗的是他!不是我!”
北卫公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歇斯底里声嘶力竭的怒吼在酒窖中嗡然作响。
啪!
清脆的耳光声合着北卫公未竟的吼声,在地窖内不住回荡。
那神秘人不知何时,竟无视刀锋,欺近了北卫公的身前。
北卫公怔怔地喘着粗气,捂着被掴得又红又肿的面颊,一时竟没反应过来。
“懦夫!”
伴随着一声唾骂,神秘人扬起的手才刚刚放下。
“找死!”
北卫公回过神来,怒吼着抬手一刀斩向了神秘人的头颅。
身影却毫不慌乱,抬手摘下了头上的兜帽,露出了隐在其中的容貌。
那面容苍白枯槁,遍布伤痕,一道道血渍已然干涸,却依然不难看出,他的眉眼间竟与北卫公有几分相似。
“稷儿,你要杀了为父么?”
刀锋悬顶,仅余一指之时,此人泰然发问。
当啷!
北卫公垂下手臂,手中的长刀应声落地。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之人,颤声唤道:“父......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