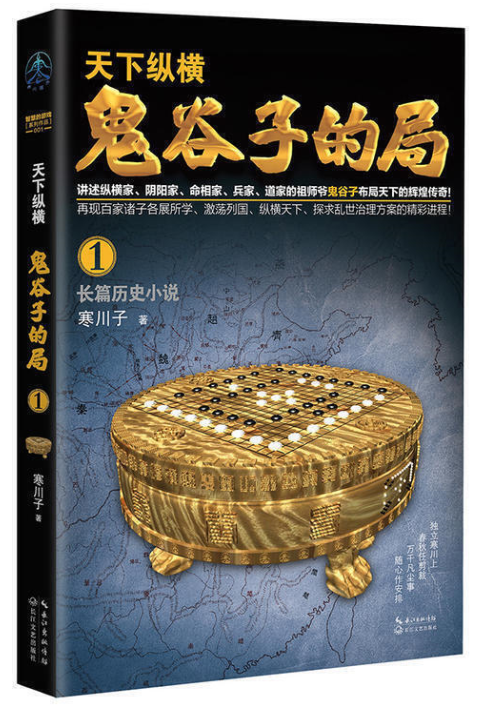昏暗阴冷的酒窖内。
北卫公围着装满修罗血的酒坛子转了一圈,在坛子后方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一日一口,循序渐进。
“这想来便是修罗血的用法了。当初落仪应是未遵循此法,摄入过量,最终落得个爆体而亡的凄惨下场。”
北卫公心里想道。
他以手指沾了一下坛中的血液,触之只觉温暖粘稠,似与普通血液别无二致,可这酒窖阴寒,寻常的血绝无可能留有余温,除非此血刚刚离体不久。
难道父亲将将离去不久?
可如此之多的血量,究竟出自多少修罗之体?
父亲究竟又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带领那么多修罗潜入此地的?
那些桀骜难驯的修罗们又为何甘愿听一个外族之人调遣?
北卫公眉头蹙成一团,猜之不透,没奈何,只得放弃了徒劳的揣摩。
他抬起手指意欲好好查看,却发现血液无法附着于手指之上,顺着掌缘流下,竟毫无血渍。
多想无益,他唯有按字条之法,俯身啜饮了一口。
浓烈的血腥气直灌口鼻,他胃里翻江倒海,险些一个没忍住给吐了出去。
好在北卫公意志力强大,强忍着体内传来的剧烈抗拒之意,舌头将血卷入喉头,皱眉咽下。
那一线血液入喉,流过胸腹,北卫公双眼紧闭,喉管内传来的黏腻之感,让他眉头蹙得更深。
血液入腹,北卫公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只觉体内一道暖流直达四肢百骸,先前的疲惫空乏之感一扫而空,周身已被前所未有的力量充盈。
腿上的伤口处缓缓传来一阵瘙痒,他低头看去,只见翻卷的皮肉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这便是修罗血么,若以此物供给军队,假以时日,拿下踞央,似乎也并非难事,奈何只有区区一坛。”
北卫公想道。
突然,他听到酒窖深处传来了声声低语,先前竟然没有察觉,看来,这耳聪目明的益处,也应归功于修罗血。
“父亲?”
北卫公向酒窖深处走着。
没有回应,他继续向前。
突然,一股极为熟悉的危险之感从北卫公的心头升起,控制不住地战栗从他的脚趾一路蔓延向上,直至头皮。
北卫公立时放缓脚步,尽量不发出一丝声音,小心翼翼地走向低语的源头。
在灯火映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里,现出了一道异常伟岸的身影,他的心随之悬了起来。
北卫公随手取下一把火盏,照向身影,定睛细看。
但见那人委顿在地,即使瘫坐着,却也与自己身高几近,壮硕修长的身躯上肌肉高耸,青筋虬结,与他相比,魁梧如北卫公,竟也显得不值一提。
他肤色玄青,面目狰狞,白齿而乌唇,四颗尖利的獠牙紧扣下唇,眼窝深陷,而眉骨额头尽皆高耸,额头生有指厚的乌青骨甲,骨甲表面遍布刻痕,额纹繁复,额上生有双角,分于头颅两侧,锐如枪尖,额甲之后则是一头深灰长发直垂腰际。
竟赫然是一名修罗!
北卫公被突现此地的修罗吓地连退几步,险些跌倒在地。
可酒窖内逼仄狭窄,避无可避,他又手无寸铁,心头不禁想起临阵遭遇修罗时,那纵横杀伐无可匹敌的凶悍之姿,惧意横生。
北卫公自知毫无胜算,却也不甘坐以待毙,硬着头皮欲要上前拼死一搏,奈何双腿重如灌铅,竟是一步也迈不开。
恰在此时,前方的修罗又发出了低语,但因距离太远,听之不清。
北卫公心想,这凶獠若要动手,又岂能等到此时,却不如听听他要说些什么,也好死得明白。
心头的好奇,终于压下了胆怯,北卫公靠上前去。
但见修罗神色木然,口中含混不清的重复着:“穹隆山,辰昼,求我族助他称王......”
这便是父亲送来的凭证么......
北卫公看着呆立不动,说着一口蹩脚人语的修罗,恍然领悟。
修罗忽然抬手。
北卫公一惊,以为他要动手。
但修罗抬手后却一动不动,北卫公诧异不解,而后见他伸出一指,指向身后,这才意识到他似乎是在向自己示意着什么。
北卫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却发觉只有一排酒坛子。
他细细看了一遍,除此之外别无他物,随后才发现,所有的酒坛似乎都曾被开过封,只是又给封上了。
他心头狂跳,莫非......
北卫公迫不及待地一个个揭开了酒封,酒坛子里果然没有酒,赫然如他所料,竟是几乎满溢的修罗血。
“独木难支,魔族允我先行打造血徒!”
修罗自他身后说道:“你须确保孕妇送往夜暮山,所有!”
北卫公心头狂喜,几乎便要吼出声来。
有此助力,便可打造一支无匹雄师,将寰氏拉下皇座,指日可待!
******
北卫公在酒窖内呆了大半日,踟蹰着要不要将修罗血给落离服用,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只想让弟弟这一生能当个平安喜乐无忧无虑的庸人,所有的富贵荣华都由自己给予,所有的骂名凶险都由自己背负,在自己的庇护下长大,
这才穿过了层层宫墙,曲径折绕,来到了宫内一处僻静的院落。
此刻天色将晚,每年的这个时候,北地的夜总是降临得很早,风中已透着凛然的寒意。
院内,一个老嬷嬷正搀扶着一位妇人往屋内走去。
北卫公上前道:“嬷嬷,我来吧。”
老嬷嬷转过身,见是落稷,微微颔首行了一礼。
“公爷,您又来看老夫人了。”
老嬷嬷理了理落母被风吹散的鬓发,这才松开了手,让在一旁道。
“嬷嬷不用拘礼,我也有些日子没来了。”
北卫公亲手搀过母亲,声音轻柔。
“老身还有些活没做完,就不打搅小公爷和老夫人说话了。”
老嬷嬷又行了一礼,这才退下。
“少倾还需有劳嬷嬷侍候母亲睡下。”
落稷对着嬷嬷的背影说道。
嬷嬷回首点了点头,径自离去。
落稷把母亲扶进了屋内坐下,点燃了灯,又拍了拍母亲衣上沾染的些许纤尘,这才陪着母亲坐在了一旁。
落母目光呆滞,口中喃喃着不知说些什么,似在哼着一首曲子。
“母亲,爹爹回来了。”
落稷低头握着母亲的手。
落母眼中一片混沌迷蒙,似是罩着一层雾,对他的话没有做出回应。
落稷习以为常,也未说话。
只是不住摩挲着母亲的手,听着她呓语般,断断续续地曲调。
良久。
“母亲,儿子怕是再也回不了头了。”北卫公肩头耸动,仿佛犯错后不知所措的稚童。
曲不成曲,调不成调。
摇曳的烛光,映照着落稷流泪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