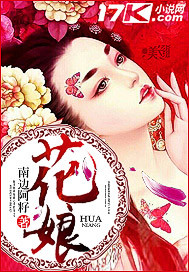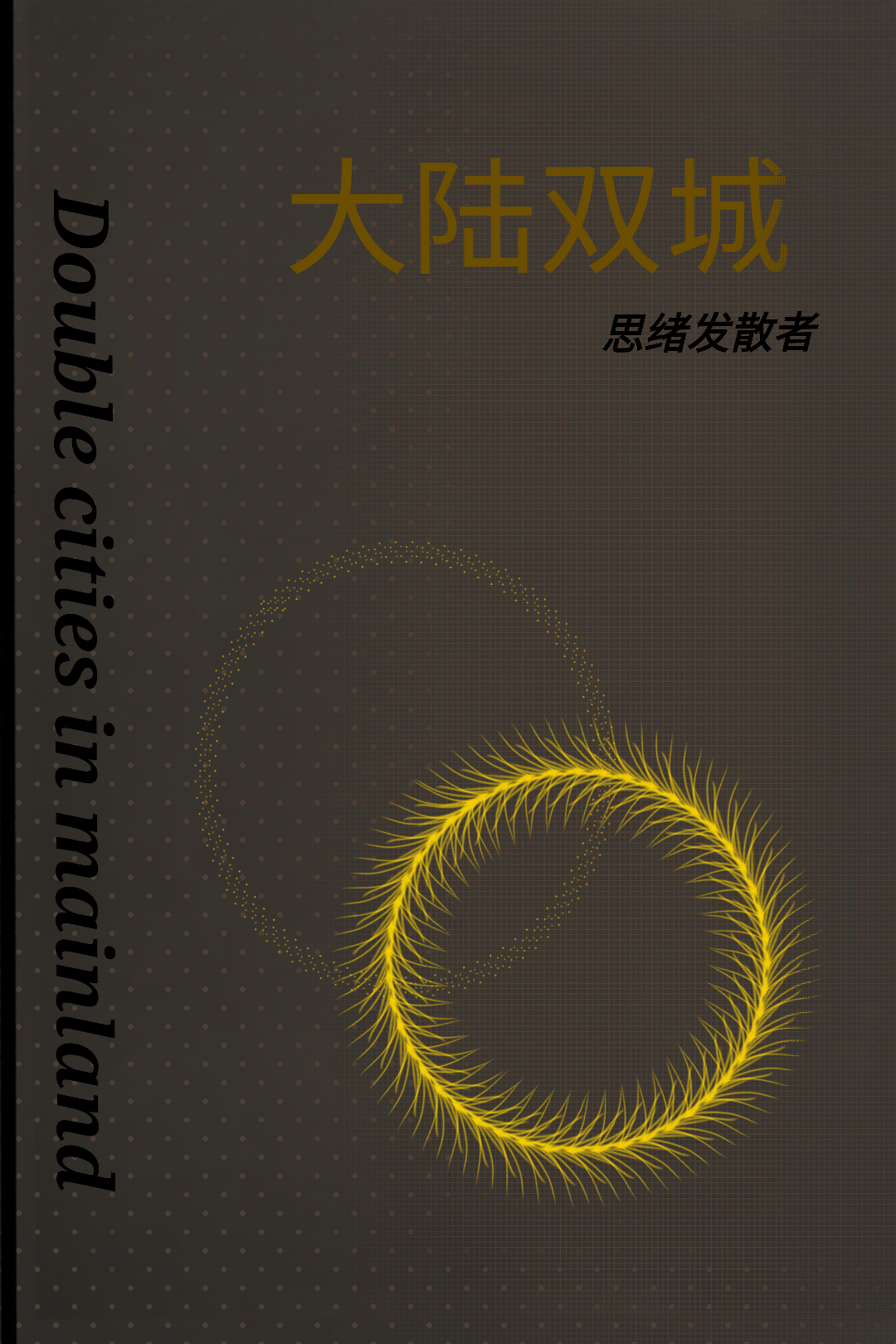自打我记事起,我便记不大清楚爷爷是怎么样的,只听父辈们说,你爷爷啊,跟你大伯很像,尤是眉宇间,这促使我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总会很好奇的打量大伯,大伯脸细长细长的,很精明的人,九几年的时候,卖铜赚了一万多,在那个时代,不可谓是不厉害,可也仅限于此,对我父亲是没有任何的救济,就因为大奶奶送我父亲上了大学,并没有送大伯去读大学,大伯读完高中就辍学了。
跟大伯相反的是我一直感怀的大奶奶,大伯是大奶奶的儿子,腿脚不利索,养着鸡鸭家畜,我们回来了,得给我们拿一只来,过年过节的,拿了不老少干货,可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晚年过得甚是凄惨啊,住的地方靠近牲畜圈,你说蚊虫虱子不得吃人,床呢,还是老式的梨木盖顶的方正床,吃,倒是还好,跟着儿子,送过来一点,吃一点,日子过得紧巴巴,去年七月份就死了,死的不是很风光,平平淡淡的,我父亲没有回去,这其中原因,是我最不愿意提及的。
因为这样,我这半年本是有机会去B城拜访下大伯的,可我不愿去,也不想去,不愿意同这势力人家陪上笑脸,不想去同这个唯利是图的人家多说一句话,但大伯母倒是心善,我妹子去,乐呵的买衣服,买玩具,买零食,领着去动物园看大熊猫,临走,还要送到汽车站,是真真做到主人家的责任,虽然我不大喜欢他们,不过我知道,亲则近,不亲则疏远,
后来父亲说“大奶奶死的日子,我没有回去,不是我不能回去,而是本不该回去。”
说到回去,石头已经三年没回过老家,他奶奶原先留了一口塘,老歪脖子细柳,岸旁的的黄芦夹岸丛生,里头还放了鱼,年底积蓄一季的塘沽要放水,村里邻近的要来捉鱼买鱼,我和石头则是里面最最积极的,捉到鱼,他奶奶是不管他带我捉鱼的,在家里生火煎鱼吃,他不大会,可我姐会,所以我总总叫我姐来吃,鱼肉外焦里嫩,撒一点辣椒丝,再配一碗香米,是最好的回忆。
回忆是美好,可这石头啊,坐牢了,不学好,跟人斗殴,把人打残了,警察找上门来,刚刚成年就去了牢房,他还有一个儿子,两岁,一个老婆,十八岁,年纪轻轻的,学了不好。因为这个事情他的母亲没少哭,没少抱怨,甚而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儿子坐牢了,老公就吸毒被抓,十月份刚刚出来,成天以为老婆出轨,背着自己偷男人。
后面啊,这个女人还是没死,活得好好的,就是胖了许多,一直说想回来陪小儿子读书,似乎把所有的希望给予给小儿子,小儿子啊,不大缺钙,有点缺爱,从六岁起父母闹矛盾,在小学里,也是不老实,上课睡觉,下课打架,我倒是跟他挺相熟,那时候在老家经常跟他去放鞭炮,到别人家的鱼塘钓鱼,稳稳的一个小跟班。
小儿子尚且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但这个女人还是活着,跟她聊天的时候,说啊“徐家小子还是聪明,不给大人添麻烦,那像我家这两个没有一个争气的。”每每于此,都要深深叹息,旁邻居不免要安慰一下。
其你要说我老家的后辈难道没有聪明的孩子,倒不是没有,是少了,连我也是愚蠢,不是智慧的,以前觉得,人人都是一样,但现在,我明白,你是什么样的,在你出生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像光叔的女儿,上次去C城的时候还看见她,背着个大行李袋,在天桥底下卖衣服,穿了件羽绒服,坐在那里卖五十块的廉价衣服,我认出她了,她也看了我一眼,可能是没有认出来,也有可能是不愿意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知道自己的落魄样子,我没打算去打招呼,因为我知道,你落魄的时候,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
“卖衣服了,帅哥,美女,来看看了,这面料,这工艺,你摸模看。”
叫卖声很大声,迫于生计,你不叫大声一点,这个摊位就没生意,别人就得抢你的生意,这地方,卖衣服的,也不止这一家,旁边还有一个男人也在卖,她跟他说着什么,没听清楚,不知道过了这个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总不能像她哥石头一样蹲牢房吧。
说到这个婚姻,我堂姐是比较幸福的,虽然家里有个妈宝男,但至少儿子听话,光叔的女儿再没有本事,还能有机会回家看看老爹,像我苗家的一个阿姐,前些日子大爷爷大寿回来,问我在哪里读书,问我学了什么,问这问那的,她嫁到云南去了,老家在A省这里,一年到头,可能回不来,这不,头一年寄钱,再一年什么都没有,往后可能电话都打得少,阿姐的奶奶带她长大,也舍不得回来看看。
更不用提她那不成器的弟弟,成天窝在床上,要不然就是出去泡妞玩车,不学无术,他老爸就是我二舅,我二舅宠着他,出了事,赔钱赔礼道歉,怀了孩子,打的打掉,有的家里人不干,还得忍受打骂,就这个,我阿姐的弟弟,回家了连声爸都不叫,还成日成天扬言在黑道上混出个模样用他的话来说叫“在法律的边缘游走”。
我老徐的生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至少比之要好很多,但像他这般的,你认为天理轮回会饶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