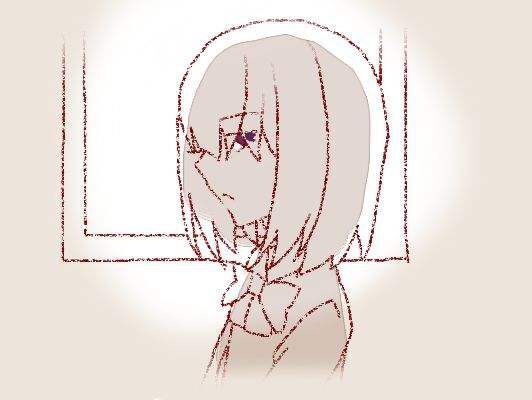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的灵魂曾是这世界上最杰出的生灵,他们善良、勇敢、睿智,有大无畏的探索精神,与无与伦比的浪漫情怀。神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如此优秀,并未感受到欣喜,取而代之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惧怕人类有一天会过于强大,从而质疑众神的权威。因此,神想尽办法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意为“先见之明”)曾与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共同创造了人类,普罗米修斯负责用泥土雕塑出人的形状,雅典娜则为泥人灌注灵魂,并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
当时宙斯(Zeus)禁止人类用火,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的困苦,帮人类从奥林匹斯山盗取了火,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因此触怒宙斯。宙斯为了惩罚人类,将潘多拉的盒子放到人间,里面装满了祸害、灾难和瘟疫等,人类从此陷入劫难。
但尽管如此,人类依然发展出了自己辉煌璀璨的文明,并模仿神建造了宏伟壮丽的宫殿。
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再次引起了神的不满,所以12000年前,亚特兰蒂斯大陆沉入海底,人类创造出的辉煌文明再次被毁于一旦。甚至在7000-8000年前,神妄图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但人类的探索精神并未因此而畏缩不前。
公元前4200年,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从此,人类有了民族、信仰、阶级、文化等隔阂,文明的发展日渐缓慢。
公元前2690年到2670年左右,古埃及文明建造了至今仍称之为奇迹的金字塔,所展现出来的高度发达的建筑、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的精湛甚至令现代的人都望尘莫及!
在曾经人类文明最辉煌璀璨的那个时代,求知欲几乎是人类唯一的欲望。但就像当初宙斯将潘多拉魔盒送入人间,众神也让人类有了越来越多的欲望,权利、财富、地位,甚至生殖繁衍。渐渐地,人类开始像动物一样掠夺领地、抢占财富,甚至发展为对生殖的崇拜与对繁衍的迷恋。人类像老鼠、兔子一样在全世界迅速繁衍,数量的增加却冲淡了灵魂的精良,人们开始变得浮躁、愚昧、自私,甚至乏味无趣。
这些故事都是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的,他总会给我讲很多有趣的故事,而我也总是选择相信。但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其实都反映着残酷的现实。
我叫奥斯米塔拉·泽尔格,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占领时期的爱沙尼亚。我的父亲西尔维斯特·泽尔格从我记事起就毫不避讳地告诉我,我们的家族是古老的安魂师,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通灵者。而且他从不会让我刻意避开那些逝去之人的亡灵,因为他们不会伤害人类,他们找到我们,或许只是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的家乡在伊萨库(Iisaku),临近芬兰湾的楚德湖畔,那里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几乎一半的土地都被森林与沼泽覆盖。父亲说波罗的海孕育了最优秀的民族,也培养了最纯净的灵魂。我想最纯洁的灵魂应该像家乡星罗棋布的湖面一样清澈,倒映着蓝天白云,湖边绿草如茵,静谧安详。
我们从不出现在逝去之人的葬礼上,因为父亲说那只是埋葬逝者躯体的场所,他们的灵魂会逗留在最不愿离开的地方,与自己的一生做最后的怀念与道别。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那些地方找到他们,然后送他们安详地离开。普通人类的灵魂只能在世间停留几天,如果因为执念不愿离开或者被困在某个地方出不去,时间一久他们的灵魂就会逐渐消散,再也无法进入冥界转世。
“所以世间的灵魂会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出生的很多人灵魂不完整,甚至没有灵魂。”当父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幼小的我非常惊讶,有些不敢相信地问他,没有灵魂的人在世间该怎样存活呢?
我记得,父亲指着邻居家的院子让我看那些低头啄食的鸡,“大概就像那些鸡,它们也能生存,吃饭、睡觉、下蛋……它们没有自由的意识,只有生存的本能,被人类圈养,就像人类被上帝圈养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怀疑父亲说的话,因为我不敢相信有人会像鸡一样活一辈子,那他们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但长大后我才明白,没有灵魂的人其实占据了绝对的数量,他们是神与人类统治者的联合产物,因为二者都希望所有的人类都像听话的牲畜一样利于圈养,而且可以自行繁衍生息,不用去管他们,他们的数量就会像草原上的兔子一样增长。
“那我们也是兔子吗?”我有些伤心地问。
“不,当然不是。”父亲摇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是灵动的小鹿,在森林里自由奔跑!”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去看邻居院子里的那些鸡,而是一有空就往湖边的森林里跑,去拜访那些自由自在的动物们,探索它们有趣的灵魂。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会在森林中见到人类的灵魂。
那是我15岁那年的一个冬日的午后,太阳落得特别早,森林中很快便被昏暗包围。我踩着厚厚的积雪向森林的边缘艰难挪步,却在接近湖边的稀树林中看到一个徘徊的身影。我以为是有外地人途径此处在白茫茫的雪地中迷路了,便上前讯问是否需要帮助。那是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大男孩,正带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在雪地上艰难踱步。当他听到我的呼唤转过身,我才猛然发现那不是人,而是一个漂泊无助的灵魂。
“你在这儿做什么?”我问,“我可以帮你吗?”
他看着我,眼中尽是彷徨与忧伤。
我几乎立即就看出他不是普通逝者的灵魂,因为他身上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灵力,古老而神秘。他略带忧郁地看着我,并未说话,而是伸出一只手,手掌向上,掌心中忽然浮现出一抹奇异的亮光,洁白而寒冷,呈现出类似植物幼株的形状,晶莹剔透,闪闪发光。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看上去是棵幼株,却能感受到比人类灵魂更强大的灵力,甚至会让人心生畏惧,却又令人如此着迷!
我尽力克制住自己复杂的情绪,想要对他说,对不起,我没见过你在寻找的东西。但我不想让他失望,不想看着他眼中的光芒暗淡下去。所以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他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我,随即收回手掌,转身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我则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将我在森林边缘的所见告诉了父亲。
“你见到的不是亡魂,而是生灵。”父亲说。
“生灵?”我闻所未闻,“生者也会灵魂出窍吗?”
“当一个人身体很虚弱,某种意愿却异常强大的时候,他的一部分灵魂就会从躯体中分离出来,游走在人世间,像是漂泊不定的幽灵,只为一份执念,一份执着的追寻。”
“那他在找的究竟是什么?”我忍不住问。
父亲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我是否能理解或者接受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依你的描述,你看到的应该是最古老的灵魂。它以灵草的形态依附在一个黑暗寒冷的地方,吸取着可怕的力量,但它本身却又是凝聚着神力的稀有之物,而且以人类的样貌存在。”
既是灵草,又是人类,又是神灵,当时的我很难想象那究竟是什么,却隐隐觉得一定是极其稀有的珍贵灵魂,所以那个人的生灵才会如此苦苦找寻!对于像我们这样专门与灵魂打交道的人来说,哪怕能看一眼也是莫大的幸运!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个灵魂!
但少年时代的美好愿望用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就在第二年,可怕的事情开始在我身边发生。先是我无缘无故地大病一场,几乎没能撑过那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在那些寒冷而绝望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卧病在床,只是偶尔会醒来几次,便很快又昏睡过去。昏迷的时候我时常会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他时而会徘徊在我的窗前,时而会来到我的床边,有时甚至会像蝙蝠一样依附在屋顶阴暗的角落里,在阴影中用猩红的双眼盯着我看。我害怕极了,却又无法醒来。我不知道那是恶魔还是死神,只知道连父亲也受到了它的威胁。他想与那个黑影做抗争,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它的对手。就在我以为自己会被那个可怕的黑影带走的时候,我却安然无事地醒了过来,而且病很快就好了,没过几天便又可以跑出门外感受大自然的清新。就在我为自己的大病初愈感到喜悦的时候,父亲却仍然一脸愁容,似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就要走了,”那天他认真地看着我说,“我们必须要分开。”
父亲突如其来的话语令我不知所措,我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在无意间伤了他的心。
“不是你的错,”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看着我的眼睛,奥斯米塔,永远记住我爱你胜过一切!但我们不能继续在一起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必须要确保你的安全!”
我隐隐觉得父亲的离开一定跟我生病昏迷时见过的那个可怕黑影有关,他一定是在躲避什么,而我,是他绝不能失去的。
“我要向西去往斯堪的纳维亚,而你,要往东去西伯利亚,深入茫茫的林海中,再也不要出来!”父亲用双手将我的脸颊捧到他的面前,看着我的眼睛,“不要相信任何人,但一定要相信自己。永远不要吝惜我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人类的灵魂已经越来越少,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挽救他们!”
我永远记得那天,大雪初融,露出一片贫瘠的荒原,如层层海浪一样的云层压得很低,铅灰色的湖面上一片阴霾,一切仿佛失去了色彩。
我按照父亲的嘱咐一直往东,不知走了多久,所到之处尽是茫茫的林海雪原,仿佛已经离开了人类生活的世界。过了圣彼得堡,一直走到伏尔加河北岸的雷宾斯克,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二年。
二十世纪初,一种叫做“西伯利亚理发师”的大型机械开始在西伯利亚广袤的原始森林中咆哮肆虐,成片的树木被快速砍伐,我的栖身之地转眼间面目全非。那天我被机器的轰鸣声吵醒,看着被巨型机械残忍推平的家园泪流满面。我知道人类正在加紧消灭自己灵魂的步伐,而这,只是自我毁灭的开始。
贫瘠的森林中没有能吃的东西,饥寒交迫的我只能违背父亲的叮嘱走出森林,去附近的小镇打零工养活自己。但人生地不熟的我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很快我便陷入了绝望的边缘无计可施。在那个地方我所见过的所有男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就像狼克制住扑上来的欲望直勾勾地看着羊从它们面前经过,而所有的妇女都拒绝为我提供帮助,甚至连一块干巴巴的面包都不愿施舍,更甭说为我提供工作的机会。我忧惧地看着他们,惊讶于为何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灵魂?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没有生命的行尸走肉,令我既惧怕又叹惋。我终于相信了父亲曾经说过的,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没有灵魂、像被圈养的牲畜一样存活在这世界上,却不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哪怕一点生命的色彩!
有一次我坐靠在路边一座被废弃的小木屋旁,饿得几乎晕厥,朦胧之中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向我靠近,无力的双眼却怎么也睁不开。
我很害怕,担心有什么危险在向我靠近,可就在忐忑不安的时候,却听到了有记忆以来最好听的声音。
“你还好吗?”那声音像极了父亲,但更柔和一些,仿佛天使就在我的面前。
但当我无力地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一张陌生男子的脸,正关切地看着我。我本能地想要躲到门廊里面,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别怕,我只是担心你生病了。”说完他走到路边在那里停放的一辆自行车后面取下一瓶牛奶,善意地递到我面前,“你很瘦,看上去饿坏了。喝了它吧,还是热的!”
我正迟疑着要不要接过来,抬头却看见他的身上散发着幽微的光晕,就像白雪反射的月光,轻微且柔和,我顿时惊讶,那是灵魂的光泽,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有灵魂的人通常是善良且可以信赖的,于是我感激地接过他手中的牛奶,举到嘴边一饮而尽。面前的这个人或许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当我将空的奶瓶还给他的时候,他惊讶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怜悯。“你迷路了吗?”他问,“是否需要帮忙?”
“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坦诚地说。
“如果你信得过我,请让我帮助你吧。”他说。
这就是我和阿列克谢·捷洛斯卡的相遇,并没有多少浪漫,甚至还有点凄凉。但他的出现就像阴云密布的天空洒下一缕阳光,照在灰色的海面上,光柱下海鸟飞翔,原本阴暗的海面波光粼粼。那天他带我去了他工作的养牛场,他是那里的送奶工,工作辛苦却收入微薄。但他乐观开朗,枯燥乏味的工作也显得颇有乐趣。他趁老板不在给我吃了差不多有10洛特(约128克)的奶糕(鲜奶煮稠后放凉的固体),和10洛特的奶渣,然后带我去看了那些养在棚里的奶牛。我很快就学会了挤牛奶,虽然他的老板坚持说不需要帮工。但在阿列克谢的恳求下,我被允许以打杂的身份借宿,不给工钱,只可以暂时留宿。但我很快搬去了阿列克谢的小屋,并确定了恋爱关系。当年圣诞节前我们便结婚了,我们在雷宾斯克医院旁边的木质小教堂举办了简单的婚礼,神父甚至还允许我带了一只奶牛作为伴娘。婚后的日子简直像天堂一样幸福,阿列克谢照常每天去送牛奶,而我则把奶牛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产奶量也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