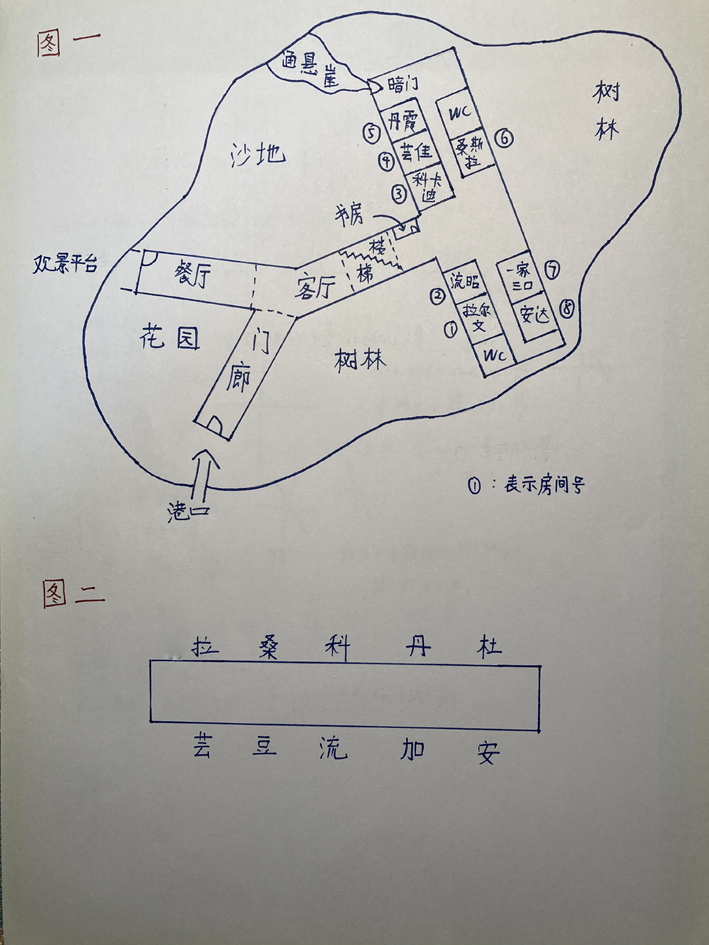维克多在回公寓的路上发觉有人跟踪自己。或许那人自他出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尾随。维克多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这一天迟早都会来临。他只是在路上慢慢地走着,脚步沉重、浑身冰冷、胸口疼痛。但他仍会举目眺望,欣赏这座城市夜色中的雪景。“真美!”他由衷地赞叹到,即使知道死神的脚步正在追随。
不知从哪飘来了凄婉动人的歌声。在寒冷寂静的冬夜,那歌声如同雪花一般静静飘散,仿佛在为即将逝去的灵魂送行。维克多听着那歌声,嘴角浮起一丝忧伤且欣慰的微笑。
回到公寓的时候几乎精疲力尽,但他内心却满是兴奋。他点燃一盏煤油灯——或许是不想让电灯浸染了如此寂静的夜晚——将桌上的打字机摆正,然后带着些许亢奋,甚至是有些愉悦的心情开始敲打键盘。
打字机旁边放着一摞稿件,他的动作如同行云流水,手指熟练而快速地敲击着键盘。
夜空的黑云散去,月光如流水般倾泻而下,笼罩着冬夜寂静的城市。月光将蜿蜒的伏尔塔瓦河化作一条银色的丝带,布拉格如同一位美丽的爱人在夜色中轻声吟唱。维克多聆听着这夜的温婉,同时双手快速地敲击文字。
与此同时,他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那声音缓慢却清晰,仿佛每一步都在楼层间回荡。
维克多却仿佛丝毫没有被那声音搅扰,而是越发聚精会神,快速敲打着最后的文字。
身后的房门终于被打开了,门外的夜风晃动着煤油灯昏黄的火光。维克多停下手中的动作,他已经在最后时刻完成了。
麦克维西踏入房门一步,同时举起一只手,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书桌前那个人影的后背。
正在此时,那个人却突然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转过身。他脸色苍白,眼神却异常兴奋,嘴角带着一丝鲜血,却也挂着诡异的笑容。那笑容却让麦克维西不寒而栗。他不明白那人为什么直挺挺地冲着自己的枪口走了过来,却高兴得如同在迎接恭候多时的客人。
开枪的声音撕裂了夜晚的宁静,仿佛空气也在振动。麦克维西看到面前的人仿佛没有痛觉一样,脸上依然挂着诡异的笑容,那笑容却在瞬间凝固,同时他胸前的衣襟顿时被鲜血染红。不断扩散的鲜血犹如华丽绽放的花朵,随着那人的身体訇然到底,那鲜花也开遍了他的身旁。
麦克维西迈步走进房间,跨过那人刚刚倒下的身体,来到书桌旁。书桌上放着一摞稿件,他随手翻看了一下,应该是小说或者诗集之类的。打字机里纸张上的文字是俄语,应该就是旁边那摞稿件的俄文翻译。
“穷酸的书呆子!”麦克维西不屑地撇撇嘴,随手将那摞稿件重重地扔回到桌面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克洛伊被关门的声音吵醒时,发现天色已亮。她在椅子里睁开眼睛,同时身边地板上的Honza也抬起头竖起耳朵。克洛伊听出那是对面邻居关门的声音,却不知对方是进门还是刚出门。正在困惑之时,自己家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人探头探脑地向屋内张望。
“您家的房门没关好,克洛伊小姐,”迪米特里笑着说,“就不怕晚上会有什么危险吗?”
“没关系,”克洛伊坐在椅子里笑着说,“我不会介意有人从这门里走进来。”
“也包括我吗?”迪米特里说着,大方地推开门,向房间内迈了一步,笔直地站在门前。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克洛伊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问,“在这个时间出门,而且还……”
“穿成这样!”迪米特里替她把话说完,一边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一身行头。他今天穿了一身整洁的礼服,平日里放荡不羁的头发也被打理得一丝不苟,与之前那个乖戾的邻居判若两人。
“你这是……要去参加谁的葬礼吗?”克洛伊试探着问。
“你为什么不往好的地方想想呢?”迪米特里说,“比如……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在殡仪馆吗?”
“在大酒店,曼德琳东方酒店!”迪米特里兴奋地说,“我要去那里正式上班了!”
“你之前说要去酒店里工作,我还以为……”
“我在说大话吗?”迪米特里再次替她把话说完,“别忘了我可是个有专业知识的高材生!”
“恭喜你!”克洛伊笑着说。
“真的吗?”迪米特里调皮地问,“不怀疑我是在说大话?”
克洛伊微笑着摇摇头:“虽然确实有那么点意外,但真的很为你高兴!”
“你去过曼德琳东方酒店吗?”迪米特里问。
“在老城区吗?”克洛伊猜测说。
“不,在河对岸!”迪米特里说,“既然你连这么有名的地方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跟我去看看?”
克洛伊似乎不相信他在说什么:“现在吗?”
“当然!”迪米特里说,“快点,我上班要迟到了!”
克洛伊本想找个理由拒绝,因为这恐怕是她留在布拉格的最后一天。她不想再让自己多做逗留。但面对毫不知情的邻居的盛情邀请,她突然决定再多待一天。但她还是想找个借口推脱一下:“可是,我没有合适的服装。”
“你的气质不输任何一位欧洲王室成员,”迪米特里说,“所以你还在等什么?”
曼德琳东方酒店由一座建于14世纪的修道院改建而成,也是世界上唯一一间中世纪文艺复兴风格的酒店,坐落于布拉格伏尔塔瓦河左岸的小城区,环境优雅、复古简洁。修道院主体建筑呈乳白色,有着橘红色的楼顶,和一座绿草如茵的僻静庭院。修道院紧邻河畔,墙外古树环绕,附近景色优美,实属休闲静养的好去处。克洛伊跟随迪米特里来到酒店内部,在大厅内落座。迪米特里实习期间暂时在总台做接待员,初来乍到的他工作起来似乎毫不生疏,上手很快,竟然做得有模有样。克洛伊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看了看彩色的宣传页,饶有兴趣地了解了一下酒店的历史,随后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本英文版的《道林·格雷的画像》,独自一人安静阅读。她偶尔会从书本上抬起头,看一眼认真工作的迪米特里,这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竟然洗脱了往日的幼稚与轻狂,举止大方、言辞得体,待人礼貌真诚,看上去非常适合这样的工作。克洛伊也很欣慰,如果他能就此融入社会,成为有用之才,何尝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好事。因此克洛伊这天的心情格外平静,手中的书不知不觉已经看了大半。午后酒店内客人渐少,大厅里也安静了许多,克洛伊沉浸在书中,看到了解道林底细的人相继死去,但挂在阁楼里的画像却常常让道林想起自己所犯下的种种罪恶。他终于承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最终对着自己的画像举起了那把曾经杀死过画家的刀……正看到关键的情节,克洛伊几乎没注意有一个人在自己身边坐下,手机还拿着一张酒店的宣传页。但不出片刻,她突然感觉到一阵寒意,这才意识到身边定有什么异常。但她并未转头去看坐在旁边的人,而是用余光看到那人正在翻看手中的宣传页。“中世纪修道院,果然是个古香古色的好地方。”那人似是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跟她说话。
克洛伊噤口不言,因为她知道来者不善。旁边的人却悠然自得,一边不经意地打量着大厅内的古朴的装潢风格:“你究竟还是来了,毕竟这里的美总能令人神往!”
克洛伊心中一惊,她转头去看旁边的人,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与其有过一面之缘,在几年前,很远的地方。虽然这些年她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但只要是有过短暂接触之人,她都能记住。但她清楚地知道,眼前这个人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用这种方式跟自己说话。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心头,同时伴随着惋惜与哀伤,以为她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来这里不想连累任何人,”克洛伊低声问,“你把他怎么了?”
那人微微一笑,看似友善却令人不寒而栗:“人各有命,苍生如芥,我们无需心怀悲悯。”
“我和你不一样!”克洛伊反驳到。
那人付之一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没有变。”
“拜你所赐!”克洛伊毫不客气地说。
“这些年来,你所做的事情与使命背道而驰。”
“那只是你所谓的使命,我的正与你相反!”
“但结果是一样的,”那人说,“你以为你们始终与世无争,就不会有人因此付出代价?”
“我们?”克洛伊颇为不解,“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牵扯到任何人!”
旁边的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似乎在讥嘲她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但他未再多言,而是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悠闲地转身走开了。
克洛伊心绪忐忑不安,她合上书本默然起身,匆匆离开了这座古老的酒店。
迪米特里在柜台后面忙得不亦乐乎,却也会不时偷空看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克洛伊,只要有她在,哪怕只是坐在那里低头看书,他也会觉得精神抖擞,做起事来心情愉悦。所以当他再次抬头,却猛然发现原本坐在那里的人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不见,不禁有些失落,心想下班后一定要找到她问问为什么扔下自己不管。然而就在他深夜下班,准备直接回家的时候,走出酒店却突然在空旷的街道上被人拦住。迪米特里步履匆匆,刚要横穿公路的时候却突然被人叫住。他茫然转头,却发现是一名自己认识却根本不熟悉的女子。
“这么着急走,是要去找她吗?”女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她一头金色的长发,身穿方领的毛尼大衣,面色白皙、神情冷峻。迪米特里记得她叫贝拉特里克斯,是“组织”里的成员,与自己是“同类”,却又完全不是一路人。
“你在这里有何贵干?”迪米特里不解地问。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贝拉特里克斯说,“你要搞清楚,你知道她是什么吗?”
“难不成是狼人?”迪米特里打诨说,“她只是养了一只狗而已!”
“你知道她不是人!”贝拉特里克斯严肃地说。
“我们也不是!”迪米特里说。
“可她跟我们不一样!一旦与她有瓜葛,对你、对我们都没好处!”
“这么紧张干嘛?我们又不是一伙的!”
“可你这样下去会连累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之间有关系吗?”迪米特里毫不客气地看着她说,“那为什么我母亲被害死的时候,你们却都坐视不管?”
“我是在警告你,”贝拉特里克斯也不示弱地盯着他,“你做的事情她不是毫无察觉!”
“我正在洗心革面,”迪米特里说,“与你们彻底脱离关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你们,就继续躲在黑暗里,见不得光!”
“你以为之前做过的能就此隐瞒吗?”贝拉特里克斯说,“你不可能隐藏自己的本性!”
“但终究还是会有所改变。”说完这句话,迪米特里随即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