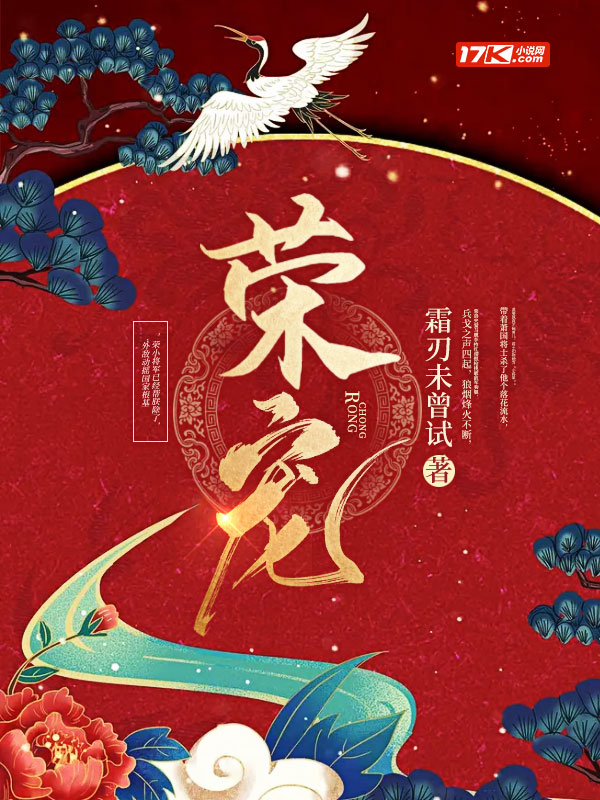回到租住的破旧公寓,维克多几乎彻夜未眠。一方面他为自己害人家摔伤感到愧疚不已,但另一方面才是更主要的原因——那名女子悦耳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闭上眼睛,眼前都是她贝雷帽下那双清澈透明的大眼睛,闪烁灵动犹如湖面上麟麟的波光。即使他一再告诫自己不应该总想着人家,毕竟自己是个罪人,没资格奢望什么,但那名短暂相处的女子的音容笑貌就像印刻在自己脑子里一样,任凭他怎样辗转反侧都无济于事。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维克多其实刚睡下,但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令他瞬间清醒睡意全无——那名女子昨晚摔伤了,那她今天该怎么出门?她昨天那么晚才独自骑车回家,肯定是刚下班,那她这几天该怎么去上班呢?这一想法促使维克多立即翻身下床穿上衣服,想开门走出去的时候却又犹豫了——自己到底是否有资格去帮助她,又是否该去如此冒昧地打扰人家?这些想法让他的头脑很凌乱,但身体却很干脆,他发现自己已经关门的时候,两脚已经迫不及待开始下楼了。
冬日的早晨寒峭清冷,维克多跺着脚在女子家门对面等了半个时辰,终于才看见门开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秃顶男子推着自行车从里面出来,后面跟着一瘸一拐的女孩,正是昨晚那名在雪地上摔伤的女子。
维克多用了一秒钟的时间给自己鼓气,然后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女子见了他便开心地笑了,推车子的男人板着一张脸看着他:“这就是那个害你摔断脚踝的外地人?”
“只是扭伤了,爸爸,”女子笑着说,“这不能怪他,是他把我送回来的。”
“谁知道他是不是别有用心呢!”那位父亲的眼神依旧严厉,似乎断定对方有罪过。
“对不起,小姐,”维克多鼓起勇气说,“不知我可否送您去上班?”
那位父亲一听这显然不乐意了,刚要瞪着眼睛疏落他,却被女儿柔和的声音抢先说到:“奶奶不是让您去买黄油吗?而且您看,我就要迟到了。”
那位秃顶的父亲一看拗不过自己的女儿,只得无奈妥协,气呼呼地支起车撑,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这个抢了他女儿的年轻人,攥着拳头转身走开了。
“那么这位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见维克多依旧满怀歉意地看着自己父亲的背影,女子提醒到。
“哦,当然!”维克多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抬起车撑,扶稳车把,待女子在后面坐稳了,便蹬着车子上路了。
来到女子工作的地方,维克多才知道她是一名初中老师。女子谢过他,让他骑着自己的车子去上班,结果维克多只是将自行车交给她,便头也不回地转身跑开了。因为他害怕,害怕自己多停留一刻,便再也挪不动脚步。
这天上班的时候他工作跟认真,下班后几乎第一个跑出工厂,马不停蹄地向女子的学校跑去。已经放学有段时间了,好在老师们留下来批改作业,所以维克多赶到的时候刚好看到那名女子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旁边另一名女教师帮她推着车子。
“我说过他会来吧!”旁边的女老师笑着说,显然是打赌赌赢了。
他负责来接的那名女子也笑了,笑容似乎带着点羞涩,却再一次惹得维克多不敢去看。
“谢谢您,请给我吧。”维克多接过自行车,推了几步停在女子跟前,等待她坐上去。女子的脚踝虽然有伤,身体却很轻盈,偏身坐上去的时候丝毫不显笨重。维克多骑车将她载回家。亦是在家门口撂下车子就想走。“等等,”女子却突然叫住他,“您这样帮助我,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
维克多停下脚步却犹豫了,不想说出名字。
“你不需要知道!”一个严肃的声音从门内传出来,接着门被“呼”地一下打开,果然又是那位气呼呼的父亲,瞪着眼睛,嘴上的八字胡都气歪了,手里好像该拿着甚么东西,“如果明天再让我看见你,我的藤拍就能派上用场了!”
维克多本想说句什么让这位长辈消消气,话到嘴边脚却先怂了,于是再一次灰溜溜地跑开。
第三天维克多照常来到女子的家门口,照样是站在对面等了一会儿,这次开门推着车子出来的却是女子本人,但她的父亲就站在后面,手里依旧拿着那支偏大号的藤拍。
“这位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维克多再次鼓起勇气走上前去,随即转过身将自己的腰背送给对方,“您请便。”维克多站稳身子,等来的却是“砰”地一下重重的关门声。转过身后,他发现女子正有些感动地看着自己,但他没有回应对方的目光,也没说什么,而是默默地接过车子,示意女子坐上。
路上两人彼此不语,只有转动的车轮声打破沉默。身后的女子轻轻抓住他的衣服,这一举动却让维克多骑得更快了。到了学校门口,维克多还是一言不发地将车子交给对方,转身欲走的时候,女子却开口了。
“我叫西蒙娜,”她说,“西蒙娜·特拉维斯。”
维克多停下脚步,他知道此时若再不自报家名,就太没礼貌了。
“维克多·马洛尔,”说着他转过身,第一次勇敢地看向对方的目光,“非常抱歉害您受伤。”
“这不是您的错,”西蒙娜摇摇头说,“是我应该感谢您每天这样帮助我。”
“这是我的荣幸,特拉维斯小姐。”说完这句话,维克多便转身离开了。
晚上下班后维克多照常跑到学校门口等待,然后骑车送西蒙娜回家。两人站在家门口洁白的雪地上,西蒙娜踮起脚尖想要亲吻他的脸颊,不料此时门却“砰”地一声打开了,“你的嘴唇若蹭上他的脏脸,我就打断他的腿!”
又是那位火冒三丈的父亲。
“抱歉,特拉维斯先生。”维克多向他点头致意,一句话却激起了对方更大的怒火。
“你已经把名字告诉给他了,”特拉维斯先生眼睛瞪得像核桃,“这下他就更难甩掉啦!”
“爸爸,您在说什么!”西蒙娜无奈地将自己的父亲推进门,随后给了维克多一个抱歉的眼神。
维克多却觉得心都要融化了。
第四天、第五天,维克多一如既往。他甚至很快便摸清了西蒙娜的出门时间,尽管没有手表,却能每天按时出现在对方家或者学校门口。即使刮风、下雪、路滑,维克多依旧风雪无阻,每天起床后快步走到西蒙娜家门口,送她去上班,然后跑去自己工厂上班,下班后快步跑去学校门口接上她,载她回家,然后步行走回自己的公寓。每次站在她家门口,虽然还能时不时地看到门内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却再没有人走出门外数落他。他们在路上的时候,西蒙娜总会说一些有趣的事,学校里哪个学生又调皮了,哪个老师又气坏了,甚至不时调侃一下自己的父亲,说他虽然看上去很严厉,却也是个听话的孩子,就像学校里很多小孩子一样。有一次,父亲因为在门口与邻居发生了口角,被个子矮小的奶奶薅着衣领揪进屋里用藤拍追着打,还被迫一定要跟邻居道歉。自那之后,父亲就恨上了那支藤拍,好几次都想扔进炉膛里烧掉。“没想到后来却被他自己拿在手里!”西蒙娜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维克多无声微笑,也不说话,只是静静聆听着身后传来的清脆笑声,感觉无比悦耳。
就这样很快到了圣诞节,西蒙娜的脚踝也逐渐好转,已经可以慢慢走路了。圣诞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维克多像往常一样将西蒙娜送回家,两人却在家门口陷入了沉默。
“特拉维斯小姐……”维克多尝试着说出自己思索已久的话,“过了假期,您的脚踝应该就能痊愈了,我……我看我就没必要再……”
“所以,我们就要就此说再见了吗?”西蒙娜看着他问。
维克多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尝试着岔开话题:“车闸有点松了,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找个时间去修一下吧……”
其实,他想说的是“忘了我吧”。
平日里开朗活泼的西蒙娜此时却无言以对,她只是低下头,轻轻托起维克多的一只手,抚摸着它残缺的手指,然后轻吻他的手背。
她的这一举动让维克多猛然想起了自己断指的原因,想起自己立下的誓言。一阵难以明说的酸楚突然涌上心头,促使他快速抽回自己的手,随即头也不回地转身大步走开,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走在回公寓的路上他泪流满面,脸上的泪水被夜里的寒风一吹立即变得冰冷刺骨,如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他必须承认自己已经爱上了西蒙娜·特拉维斯,她犹如黑夜中一颗闪亮的星、寒冬里一抹温暖的阳光,照亮了裹挟他已久的黑暗阴霾;但他也必须铭记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他害死了自己的父亲,余生必将像饿鬼一样苟活!
可是怎么办?他的心此时在滴血,一边是对心爱之人的依恋,一边是对逝去亲人的愧疚,以及对自己无法释怀的怨恨!
“忘了吧,这就是对你的惩罚!”维克多在心里对自己说,“越是渴望的就越不能奢求,因为你不配拥有这世上哪怕一丁点美好,而她,她的完美更是你无权奢望的!”
于是从那天开始,维克多又将自己重新推入了泥潭。而且比以前更痛苦的是,他曾经游上水面呼吸了一口甜美的空气,再次沉入泥泞感到的是比之前更痛苦的窒息。
他只有每天拼命地埋头工作,将所有的力气全部消耗殆尽,或许就没那么痛苦了。但仍然心如刀绞。而每逢节日,更是各种痛苦的催化剂。圣诞节前夜那天,维克多下班后简直不想回公寓。因为他知道那里会像一只黑洞洞的巨嘴,顷刻间就能将他吞噬。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惧怕孤独的黑暗。而且回公寓的路上同样也是煎熬。大街小巷处处张灯结彩,目及之处皆是一片欢快的氛围,路过的每一座房子、每一处庭院都会有欢声笑语传来,而这一切,无一不是能将他淹没到窒息的潮水!
那天晚上,他允许自己热泪盈眶,允许自己将积压在内心深处的苦闷与悔恨彻底宣泄,允许自己走在铺满积雪的石板路上,听着自己灵魂碎裂的声音,任凭无尽的悲伤将其彻底冻结!
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维克多脚步机械地走过一个路口,却顿时愣在原地。因为他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幻象——他看到昏黄的路灯将积雪照亮,柔和的光晕中,西蒙娜·特拉维斯站在灯光下,如同雪夜中自带光芒的美丽天使,突然降临在他的面前!维克多被这美妙的幻象吸引,情不自禁地挪动脚步慢慢走近,却猛然发现那不是幻觉。因为他看到西蒙娜在雪地中跺着脚,脸颊已经冻得苍白,睫毛上甚至凝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我不顾父亲反对执意跑了出来,”西蒙娜看着他说,“这是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我想你应该会路过这里。”
维克多走到她的面前,西蒙娜抬手帮他拭去脸上的泪水,刚碰到他的脸颊却欲缩回。“对不起,我的手太凉了……”
没等她说完,维克多就用双手握住她冰凉的手指,放进自己的衣领捂暖。
“什么样的人会在平安夜独自徘徊泪流满面?”西蒙娜看着他的眼睛问。
“内心永远无法得到平静的罪人。”维克多说。
“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要这样惩罚自己?”
“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离开却无能为力,”维克多流着眼泪说,“是我身上的厄运带走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我是恶魔,所以要远离所有心爱之人(包括你)。”他没有说出最后几个字,但西蒙娜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我刚刚出生的那一刻,我母亲就因难产去世了。”她说,“我的父亲悲痛欲绝,却从未因此而憎恨我。‘我爱你的母亲,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但那不是你的错。’”西蒙娜靠近他的面前,凝视他的双眼,“那不是你的错!”她重复到,这句话却是对维克多说的。
维克多看着她清澈的双眼,她的晶莹瞳孔仿佛能融化人们心中积累的厚厚冰雪。
“如果你依然深爱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就将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吧。”西蒙娜继续说,“如果离开的人已经无法挽回,那就去拯救更多还在活着的人,包括你自己。我相信这才是他们在天之灵更愿意看到的!”
维克多将西蒙娜送回去的时候依旧沉默不语。到了家门口,发现门开着,特拉维斯先生站在门内,似乎已经等了许久。见两人结伴回来,他闷不吭声,只是板着一张脸,一把拉起自己女儿的手腕,顺势就要往屋里走。
西蒙娜回头看着维克多,看着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向自己露出苍白的微笑。就在即将走进屋门的时候,西蒙娜突然一把挣开父亲的手,转身向路边跑去。身后的特拉维斯先生无奈地关上了屋门。她像只雪地中的小鹿一样欢快地跑到维克多跟前,踮起脚尖亲吻了他的脸颊,并在他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令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你已经拯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