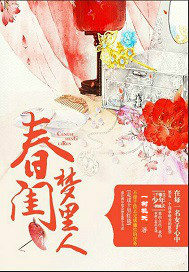这样过了大半个月,连闻笛的脸色都一日差过一日,时不时的在方静秋耳边念叨,要她去军营将参日接回来。方静秋拿剪刀剪去荼蘼长得不规整的枝叶,“他如今正在气头上,我能劝得回来?退一步说,就算我能将他劝回来,他就一定能消了气?”
“王妃!”闻笛却是急了,神色忿忿:“闻笛觉得你对王爷太苛刻了些。你看三年来王爷做什么不是为了你好为了你欢心,你倒好,总是作出这么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闻笛看着都觉得寡然无味。哪像从前在皇城,喜怒哀乐都可以挂在脸上……”试探的看着方静秋,闻笛迟疑道:“王妃……是不是想回皇城?”
方静秋却只舀了一瓢水去浇那荼蘼。
“王妃还想着报仇的事情?”许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闻笛抖了一抖,“王妃想念皇城的原因,不是报仇吧!”
“闻笛,”方静秋警告道:“奶娘临终前曾嘱托我给你找一户好人家,你看你现在这年纪,是不是该出嫁了?”
“闻笛该死!”顷刻之间,闻笛双膝一弯便跪了下去:“我保证以后再不会说这样的昏话了!”
“明白就好。”方静秋放下盛水的葫芦,上下打量了闻笛两眼:“如你所说,王爷这一个月都不会在府里,可你还是穿着王爷最喜欢的紫色衣裳。你真以为,你的那些小心思没人能看出来。我不挑明,是还顾念着你我之间的情分,是想着当年对奶娘做过的承诺。王爷是世间少有的好男儿,你倾慕于他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你若想要成为王爷的枕边人,就自己去讨王爷的欢心,我这里,是不会给你铺路的。”
“王妃!”闻笛脸上的表情有些魔障:“谢王妃!”
闻笛在当晚消失不见,只托水墨留了句话给方静秋,说她要去陪自己的心上人。方静秋听了只抿唇一笑,吩咐水墨道:“既然如此,以后便由你来负责我的汤药吧。”
“王妃稍待。”水墨行礼退下。
其实水墨这姑娘不错,方静秋想。虽然她那一张脸总是板着,严严肃肃的样子很难让人觉得有趣亲和力,但是做起事来一直很靠谱。更重要的是,她是个有分寸的人,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还剩五天。参日说好的一个月,还剩五天便过去了。自成婚后,她还从来没有和参日分开那么久过。从前参日也会去边关巡防,也去四方城操练军队,只是从来没有丢下过她。
军队里有严禁女眷的规定,他每次带她去军营里,都会叫她女扮男装。她还记得自己第一回穿上男儿盔甲时,四方城外草原辽阔一望无际。她抬起头,天上星光闪烁,而她在星芒的交错里看到了两个人擦肩而过。在高高远远的夜空,在本该只有星芒的夜空,她却看见了两个人。一个俊逸清雅,一个邪美不羁,一个是她爱的人,一个是爱她的人。
那是第一次,她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流动着的,是占星一族的血脉。也是第一次,她感受到占星族的悲哀。命运可以被预料,结局却不能被更改,就算知道走下去会是万劫不复,却停不下前进的脚步。这,就是她方静秋,作为沉日大陆上最后一个占星师的悲哀。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那两颗映出两人容颜的星子,正是参商两星宿。那也是她最终放弃利用参日来报仇的原因——结果的惨烈已被预知,再去设计则过于残忍。更何况,她并没有那么恨奈涅,只是为人子女的责任感所驱使,叫她不得不想要复仇。
参日的军队叫静王军。方静秋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她与参日共乘一骑。白马停在草甸上,而参日一手拉着缰绳挽着她,一手指着四方城下的千军万马:“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们改名静王军吗?”
“大概是你太喜欢我了,想要把自己的封号改成静字吧?”方静秋玩笑道。
“我还真有这么想过。”参日笑:“其实我以前总是觉得练兵除了打发时间之外没什么好有用的。可是有了你之后,我忽然觉得,有一支军队挺不错的。”
“嗯?”方静秋不解。
“有了军队,就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守护不了你了。”他将头埋在她的颈间:“就让我藩地十万好儿郎,为你守一世平稳安康。”
还有五日,方静秋喝下水墨送上来的药,洗漱一番便沉沉睡去。
是谁的血流得那样多?是谁的心跳得那样快?是谁的眼里无尽眷念痴缠,又是谁终于放下偏见,终愿与他执手,把酒言欢?方静秋在半夜惊醒,她的梦看着倒是绮丽无比,底色却是阴沉沉的暗红。整个画面更像是漂浮在水面上,朦朦胧胧的,竟叫她看不清那个与她同行的人,究竟是谁。
拍了拍胸口,闷闷的。然而不待她再次睡下,院子里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随着一声声吵嚷,门外亮起光,连水墨的声音都有些慌张,伴着叩门声响起:“王妃!王妃!”
她急忙穿好衣裳,快速将披散的头发用两根素银簪子固定好,方应道:“什么事?”
打开房门,她愣了愣,看着人群中间怒气冲冲地敦和太后,迟疑行礼李:“母妃深夜来访,是有要事吧?”打量了一干人,她退了一步:“更深露重,母妃请进屋说话。”
“还有什么好说的?”敦和太后一眼剜过来,“闻喜翁主,我儿今日落入如此境地,全拜你所赐!”言罢,一张素帛被扔在了方静秋脸上。
方静秋不明所以地捡起素帛走到烛台边,待看清上面的字眼,脸色也是为之一变:“消息可当真?”
“凤华的消息不会有错?!”敦和冷冷一笑,“更何况,上头还有你那不安分的丫鬟的手书。”
方静秋却拨开人群跑了出去。敦和忙忙叫住她:“你要到哪儿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绢帛只说他在战斗中误入敌阵不见踪影不是么?”方静秋停了停,又转向水墨:“去收几件厚衣服,带些止血的膏药送到宫门口!”
藩王宫门口灯火通明,方静秋远远望见了停在宫门处的马车。嘴角牵出一抹冷笑,有些失望但并不觉得有什么好伤心的。身着盔甲的副将站在马车前,神色肃穆。方静秋带着笑走近了些,觑眼打量面前约莫四十五六的副将蔡宗。瞧了片刻,她忽地脸色大变,厉声道:“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蔡将军,如今你来报说是凯旋而归。你的将军呢?”
“王妃……”蔡宗行军二十余年,亦是看惯了生死离别:“王妃节哀?”
“节哀?”方静秋不怒反笑,上前揭开马车的帘子,里头空无一人,只有一套被血染红的护身软甲。眸光暗了暗,她回过头,眼神凌厉:“本宫问的是,你的将军现在何处?”
“王爷……”蔡宗跪倒在地,英挺的脊梁第一次弯了下去:“末将护驾不力,请王妃责罚!”
“王妃!”红衣的凤华从马车背后闪出来,目光钝钝的:“你是想要王爷不得安宁吗?王爷在哪里?呵呵,王爷在哪里!你惹得他离宫巡边陷入敌阵身亡,却做出这个样子来质问蔡将军,王妃——或者凤华该称你一声尊贵的闻喜翁主。你害死了自己的夫君,就不觉得羞耻吗?”
方静秋无奈叹了口气,向着马车后头望了一眼,唤道:“闻笛,你也觉得,王爷死了么?”
闻笛低声抽泣着:“王妃,那件护身软甲,错不了的!”
水墨抱了包袱跑出来,方静秋提着包袱,一步跨坐在蔡宗的黑色骏马身上。她居高临下睥睨着蔡宗:“你们在何处找到了那件软甲?”
“四方城西北向三十里处……”话音尚未落下,只听得马鞭掠空的声响,骏马一声长鸣,撒着蹄子一溜烟儿跑出老远。留下一干守着软甲当参日遗体的人愣在原地。
藩地并不大,本就处在大庆的边陲地带。草原的夜风刀子般锋利,她出来得太急,身上穿得并不多。加上身下的马赶得飞快,更是让风来得猛烈。一双手在夜色之中渐渐冰冷,甚至有些僵硬。待到第二日,遥远的天际显出熹微晨光,四方城城墙上旌旗飞扬,她发上覆着一层蒙蒙雾气,翻身下马的动作都做得有些艰难。
脚刚落地的时候还有些站立不稳,扶着同样疲惫不堪的马站稳了,她动了动脚,径自走向城门口的士兵。士兵拔剑便拦,方静秋只拿出奈涅当日赐下的明黄圣旨:“闻喜翁主。去牵一匹好马过来。”
士兵上前看了看,又摇摇头,方才战战兢兢跑开,边跑边招呼着一边的几人。等到方静秋的手脚渐渐恢复正常,那士兵方才牵了马出来,手里拿着两个白面馒头:“王妃星夜兼程,军中也没什么好吃的,这……”
方静秋牵过马,犹豫片刻接过馒头,“我会记得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