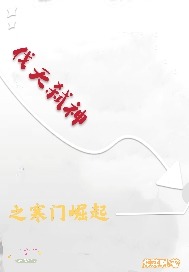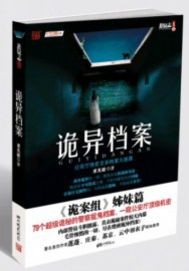“十八岁那年,我也曾对李君同用情。”林月见似是想起了什么久远而美好的事情,脸上的笑像三四月份的嫣然桃花,唇角间更是挽着温柔幅度,就像那一年,苏以归牵着她站在弯弯小河边,为她擦净额畔的细密汗珠。
“可惜后来,我将他的连绵情意忘了个干净。”她又说,面上晦明一片,叫人看不出半点儿喜悲。
而我透过她那近乎喟叹的声音,以及那方手帕上方飘起的袅袅轻烟,看到一个被时光掩埋三十年的故事的原本面貌——那是,李君同一直想说却又不愿说的,属于男子的坚持。
他将他的所有坚持,都附在了这首诗上。桃花依旧笑春风,他的心思如同柏城的桃花,一时零落,便是半生辗转天涯。
李君同原是对林月见一往情深,鲁国合谷宴,他遭人落井下石,是林月见出手相助,朱唇轻启间为他解了围。他一直记着这份恩情,并一直由着这份恩情,在时光的细细碾磨间变作男子对女子的倾慕。
时光转回到楚国先帝二十六年,一封诏书随着锦衣郎由北到南,辗转抵达苏以归的小小庭院。八年了,因左右相党派之争而遭受牵连的苏家,终于得以沉冤昭雪,回归世家本位。
苏以归收到诏书后并未表现出多余的心思,白日里陪着林月见填词写画,夜间却频频往李君同的府上跑。李君同乃是朝堂之上的后起之秀,眼下看着虽只是小小一个柏城的地方官,但依皇城那位圣主时不时送来的封赏看,这位状元郎的升迁自是指日可待。
苏家衰落日久,苏以归结识虽广,却少有交情至深之人——李君同,能算得了其中之一。苏以归要他在秋季的“集贤令”下发至柏城之时,填上他的名字。为此,他愿答应他任何条件。
李君同好看的眉头一挑,手中画扇遮住薄唇:“包括她?”
苏以归垂下眉目,像是不忍,端过桌边那盏没了热气儿的清茶:“你明知她对我……咳咳……”却又像是被茶水呛住了喉,再开口,却是凉凉一句:“也罢,也罢!若是她愿意,我也就随你。”
“你不得不随我。”李君同眼底闪过一丝笑纹,瓦蓝衣衫上的碧竹纹遮着手中握的尺素:“礼部侍郎家的千金,正等着你去迎娶不是么?”
二十六年秋,楚国前君主发出求贤令,要全国二十一州城各自举荐两位德才兼备的能人。柏城李君同举荐的,便是久负盛名却远离朝野的诗词天才苏以归。一时朝野大动,多的是人笑李君同不知好歹,那苏以归多年间从未出仕,又怎会应一个黄毛小儿的举荐?
然而苏以归不仅应了李君同到皇城觐见,更在第二年春日,与礼部侍郎家的千金张玉婉结了百年之好。
那几日苏以归夜不能寐,几番踌躇,也不知要如何将这消息告诉林月见。好歹顶着风流才子的名声,他又怎会不知他那小小徒儿的旖旎心思?只是他要如何开口?如何开口,才能让他的徒儿,不被伤到分毫?
却是他的徒儿千里迢迢赶到皇城的佛衣巷,在他整理婚宴事物的屋子里将他堵住。她仰头看他,一双桃花眼里尽是少女的期盼:“师傅,他们说你要娶亲了,月见不信。你不曾亲口告诉月见,月见不信。”
他指头哆嗦着,指向桌头堆的红烛囍字:“师傅今年已经二十九岁,该有一位贤良淑德的女子做妻子了。”
“月见不行么?”她慌乱放下肩头包袱,从中掏出那件鲜红嫁衣裳:“师傅可还记得当日月见曾说过什么话?”
“不记得。”苏以归答,看见林月见动了动唇想要说些什么,又按捺下心间的不忍,冷冷说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苏以归教出来的徒儿,不该不明事理为所欲为。玉婉贤良,正是我寻了许久的梦中人。至于你,月见,”他看着她,像是看着一场过往,“你将永远是我的徒儿,我此生唯一的徒儿。”
“你曾说你在不会抛下月见!让月见独自一人!”她愤然言道,两行清泪忽然就落了下来,质问一般:“你怎可这般言而无信?”
迷蒙泪眼间李君同疾步而来,额间碎发掺了热汗淋漓,拉了林月见便往外走。林月见唇角忽地绽出清丽笑容,看着李君同,字字句句皆用尽了力气:“你来做什么?”
“我一直跟着你,只是你看不到罢了。”李君同一番踌躇,竟是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弃下柏城政务快马加鞭赶来皇城的缘由。
林月见伸出手堵住他的唇:“你不说我也猜得到。君同,你若真心喜欢我,便在三日内上这苏府娶我。记得,我要一场最风光的婚礼,在苏以归同张千金成亲之前。”轻佻的话语轻佻的语气,偏偏一脸的倨傲。
手中华美嫁衣倏尔落地,林月见径自向前,“师傅,不怪徒儿借你的地方住上一两日吧?”纤纤玉足,就那样毫不经意的,踩过那一件原本捧在手上捧在心上的衣裳。
有些东西,真的会在时间面前乱了分寸,只需片刻,便是人间天上。
他又怎么会不记得呢?夭夭桃花树下,她笑得一脸天真无害:“师傅,若是换做你来娶我,我就答应了。”
三日后李君同果然骑了高头大马来娶她。李家家大业大,经营着楚国最大的钱庄,是以,即便李君同在皇城无基无业,却也拿得出大把银子,为她办一场隆重繁复的婚礼。
那一日皇城铺满十里红妆,百人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热闹了整个佛衣巷。她身上的嫁衣是临时赶制的,比不得前一件精致华美,料子却选用了上好的蜀锦。隐藏在鲜艳红色之下的图案,是戏水鸳鸯。
她就这样嫁给李君同,在皇城里杏花纷扬如雪的季节。她从花轿的间隙间看见道路两旁精心装点的红锦,以及偶尔路过的小姑娘不无艳羡的目光,心里竟觉得静如深潭。
她就这样嫁给他,匆忙地,不甘地,带着自己十七年间从未妥帖安放的心。
她就这样与他分道扬镳,甚至没有好好听他诉一诉苦衷,便将六年的依恋信任粉碎。
就像五年后,李君同一封诀别书送来,她便不动声色地收拾好自己的细软离开李府,眼底连一点眷念都不曾显现。
她在爱的人面前,从来都很坚强。她总是想着,哭这样的东西,偶尔有一次就够了。她应该过得很好,至少,要比抛弃她的那个人过得好。可是人后怎么办?她毕竟只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一场芳心错付,说不难过,无人会信。
李君同喝了许多酒,多到脑子都有些昏沉。这一场婚礼他一直按着司仪的指引行事。宾客散尽之时,他的头脑犹自清醒。他倾慕已久的女子终于嫁给了他,而他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
他寻来一坛好酒,十年的女儿红。他想他须得借着酒气,才敢去面临她。洞房里,那个红妆在身的她。多年前,言笑间护了他周全的她。
时辰早已不是月上柳梢,夜色黑得深沉。李君同跌跌撞撞回到新房,房里的灯却已然被灭了个干净,就连他亲手点上的红烛,都冷着身子在夜里独自寒凉。
喜床旁边,更没有他的新娘端坐的身影。他心中咯噔一声响,唇边一丝薄凉笑意,带着无尽的酸楚与执迷。他爬到床边,借着自窗边照进屋子里的月光将裹着被子紧靠着墙壁的小小身影形看得清楚。
他轻轻掀开被子的一角,能感觉到她用双手紧紧拽着被子不愿让他的动作更近一步,于是顿了动作,改去摸她柔顺的头发:“总有一天,月见,总有一天,你会接受我……”
月尽天明,一夜好似一年光景。林月见就这样成了李君同的妻子,在空有一场豪华讲究的婚礼,却没有任何人真心祝福的情况下。
她将所有的头发高高挽起,三千烦恼丝从此再不会垂在肩头,因为,她是与李君同拜过天地的女子。
她的笑始终寡淡,浅浅的落在唇角,却始终抵不到眼底。李君同陪她三日,三日后,本该是新婚女子归省的日子,她却无处可归——苏府上上下下,都为苏以归的婚事忙得不可开交。
她寂寂坐在李君同租来的小院内,杏花已经落了,一地凋零的花瓣犹自雪白,放佛尘世这一糟来去,不能让它染上半分浊气。
房门忽被推开,李君同小跑着拉过正坐在杏花树下刺绣的林月见,又匆匆将她推出门抱上马背。院里的小童见状,也随着出门,像是要追问些什么。李君同优雅一笑:“今儿个中午,我和夫人都不会回家。”
夫人。林月见第一次听他在别的人面前这样唤她,夫人,这称呼亲昵又庄重,由他唤着,竟有些好听。
李君同扬起马鞭,瓦蓝衣衫与桃色衣裙襟带飘飘,远看近看,都是极般配的一对人儿。
“你要带我到哪儿去?”林月见被李君同护在怀中,小声询问。
李君同却眨了眨眼:“带你旧地重游。”
“皇城不是不许人随意骑马么?你这样,就不怕被巡逻卫发现治你的罪?”
“我家娘子,终于开始担心起夫君了么?”却是他不甚正经的一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