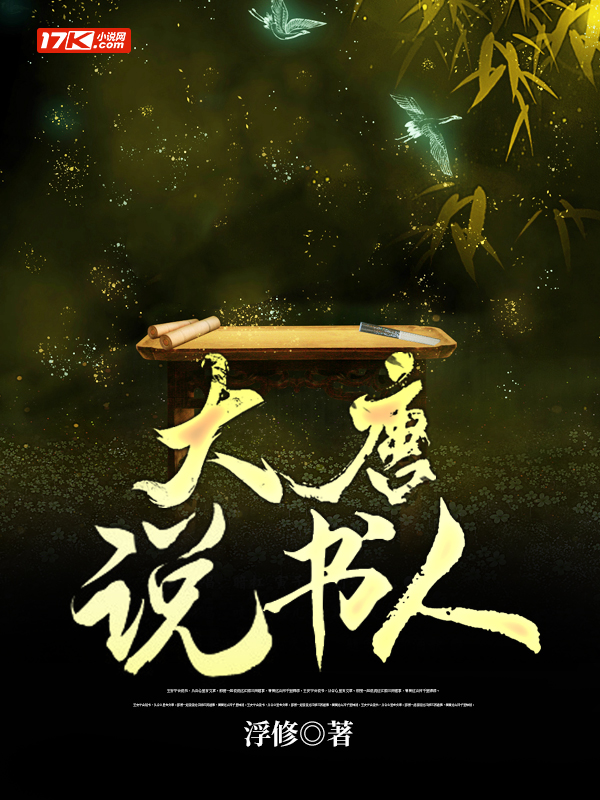洪启年做好饭,盛到碗里,递给老娘嘴边,吹了几口气,想要喂她,却被拒绝了。
她自己端着碗,吃了几口,就放到床上,双手抄起未做好的布鞋,继续做活。
洪启年看在眼里,自己也盛了饭,坐在灶台边连吃三碗,吃的饱饱的,脸色也红润起来。
今晚他要连夜进山,必须要吃饱喝足,养精蓄锐。
寒冬腊月,大雪封山,长白山脉千里蜿蜒,龙蛇裹雪,已变成人类禁区。
但事关老娘性命,纵使是刀山火海,自己也要博命去闯。
洪启年心心念念,把火折子、剜参的小刀、引火干草、麻绳,一股脑塞进布兜子里,放在米缸盖上,又脱下棉袄,露出结结实实一身黑肉。
常年种地,身上也被太阳晒得漆黑似铁,洪启年有些练武的底子,因此这幅身躯虽然精瘦,但一只手举起二百斤的麻袋不在话下。
走出门外,洪启年用堆在院子里的雪揉搓自己的身子,直到把身体搓到发红,激灵灵打了个寒颤,才从门外进来,用毛巾擦干自己的身体。
一切都准备妥当,洪启年就坐在屋子里升起了个火盆,坐在板凳上等着。
过了一会儿,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他穿着大厚棉袄,直鼻紧嘴,颧骨高耸,一脸油灰,正是洪启年的五叔,洪真。
“五叔。”洪启年见到他,脸色一正,喊道。
五叔为人踏实,这些年里多有帮衬,对于洪真的为人,洪启年很信任,把母亲托付给他,也很放心。
“喏,拿着。”洪真提着一串大饼,卷了卷,塞进洪启年棉袄里,热气腾腾的大饼熏得洪启年脸颊发红,身上也热热乎乎的。
“这是五天吃食,五天内要还是没结果,就回来过年吧。”洪真说完,就一屁股坐在灶台前,用烧火棍扒着灶坑里的柴灰。
洪启年感受着胸前的温度,心里一阵感动,又回头看了看老娘,她僵僵的坐在床上,泪眼婆娑,终究叹了口气,就垂下头做鞋了。
“娘,我走了!”洪启年起身把火盆搬到床边,裹了裹棉袄,走出门外。不等风雪卷进屋里,“砰”地关上门,抄起一根搭在窗棂上的哨棒,他就提着哨棒离开了自家小院。
靠水吃水,靠山吃山,这四里八乡的农户不少人都是忙时种地,闲时打猎,因此一直到山脚下,都还有人踩出来的小路。
不过到了山沟,这里的路就已经被大雪覆盖,人站在路的尽头向山脉里望去,只感觉这千里雪山起起伏伏,在夜幕下好像无数头趴伏的巨兽,露出高耸的脊背,时刻准备择人而噬。
腊月二十五,农民洪启年一头扎进芒芒雪山,不见踪迹。
洪启年在山沟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夜,终于觉得一直扎在山沟里走不是办法,目光被四周的山脉遮住,只能凭感觉去找。
于是在天色蒙蒙亮的时候,他决定爬上山顶,按照采参客的习俗,爬到半山腰时候要喊一声“棒槌”,把藏在土里的山参都喊醒,但现在满山是雪,洪启年不敢轻易开嗓,否则引发雪崩,真不是人力能挡的。
等到洪启年爬上山顶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直照的千里山脉银装素裹,曲线如龙蛇蜿蜒,高低起伏处,雪岸接着冰河,河面冻了三尺来厚,底下却仍有鱼儿游动。
大雪终于停了,只见寥廓山河,天苍苍,地茫茫,白色天地间已是人迹全无。
洪启年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只见极远处有一大片银色的山林,在山沟里一直延伸到天边,见不到边缘。
“相传野山参乃是灵气之物,性喜温凉,多数生长在密林里,我先去那树林去找找看。那里挨着河流,水气充沛,植物最喜这样的环境,那山参也说不定就那里生长。”
打定主意,洪启年用麻绳把哨棒绑在背上,从怀里掏出大饼啃了几口,就向密林走去。
在山上望着那密林近在咫尺,但洪启年下了山腰,才明白什么叫望山跑死马,又趟着雪走了一天一夜,才摸到密林边缘。
这时候,天色发青,又像是要下雪的征兆。
白雪极亮,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洪启年眯着眼睛,晃晃悠悠的踩在松软的枯枝上,走了几步,似是累极,就靠着树干坐下来,眼皮半睁半合,走了两天没歇脚,的确是又累又困。
洪启年看到这杉树林里的树都光秃秃的,像是死了,要等到来年开春才能活过来。
打了个哈欠,洪启年抱着哨棒闭上眼睛,准备先打个盹,再细细的在这树林里找参。
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洪启年半睡半醒之间,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从鼻孔里往脑仁里钻。
他正细琢磨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噼啪”一声,那是踩断枯枝的声音,洪启年立马睁开眼皮,明晃晃看到一头黑黄条纹的瘦虎半边身子藏在树后,尾巴拖在地上,两只铜铃大的眼珠子正盯着自己。
洪启年一下清醒过来,猛地从地上弹起,抓起哨棒,看着从硕大虎头吞吐出来的白气,只感觉自己头发都已经根根炸起,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在僵硬,发抖。
洪启年细细打量,那老虎干瘦干瘦的,一定饿了很久,现在大雪封山,山鸡狐狸都稀少,遇到老虎直接钻进雪里,令其捕猎难度几何倍增高。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猎物,这老虎绝对不可能放过自己!
“我总不能像山鸡狐狸钻进雪里逃走吧。”洪启年知道,自己这么大身形,想要效仿白狐入雪逃遁,实在异想天开。
于是他背后靠着冷杉,抓紧了哨棒,把心一横,大声叫喊:“死畜生,还不过来领死!”
这话喊出来是为了壮胆,洪启年喊完,当时就发现自己的身体虽然依旧紧绷,但却没有那么僵硬了,掌心也涌起一股热流,洪启年脸色通红,感觉一身筋骨都热血浇灌,完全活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