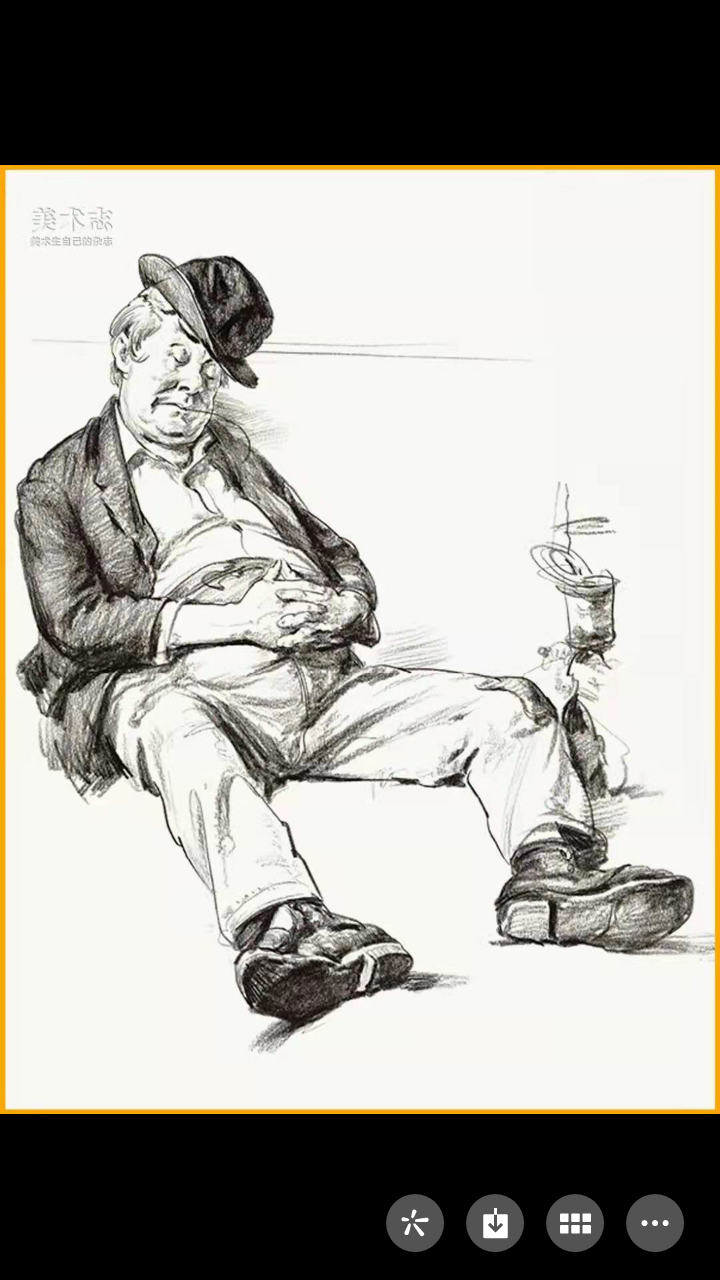大家对于那座山那个洞的猜想与探索从来没有放弃过,但是那山依然寸草不生,那洞依然深邃无比,山上的风依然如呼吸一样来回的刮,而山下这个闭塞的小小村子里的人却是生老病死一代接着一代的传承着。
曾经有人认为这土山是风水绝佳之地,把父母的骨殖葬在此处后辈必能大富大贵,但却被这方面是权威兼专家的爷爷喷了一脸的唾沫,什么样的风水宝地会如此这般的荒芜到以至寸草不生的地步?而且还会有这么个地眼将地气放的干干净净?于是我们全村乃至方圆数十里的人们都深以为然。
站在土山的顶上向四周看,会看到连绵的群山环绕我们的村子,只有一条蜿蜒的路从村东头经过,把我们村跟外面的世界连了起来,村头上的公交车站点儿与我们村隔河相望,河里平日里没有水,只有下了几天透雨后山洪爆发时才有水,
站在土山的顶上向四周看,会看到连绵的群山环绕我们的村子,只有一条蜿蜒的路从村东头经过,把我们村跟外面的世界连了起来,村头上的公交车站点儿与我们村隔河相望,河里平日里没有水,只有下了几天透雨后山洪爆发时才有水,
河上架着一座石桥,据说从秦朝时已经有了,斑驳的石头桥面上不知为什么会有两条深深的车辙,古朴的石头栏杆两头原先刻着两条龙,现在龙头龙爪被人给砸走了,只剩下依稀辨认出大概的龙身,桥向山谷的一面原先还有一块石匾嵌在上面,上面用古篆写了两个不知什么字,也被人抠走了,只剩下一方浅浅的长方形的窟窿。
我小时候经常到那座桥上玩,也会常常爬下桥躺在满是黄沙的松软河床上,仰望着高大的拱形石桥,看着那斑驳满是伤痕的石块,心里会莫名感觉到无比的悲伤,这似乎是一座缺了两扇门的门框,那门框中间的铁锁链还剩下几扣垂在桥梁的中间无风自动。
村里曾经有老人说听他爷爷的爷爷说:那条锁链上原先悬着一把样式古怪的剑,后来被不知哪个文物贩子给偷走了,只剩下挂剑的锁链还悬在那里,对于此我更是嗤之以鼻,谁会闲的没事干挂把剑在那里?那么高怎么挂上去?
我爷爷在我二十岁那年死了,是老死的,无病无灾的人瘦成了一俱骷髅,只有两只眼睛还是那样的空洞与无神,却绝没有正常人应该有的那种对死亡的惧怕,他盯着我,大张着嘴,肥厚的舌头在仿佛用纸糊就的口腔中搅动着,发出嗬嗬的声音,伸出枯枝般的手拽我的衣服,
我把耳朵凑在他嘴边,他费力的喊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就咽了气,我根据对他老人家日常的了解对他那句含浑不清的话做了一番猜测,
他在弥留之际让我等一个叫龙姐的?女人?应该是个女人,男的不应该叫龙哥?
这句象是临终遗言的话让我觉得很纳闷儿,因为我跟他住了二十年,从未听他说过我们有亲戚朋友,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俩个日子过得清贫无比,尽管他有一身算命打卦看风水的绝学在身,尽管有无数人把成捆的人民币摆在他面前,他却极少展现自己的本事,我怀疑如果不是我们同样需要穿衣吃饭睡觉,他会一个人也不接待,就这么甘于贫困下去。
现在他在临闭眼前突然提到了这个叫龙姐的女人,而且是在这里等那个龙姐来,而不是去找,我爷爷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得他曾经跟我提过同治皇帝大婚时的情形,尽管我知道他是在吹牛,但不能否认他的寿命确是悠长无比,那他口中的龙姐会有多大?是否还健在人间?
难道他就不能在身子骨还硬朗的情况下交待一下后事?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爷爷下葬后天就开始下雨,雨并不大,却淅沥淅沥的下个不停,后半夜时,村子远处就会响起一声声“哞哞”的牛叫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象是找不到回家路的老牛一样,声音凄苦而悲凉,不少心存侥幸的人拿着手电披着雨衣在村口四处寻梭希望能够找到那头不知是谁家走丢的牛,结果全部都是一无所获。
雨一直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牛也叫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爷爷烧完七七,八月十五也到了,天空终于放晴了,久违的阳光照在我苍白的脸上让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他娘的,天再不放晴我都要发霉了,我家的门框上都长出黑木耳了你信?
夜里我坐在灶台旁往灶里添着柴,看着金黄色的火舌舔着漆黑的锅底,心里想着自己将来的出路,绝对不能在家里窝着,那个叫龙姐的人不会来了,爷爷除了留下这三间的破瓦房以及那把破旧的摇椅,其它的什么都没留下,老东西空有着一身的本事却并不施展,如今缸里的米面都已经见底了,七七也完了,是不是该走出去见见世面了?
正在胡思乱想间,一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出现的很突然,仿佛凭空出现,又仿佛早就站在那里,一抬腿就跨进门来,这个人很高大,能有多高?他坐在我面前时我仍需抬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他的脸很长,两只金鱼般的大眼睛几乎是长在脑门上,鼻子和脸颊象被人用手上下拉过一般,徧徧又生了一张阔嘴,嘴唇几乎包不住焦黄的大牙齿,就那么呲着,两只小耳朵在脑后不停地抖动着,
“我姓马,就叫马面。”他一边说一边用骨节粗大的手从腰后不知什么地方拽出一根两尺长的烟袋,前面的烟锅足有小孩拳头大小,这样的烟锅我爷爷也有一个,只不过从来都没见他用过,那人用烟锅伸进皮质的烟袋中挖了满满一锅烟丝问我:“你就是这一代的某某?”
我诧异了,而且有些被惊着了,他叫马面不惊奇,因为不光是他的脸,包括他整个脑袋都象极了马头,这样的人无论谁看见都会被联想为阴曹地府里的牛头马面兄弟俩,但这一代的“某某”是什么鬼,难道我爷爷是上一代的“某某”?
难不成这个“某某”两个字代表着的不是一种称呼,而是一个古老的传承?我果然是不同凡响的!就是不知道我的超能力是什么?但爷爷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对我说过啊!我不由开始腹诽起那个死去的老东西,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厉害,偶尔间话多时也多是吹牛说些不见影的古事,到死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遗言,
“你认识我爷爷?”我试探着问,说实话我有些怵眼前这个自称马面的人,并不是因为他长得象极了传说中的牛头马面,而是他身上散发出的一种类似于泥土沤烂般的腐朽气息,就象是被埋了很多年的木材刚出土时的味道,我知道那是一股死气,爷爷死了之后身上散发出来的也是这种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