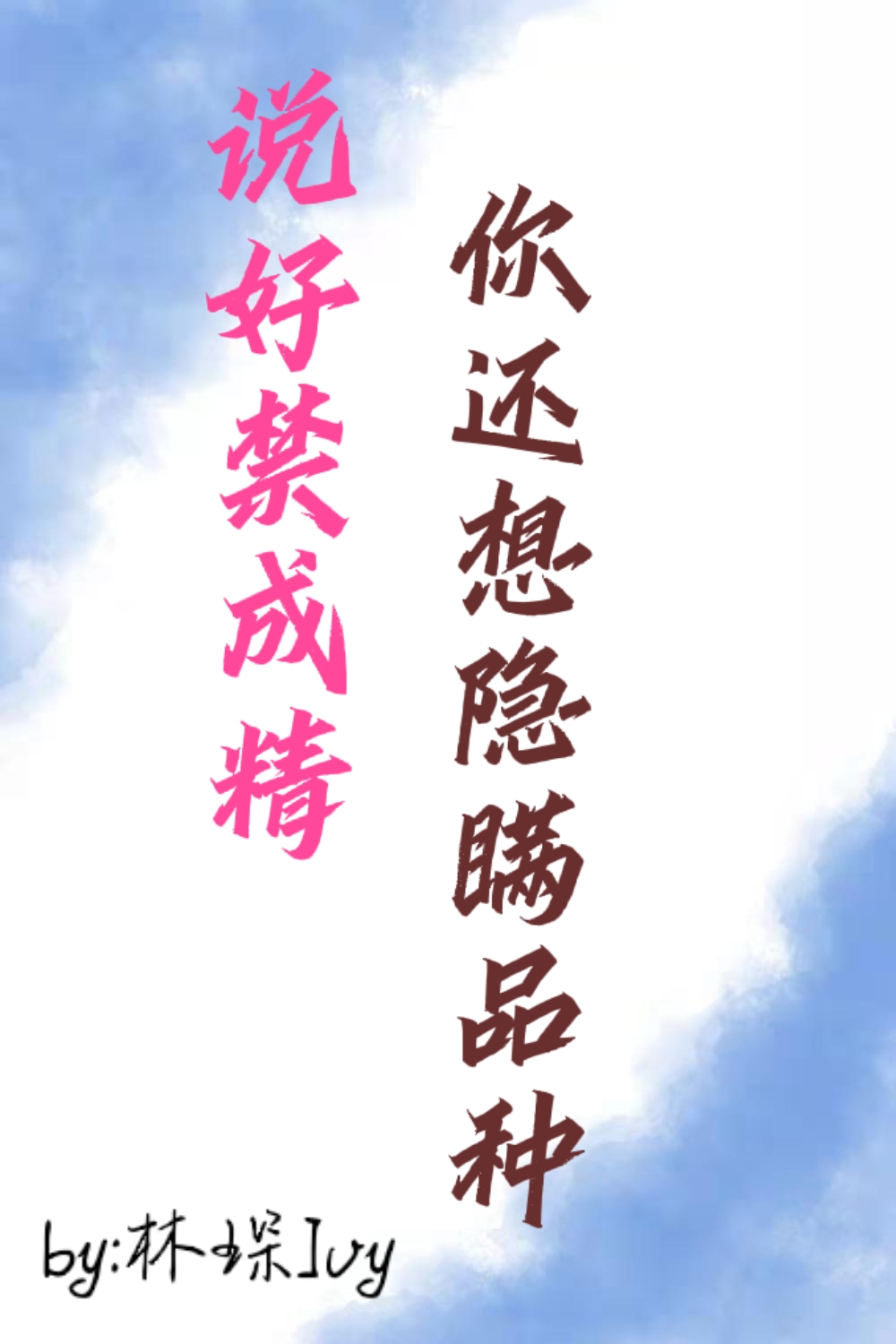虽说耽搁了一会,但李二狗的脚程却远胜往日,到达府衙的时候倒也不晚。
门外聚起了不少人,远胜平日门可罗雀的程度。
最内圈正是金国商队一行人,十几个商人来了大半,其余闲杂人等似乎也是因为商队人多,从众的凑热闹心理导致挤了个水泄不通。
换牛兰珊在前开路,李二狗从商人们身边穿过时特地留意了他们的眼神,本以为会从中读出仇恨等情绪,没想到却是轻松和轻蔑的成分占多些。
心中有些计较,李二狗穿过府衙的外门后就在几名衙役身边站定。
此时与衙役们搭话只会落个官官相护的口实,李二狗自然三缄其口。
倒是几名衙役主动与牛兰珊见礼,因为比起只挂虚名的大皇子,实力与官职并重的七品带刀侍卫才是他们学习的好榜样。
没等多久,从内走出个堂役去门外擂鼓三声,鼓声未平,三班衙役齐声高叫升堂。
只在前世电视剧里见过的场面震得人一阵恍惚,头回来这地方的李二狗有种自己不是穿越到异世界而是穿越回了古华夏的错觉。
在和着威武二字的一阵杀威棒敲击声中,旧都的知府迈步而出,落座后轻拍惊堂木,训练有素的衙役们顿时收了声。
知府没急着开口,反而端起面前备好的热茶轻啜一口,眼神斜瞥身侧的小桌。
一个半老的师爷不知何时悄然出现在座位上,接到自家老爷的眼神暗示,了然老爷还没来得及看今日的卷宗,主动起身朗声叫堂役带原告和被告上堂觐见。
此事倒也常见,毕竟眼下入了秋,正所谓临秋末晚,多事之秋,旧都知府在这胜国首都不算大官,却也实实在在是个京官,着实忙得很。
昨夜卷宗送到时他已经睡下了,没出人命的案子贸然扰人清梦实属大忌。胜王虽然还在城外主持大局,但三省今日仍是主持了早朝,眼下不过是刚下朝的时间。
热乎水刚下肚,堂下就多了四位,两名衙役押着那商队副领队,第四位不是李二狗,而是昨晚那位巡夜的士兵队长。
四人都站得笔挺,无人下跪,这也是胜国的独特风俗了。
跪天跪地跪父母,不必跪官。
若是想跪,也可以,却是只能跪父母官。这一跪,若是被人见了,那被跪的父母官少不了多挨几轮考课,弄不好就要掉脑袋。
师爷先让原告开口,那队长显然是见过大场面的,不急不缓报出自己名叫严宁,昨夜夜巡途中偶遇店小二求助,声称自家店里有人持刀伤人。
自己带队上楼,见房内场面已经得到控制,一人着夜行衣蒙面被另一人持刀控制。遇官兵控制二人都无抵抗。
未蒙面男子腰腹受伤,主诉被袭击,供词与现场情况相符。另一人无异议。
知府听完清清嗓,心里大致有了谱,正打算让被告陈情,没想到师爷主动出声打断道:
“老爷,被告自称口舌不利,请求讼师上堂代审,因被告是金国人士,在旧都并无认识的讼师,请求以商队的领队做其讼师。”
面无表情地听完,知府挥手让衙役传那讼师上堂,在心中不由得暗暗皱眉。
讼师是很讨厌的一种人,不论是从官还是从民的角度。
官讨厌是因为,只要请了讼师,再清楚的案情也要无风起浪,被胡搅蛮缠地拖上一拖。如今日的案子,快些原本没准能赶上今年的秋后问斩。
民讨厌是因为,就算因为讼师侥幸得活,但家底必然是要被刮地三尺。
这次虽然不是专职的讼师,但这样反倒不好办。
讼师?朋友?若是没能刀口夺人,犯人的家属哪管你是朋友还是讼师,责任天然就要分你一份。
商队的那位贾领队从李二狗身侧的角落里走出,气定神闲又胸有成竹,一点也不似要从虎口夺食的样子,引得李二狗微微挑眉。
知府是标准的老城府,不喜归不喜,但面上不动声色,按流程叫问堂下何人。
“草民,贾仁义,是邻国大金的一名商人。被告付贵,是我商队的副领队,不善口舌,请草民代为陈明冤情。”
贾仁义口齿伶俐,一改平日略带的金国口音,流畅又标准的胜国官话甚至带点旧都口音,让知府观感稍有改观。
入室袭击是可以判问斩的大案,但今天就算当堂判个斩立决也免不了递到三省和胜王那复核。平日里要审上五次,哪怕如今入秋也要按流程审上三次。
既然不是一言堂,知府直接示意贾仁义说说那夜发生了什么。
贾仁义敢代人发声自然早已想好说辞,开口道:
“付贵昨天下午从南城的路人处得知有只颇有灵性的猴子在城中逃窜,怀疑是中午我们商队卖给一位顾客的猴子。心生邪念,想抓住猴子去顾客那讹一笔赏钱。”
“根据线索一路追查,最后追至一扇洞开的窗下,利令智昏,想都没想就追了进去,没成想屋中恰巧是中午那位顾客。”
“顾客一见付贵身着黑衣,以为是歹徒,没给付贵解释的机会,直接抄起身边的花瓶打算擒下付贵。”
“付贵见对方有了兵器,又不知对方深浅,只得拔出腰间的短刀防卫。奈何技逊一筹,还是被顾客给制服在地。”
“之后就是严队长来兵控制了二人,就地审讯。不过……”
贾仁义拉长了尾音,斜瞥身旁不为所动的严宁,丝毫没有表演的痕迹,语言动作熟练而流畅,满带怀疑的感觉,接着道:
“严大人似乎与那位顾客认识,殷勤地将其扶到床边坐下,不先问被刀架在脖颈上的付贵,反而先问除了一处小伤绝无性命之忧的顾客。”
“付贵嘴笨,脑子却不算糊涂,一见严大人的表现,害怕对不上口供就要被屈打成招,这人生地不熟的,面对严大人的追问也只好先应下来,等升堂再由我代为分辩。”
说完,长鞠一躬久久不起,姿态做得很足。
牛兰珊原以为今天这会是件铁案,没成想竟出了岔子。
连忙转头想安抚一下李二狗,没成想李二狗被泼了脏水却不为所动。
再看堂内的原告严宁,同样是副木头人的样子,半分急迫也无。
知府反倒是反响最大那个,原以为这讼师只是个会胡搅蛮缠的小贼,没成想还真有些本事,仅听其一家之言并没有大纰漏,当真有些颠倒黑白之能。
轻拍惊堂木让贾仁义起身,知府开口问道:
“严宁,不知你可认同讼师贾仁义所述皆为事实?”
只是去了佩刀,一身外甲都没脱的武夫懒得和高堂之上的文官客套,提出请求却连个拱手也不肯做一个:
“所述基本属实,但仍有些问题,我请求提讯本案另一位当事人。知府大人,有些事不消分说,您只要见到那位当事人就知道了。”
话有些不客气,知府不以为意,也不是新官上任了,在朝堂上和那些武将吵了这么多年,多少习惯了他们的性子。
一个眼神,师爷马上给了反应,善解人意地代老爷说出了另一位当事人的名字:
“传当事人李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