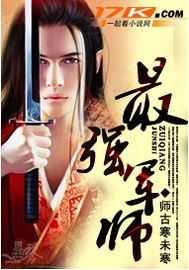自欧阳羽于长安拥立刘昃登基,重建大汉后,这长安城便吸引来一批批各地名望之士,而名士汇聚之地自然是缺不了酒肆人家,若要说这长安城内名声最胜的,便是那浮云楼了。
这浮云楼自前汉朝时便已有了,流传自今已溢百年,其间自是翻新多遍,而便在刘昃长安登基后,这浮云楼便又再次翻新,方才开张,宾客自然盈门。
这一日,刘昃正微服行在这长安大街上,而他身后自是少不了十数个跟班,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刘昃也不在意,此时天景渐寒,刘昃身着大袄,信步而行,不多时竟行至浮云楼前,挥手唤来一个从人,问道:“此浮云楼是什么背景,这寒冬天里生意竟仍是如此火热。”
那从人忙答道:“回公子话,若说这浮云楼可谓是长安城甚至天下酒楼中之翘楚,天下名士或不识文章,却无不知这浮云楼的。”说罢,便将浮云楼一应历史讲与刘昃听,说道这刘昃身旁的从人那欧阳羽亦是费了许多心思,尽是些伶牙俐齿之人,且都通晓数样奇门兵刃,作为随从是再好不过的。
刘昃听罢,奇道:“哦?可如何我来长安数月,竟从未闻浮云楼之名?”那从人忙答道:“公子您自入长安来未尝与闲人交谈,而公子亦未曾与小人等谈论过此等事务,是以不知,此实乃小人等的疏忽,还请公子责罚。”
刘昃哈哈一笑,信步走入浮云楼内,那答话从人见刘昃进去,忙回身对身后其余从人做个手势,只见其余从人纷纷四散离去,想是隐在浮云楼四周了,而那答话从人见众人散去,忙跟随刘昃进去。
刘昃进得楼内,却见一楼四周或三四人,或六七人,不是摇头晃脑诵读文章,便是指指点点畅谈世事,楼内小二见刘昃进来,忙上前问道:“公子是有熟识之人么?”
刘昃听小二过来招呼,答道:“没有,我就一个人。”那小二又问道:“二楼尚余一雅间,公子楼上请。”说罢,便引着刘昃二人往楼上行去。
便在此时,店门又被推开了,只见一人迈步行入,却是那平阴侯杜远阑,店内另一个小二见杜远阑进来,忙上前招呼,仍是先前那小二一般言语,杜远阑亦道自己独自一人,那小二却躬身道:“公子,对不住您了,本店雅间已经满了,请公子稍移尊步,改日再来。”
杜远阑听闻雅间已满,正欲转身离去,却又瞥见刘昃被先前那小二往楼上引去,不由停下脚步,笑道:“无妨无妨,今日正巧,本公子碰上个熟识之人了。”说罢径直向刘昃行去。
杜远阑尚未行至刘昃身后,那从人已自杜远阑脚步声中知晓其是朝着刘昃而来,兀地转身,将杜远阑阻在上二楼的楼梯口前。
刘昃此刻也觉身后动静,回身一看,见是杜远阑,面色一冷,转瞬便又恢复过来,直朝杜远阑行去,并朝那从人使个眼神,令其退开,那从人无法,只得闪身,杜远阑也往楼梯上行去。
“原来是杜兄,相请不如偶遇,杜兄可愿赏脸与小弟共饮数杯?”
杜远阑听罢,忙道:“刘兄您说得哪里话,杜某身份卑微,如何敢与刘兄您同桌共饮!”刘昃上前作势拉杜远阑手臂,笑道:“杜兄此言谬矣,此地乃名士汇聚之所,进得这浮云楼之门,便只在才学上有短长师长之分,何来身份贵贱之说?”说罢,杜远阑顺着刘昃作势所拉方向前行一步,二人并肩往二楼行去。
不多时,二人来至楼上雅间坐定,刘昃吩咐小二去准备酒菜,又把那从人遣出房门,还未与杜远阑寒暄几句,那杜远阑却直道:“久闻刘兄您碧锋玉笔生花,今日巧于这浮云楼上相会,请恕杜某斗胆,向;刘兄您请教则个。”
刘昃心知杜远阑对自己搅闹了他的婚礼心下气愤,今日怕是借讨教之意让自己丢面,却仍是笑道:“杜兄你抬举了,若论文采飞扬,这长安城内又有何人堪比杜兄你呢!”言罢又思道:“前日独孤叔父传来密信,言这杜远阑虽是杜氏叛逆之后,却是个性秉直,若今日能借论文之机,化解我与他二人嫌隙,日后必有借重之时。”
杜远阑亦是笑道:“好!既蒙刘兄不弃,杜某便献丑了。”说罢,环望四周,须知此时已是天寒,这雅间一墙角处栽了几株梅花,正自开放,杜远阑正撇见这梅花,便道:“今日便道一道这冰雪寒梅罢。”
刘昃面带微笑,直道:“还请杜兄出题。”杜远阑道声好,便信口念道:“梅谷行吟香染句。”刘昃略一思索,答道:“杜兄是出了个上联,那我便对‘雪峰望叹愁书独’。”
杜远阑沉吟片刻,便鼓掌道:“好!既如此,便换刘兄先出上联罢。”刘昃便又道:“梅花枝头七分春。”杜远阑听罢,起身踱了几步,便停下脚步答道:“冰雪林中一段香。”
刘昃笑道:“杜兄果然文采敏捷,小弟佩服,还请杜兄再出题。”杜远阑复又坐回座位,心思这刘昃果不负盛名,心下亦生几分钦服之意,只道:“刘兄说的哪里话,那杜某便再以这梅花出一题,说是‘寒梅初发不识雪’。”
刘昃不假思索,直答道:“璞玉未啄穷叹石。”杜远阑听罢大笑,道:“好个‘璞玉未啄穷叹石’,看来刘兄其志不小啊!”刘昃苦笑道:“刘某如今还有何大志,杜兄虽为凉王胞弟,且日前刘某更是曾与杜兄交恶,但刘某今日见过杜兄却若得遇知音,自不敢相瞒。杜兄不见刘某身后跟随的随从么?”
杜远阑神色一怔,起身叹道:“刘兄您视杜某若知音,杜某自非小器之人,日前之事杜某自不再放于心上,何况杜某观刘兄亦是性情中人,只是刘兄您与家兄中间之事系属军国大事,杜某却是不好参与,可若有人欲加害与您,便是家兄与军师之意,杜某亦当竭尽全力以保刘兄周全。”
刘昃听罢大喜,起身上前紧握杜远阑双手,道:“杜兄果真慷慨义气之人。”杜远阑却是大笑道:“那今日你我君臣二人少不得要畅饮千杯了。”说罢,二人齐声大笑,自是一番把酒言欢、笑论诗书不提。
话分两头,另道那山东齐王府内,只见李元和端坐主座,两旁依次站立着齐王府内一班文臣武将,左首第一位站着的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姓李名正典,乃是李元和家族中的长者,早年曾任山东布政使,后来见朝纲昏聩,便辞官隐居乡里,而自李元和受封齐王后,复被李元和请出山,总领山东政务。
只见李正典率先走出道:“齐王,既已决定遣人往长安朝拜新皇,可否定下人选?”李元和笑道:“朝拜新皇并非小事,自得遣一个身份相当之人去,可这齐王府上下我找遍却只有两人合乎标准。”
李正典疑道:“不知齐王所指何人?”李元和道:“并非他人,正是我两个孩儿,天成与天宝。”李正典听罢,忙道:“齐王万万不可,那欧阳羽诡计非常,若使二位少主去只怕遭欧阳羽算计。”
李元和道:“叔父多虑了,我意遣天宝去,一来可以锻炼于他,二来天宝年纪尚轻,待到得长安后必使欧阳羽轻视于他,三来,那欧阳羽当知如今西北看似风光,却是如履薄冰般,稍有不慎便入万劫不复之地,如今之际他自不敢得罪我山东。叔父便安心好了。”
李正典听罢,只得退回去,李元和振声道:“李天宝听令。”只见下首走出一人,正是那李天宝,如今已是十三四年纪,眉宇之间颇有乃父乃兄之风,李天宝站出来道一声:“在。”李天和自桌上取过一纸诏令,道:“封李天宝为朝圣使节,后日出发,朝拜长安新皇。”李天宝上前接过诏令,道声“得令”,便又退回去了。
李元和待得李天宝退回去后,便挥手道:“今日无其他事务,诸位可散去了。”说罢,屋内众人纷纷施礼退出房去,不多时,人已退尽,屋内只剩两人,便是李元和自己与那即墨黄青。
黄青见众人离去,便道:“殿下,果真欲使天宝少主往长安朝圣?”李元和道:“如今那欧阳羽手握雄兵,更有天下大义,且那欧阳羽本便是绝代智慧之士,假以时日,天下诸侯必尊其号令,如今唯有使我至信之人往长安去,明里朝拜新皇,暗里则推波助澜,协助新皇逃离长安。”
黄青苦笑一声,道:“看来殿下又要使我跑一趟远门了。”李元和听罢大笑,道:“黄青你此行可先赴蜀中,与那独孤云协议之后再往长安,届时你只需暗中辅助蜀中势力即可。”
黄青疑道:“可若将刘昃救往蜀中,不是又为我山东增添一敌手么?”李元和笑道:“黄青你有所不知,我儿天成曾与刘昃相交,据天成所言,这刘昃可成天下名士,却难成天下明君,此刻刘昃在西北必是俯首听命于那欧阳羽,可一旦回归蜀中,那独孤一门乃是大汉忠贞之臣,必不敢拂汉皇君意,如此看来,便让那刘昃回归蜀中亦难成大患,况蜀中北有凉州虎视,东有赵氏余荫,南有巴地蛮夷,西有大山阻隔,如此四难之地,又何惧之有?”
黄青听罢,道:“殿下雄略,黄青这便赶赴蜀中。”说罢,转身便离去了。
却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