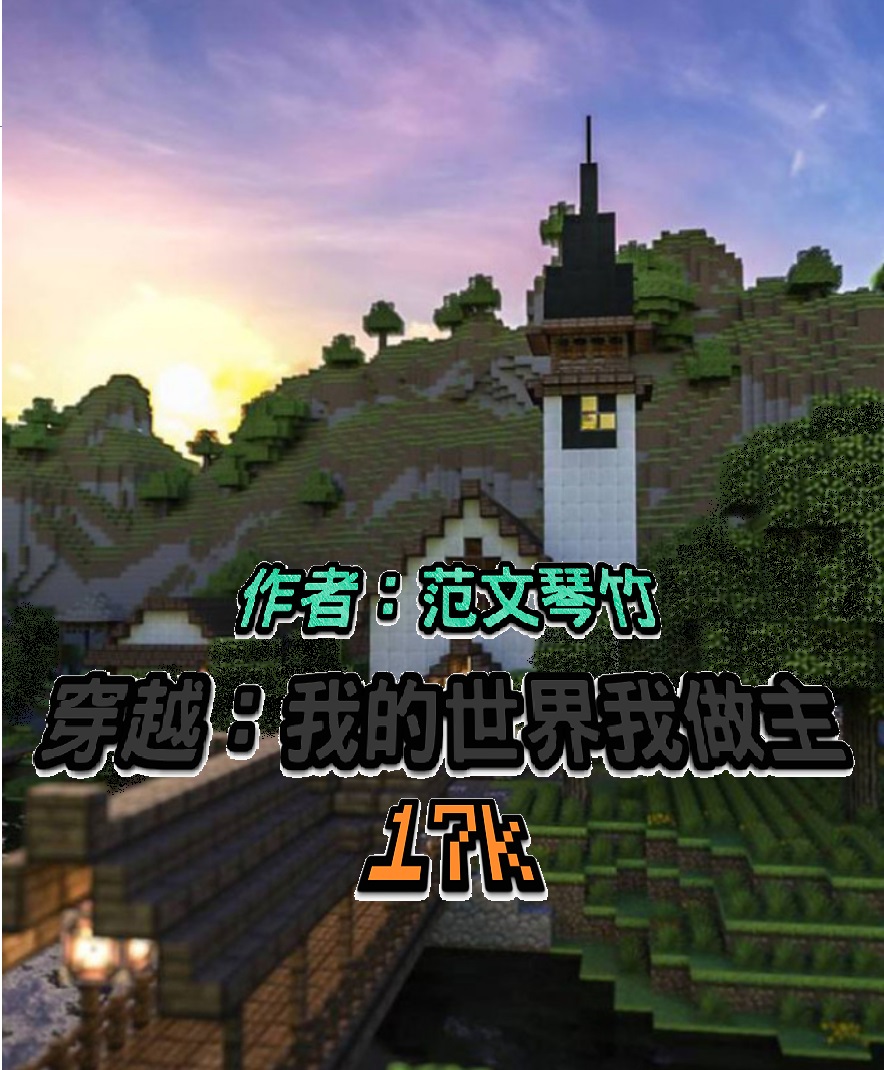老吴来之前最担心的就是鼻血复发,倒不是怂,只是当年留下的阴影太过强烈,还记得当年鼻血流起来的感觉就像没法关紧的水龙头,还记得鼻血滴下去从映射着阳光的鲜亮进入戈壁砂石地变成溅射状的暗红,还记得鼻血流的太多经过嘴唇时咸腥的味道,还记得那时候虽说不怕但是偶然会涌上心头的绝望:“会不会就这样挂在这里了”。老吴没有了兴趣去探究那声音的来源,赶紧抽身往回,加快脚步,迅速回到屋里,掏出装备,干棉球上药,堵住,5分钟止血,清洗,喝水,湿棉球润湿鼻腔,简直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老吴做完这套动作,不禁自我嘲笑:“真是惜命啊”。前后折腾了有四十几分钟,之后躺在被窝里喝着保温杯里热水的老吴又一次迎来了睡意,很快睡着了,这一次,没有再梦见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一直睡到有人叫门:“吴工,吴工,该起床了!”
叫门的是站上的技术员大刘,老吴赶紧一骨碌爬起来,开了门。大刘说,司机和他已经吃过早饭了,等老吴吃完,一起去现场踏勘一下,初步商量一下方案。老吴赶紧洗漱,也没有像在城里家中那样墨迹着先“酝酿”后“解决”,匆匆的吃完馒头咸菜粥,拿了一个鸡蛋,就跟着大刘他们出发了。毕竟自己是乙方,不能让甲方等太久,老吴在这一点上是有自知之明的。
上了车,司机脚踩油门,从大门冲出去,左转再左转,开上了站后头的一条不是特别明显的石子路,路边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标识牌或者小小的指示桩,老吴明白,这是沿着大管道在走。老吴跟大刘他们聊起来昨晚流鼻血和听到奇怪声音的事,大刘和司机都说,刚来站上的人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天气干,风大,容易流鼻血,至于那个声音,他们都猜想是晚上远处那趟火车经过的声音,老吴感觉不像,但又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印象,也就撇过一边不再提了。不知不觉说到这次的任务,老吴问大刘为什么站长不一起去,毕竟可能涉及到不小的投资。大刘呵呵笑了,站长对这样的小事肯定是有个明确的方案以后,才会出面,这个阶段是不会参与的。老吴后来才知道,站长很快就要去管理区升处级干部了,这个时候主要忙的事儿肯定不在于这些事情,而且,越是这个时候,越得谨慎。
车子大约开了30公里,路上还经过了一个跟小站风格差不多,但是要小很多的建筑,只有一间房子大小,外面原处还竖着一跟高高的管子,老刘知道那是用于检修的放空管,自己当年曾经做过设计,但是从来没见过真东西,比想象的要高不少。一直开到路的尽头,车子停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山坡的山脚下,尽头这地方往前看有一个明显的向上的坡度,一跟跟路上碰到的黄色小桩子、一块指示牌相隔不远的立在这里。老吴随大刘下了车,司机也下车一边抽烟去了。大刘走到桩子跟前,跟老吴又详细的说了问题的细节,没听之前老吴一直认为这就是个钱的问题,听了之后,老吴瞬间觉得头都大了。
“这条管线沿着山脚下铺过来,本来应该顺着山脉一直铺到80公里开外,没想到铺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开沟时发现1米以下都是基岩,而且硬度非常大,覆盖了超过10公里,开凿基岩的成本太大,因此从这里直接90度转弯朝向现在站的方向,正好也照顾到那周边的用户。”大刘说话干脆利落,声音洪亮,脸上明显的被风吹出的黑中带红的颜色,使得他越来越像是一个西北汉子。“管道这两年易手之后,上面改变了气源,还准备二氧化碳、氢气这些气都进来,间歇输送。这个弯头,承受原来气源的磨损是没问题的,新的气源、三种气顺序输送,从理论上讲,对它的损坏要加快。站长的意思,这次由你们出方案,用最少的钱,保证这个弯头跟输送原来单一的气有一样的寿命。”
来之前,老吴只听领导说这里是要求测算弯头寿命,老吴想着这个活虽然以前没有领过,但是毕竟是有据可依的,查查站上逐年运行的环境数据,结合实地观察,自己编个表格,代入公式计算一下,也多少能测个八九不离十,把计算方法和参数甚至都能一并上交都没有问题,还能拿个不大不小的公司级奖励。现在倒好,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10倍不止,问题就处在,按照原计划,只测算弯头外部减薄速度就可以推算寿命,现在还要叠加内部减薄速度,何况内部还不一定是简单的均匀减薄,还存在点腐蚀、开裂腐蚀这些可能性。现在站上的运行数据获取的输量一下子翻了几倍,除了环境数据,还要这个站进站的介质参数,压力、温度、流量甚至一些取样的参数,因为这个弯头处于两站中间,还要上游站协助提供同类别同数量参数,并且还要推算出弯头这个位置的实际参数。更大的问题是,二氧化碳、氢气现在还是没影的事儿,客户那里还在规划当中,到时候有多大的量,气体的品质如何、输送方案怎样,都是未知数,原本胸有成竹的老吴,从轻松愉悦的心态一下子调整成了眉头紧缩、心事重重。
当然,老吴的表现有一部分是给客户看的。毕竟这个跟原来的委托差别太大,如果真的决定干下去,一定是要借机增加成本的。而且领导这次只给了老吴一周的出差时间,搜集数据都不够,还不知道汇报之后领导会是什么样的指示。如果在这边拖的时间太长,疫情反复的风险就会加大,在现场的时间就会更加拉长,老吴的鼻血问题就会无限期的得不到解决,老吴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了一点点十年前的绝望。
但是老吴是干事儿的人,在皱了眉头叹了气之后,还是按照原计划把周边的地貌和土壤情况进行了记录,还按照大刘的指示在大概管子的正上方脑袋贴着地面听了听。当然这有一点装的感觉,这也是老吴在看“让子弹飞”这样的电影时受到的影响,有一些仪式感的动作会让你显得很专业。显而易见,这么听,是听不到气里面混合的微不足道的细小的沙子撞击和摩擦弯头的声音的。做好了这些方面的记录之后,老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直接在现场跟领导汇报了情况。不出所料,领导的反应就是延长出差时间,在这里做好充分的记录,该算的算,拿出初步方案,再考虑返程。老吴除了暗暗骂娘,做出的动作却还是点头哈腰,并且谦卑的回答:“好,好,一定办好,我会细致的测算,打好客户关系,寻求公司的其他机会”。领导那头回答了一句“好”,就挂了电话。
回到站上的这一天,老吴除了午饭和晚饭的时间,都耗在了控制室的数据记录机器里。密密麻麻的数据敲的老吴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倒睫毛在这种时候十分的尽职尽责,让老吴的眼睛疼痒难忍。腰、脖子好久不曾有的酸痛也顺利的回归到老吴身上。老吴抬起脑袋,转了一圈,骂了一句“娘的,这样玩命干啥”,点了存盘,拍拍屁股回到了宿舍的床上,没几分钟就打起了瞌睡。强打精神洗了洗,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这次睡的,整夜香甜,甚至连那个“尽头,尽头……”的声音变得略微有些急促,都没能引起老吴在梦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