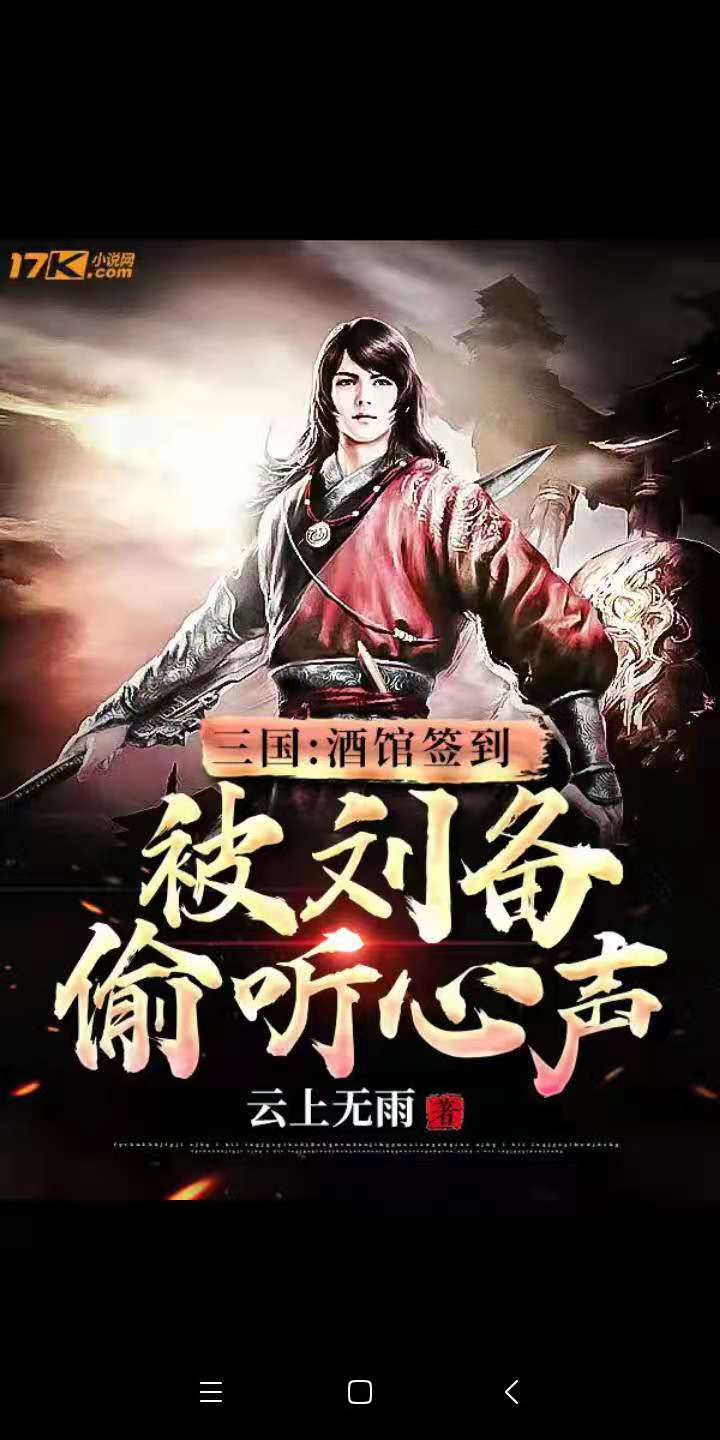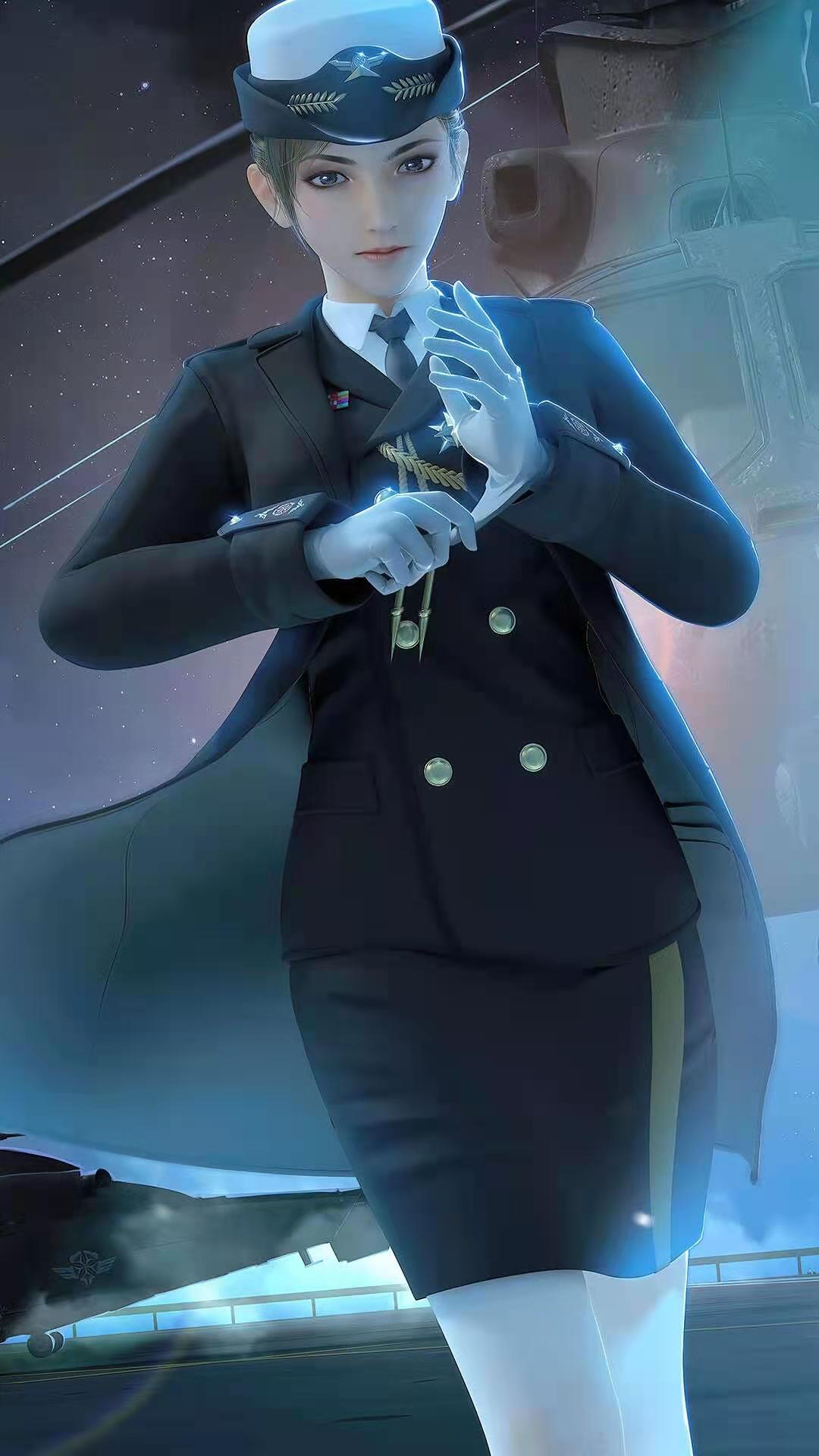上回记到:“绿色环保”让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我们事务所另一主角小王了。我对闻老师和老胡说:“我们的忘年交小王,他一直想加入我们。目前我们事务所仅几位中年人士,市场亲和力明显欠缺。不如让他加入吧,增加小鲜肉提升点市场亲和力,怎么样?而且他也是绿色低碳生活的热心人。”
小王与我们认识也好几年了,他父亲经营着一间小茶楼。几年前,我们经常到他父亲王老板的茶楼去喝早茶。这茶楼占地不宽、高处也只有三层,隐在高楼林立的大马路拐角,沿茶楼旁的小巷往里走,便有一种城中村。茶楼外面看是素墙旧匾石阶砖柱,很似行将拆迁的搁置之所,但一进入店门,鱼池假山、庭井回廊,倒给人以另有天地之感。老板老王,是位五十来岁的当地人,待人热诚;茶点款式多样、味道正宗价格公道,所以,店子生意不错,经常坐满了老老少少的顾客,都市白领、当地村民、市井街坊,间或其中。
我们也喜欢这里的氛围,假日常到这里坐上一两个小时。有一日,我们正闲聊着,王老板径直走向我们。客套几句之后,直爽性情的老板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是这个村子的人,年轻时候也刻苦念过书,无奈家境不好,早早便做过学徒,到沿海打过渔、跑过运输、搞过建筑;后来,随着城镇城市化的加快,这座南方城市开发力度空前,当地经济也跟着迅速活跃起来;现在他们村的富裕程度,虽没有某些电视报纸上报道的那么夸张,但确实可以这么说:他们这辈是可以不忧吃穿的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还辛苦开店呢?他说:他不觉辛苦,做惯了、闲不下来。闲下来,就心不安。这些年他一直做着事情。前两年他们村集体刚好有这个闲置房要出租,他便承租下来做成了这个茶楼,来茶楼多是些附近老街坊,是些薄利,但勉强能维持,不求赚多少钱,只是图有个事做,日子过着踏实。
不过,他又说到了他的一个不安:“我儿子也是大学毕业,学建筑,我这店的装修是他琢磨的。原本我很欣慰,比那些成天花天酒地的村里小年轻踏实多了。不知怎么,近两年他所在企业效益不好,他便闲了下来,也没出去找事做,却成天看些什么管理书、古文书,与村里同龄人没话说,憋在家里,我怕他憋出毛病来!你们来店也有几次了,我见你们知书达理,我虽没读过多少书,我还是能大致听得出你们也是念过不少书的人。我想找你们帮个忙,你们说得上话,便引导引导我儿子吧!”
见王老板如此说,我们也倒想见识见识这位年轻人。我热心答应道:“谈不上什么引导。现在读什么古文的年轻人确实很少,难找到共同兴趣的同龄人交流,有东西憋着对身心确实不好。就当是相互交流吧。”于是,王老板便出去联系他儿子小王了。
我们边等小王,边说起了老板们的不安。我当时闲扯起来道:“看来,现实生活中常常富人更富,是有许多原因的,包括他们的进取心等等。我想,有些富人更富的原因可能是这些人应对不安的方法,为了把日子过踏实、他们习惯通过做赚钱的事来压制这种不安。金钱确实能带来一些安全感,但毕竟金钱并不能使人固若金汤,人总会有不安的;于是这种人的不安便持续不断为他们创造财富,使他们钱越赚越多、越来越富。”
老胡接着说:“是啊!这种人通常又非常理性,不太喜欢冒险,只做他们圈内的事,通过重复的理智来积累钱财,从而把赚钱事做成了习惯,别人很难与他们竞争。幸亏现代管理加强了税收、防止垄断等调节机制,通过机制来防止这种贫富来得相差过大、形成常态。”
闻老师却道:“你们所说的属于个别现象,大部分的富人更富应当是源自他们的修为与管理精神,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不安,相反他们能逐渐把物质这个目标管理成愿景,转而注重内在层面上的追求,成就物质与非物质两层意义上的富贵人家。”
老胡这时说:“为富不仁也还是有的,发了财而修为却止步不前也是有的,而且使起坏来破坏力更大!好了,我们还是不要把钱与和乐相提并论,有钱人只能是少数,而和乐是人人可以有的。大庭广众少谈钱,有失我们斯文形象;闻老师,你就说说普通人该如何和乐?和乐不一定非得行事生财,应当也可以在事外求吧。”
闻老师这次认真说开起来了:“也许同富人更富道理一样,通常来说,和乐的人总会和乐,不和乐的人总是不和乐,其中的原因也有潜意识里的习惯作用、或叫条件反射又或是理念自相矛盾之类。比方说,悲观的人总是单方面、或悲观角度看事物,为何总是如此呢?这恐怕与这个人的悲观习惯思维分不开的;急性子们不和乐与目的性太强有关,不知迂回分合、抽丝剥茧,便有路怒症之类的燥动。又比方,悲观的人也总是习惯于固定某一事或某一阶段,不习惯于变换,不得不变的变换又显得很被动,而被动往往让人沮丧,更加重了悲观的情绪感觉。又比方,我们的感觉在情绪影响下,已经不是一面正常镜子而成了哈哈镜,我们感觉到的事物完全失真,没有机会或时间得到修正,确实有时也有没必要修正的逻辑。又比方,我们极力想出人头地走在前面,到走在前面之时又觉不安全……”
我们正瞎说着,王老板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