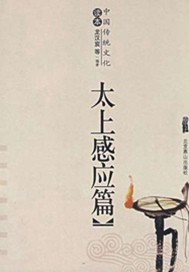炸山炮集体哑火那年的夏天,他偷了一盒火柴,在工棚后玩火。他们一家和很多工人都住这一溜长长的茅草工棚里,用茅草搭的墙、茅草铺的顶。他弄了很多枯枝败叶,堆在草墙后边点火玩。火势烧得很旺,他都能感受到灼面的热浪。蹊跷的是,烧了好一会,草墙居然毫无影响,直到一个路人发现了,赶过来扑灭了火。很难想像,如果烧毁了整座工棚,会有什么后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被烤成乳猪应该是大概率的事。直到现在,他还是想不明白,明明都是草,为何草墙居然烧不起来。蹿起来的火焰几乎已碰到茅草屋顶,而屋顶也没点着。(那天玩火付出的代价,是父亲用洗锅的竹篾筒狠狠地戳他的左手大拇指,戳得鲜血淋漓。后来伤势愈合后,指甲里长出一层赘肉。四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熟人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转发的一则古琴招生广告,一时兴起就去报名学古琴。他的指甲偏薄,多滑几次弦就会出现凹痕,本不适应古琴,但这层赘肉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使指甲变得经磨。这应该是另一个小意外了。)
六岁那年冬天,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他跟几个小伙伴在海边捅水面的薄冰玩,一不小心滑下堤坝,掉入海里。他不会游泳,厚厚的棉袄一开始还有点浮力,所以没很快沉下去。仰头看到岸上的小伙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丝毫没有想帮他的意思,也没有去找大人帮忙。棉袄进水后,逐渐下沉。他仰望着灰色的天空,脑子里似乎也这么灰茫茫的,但绝不是恐惧。他还小,没有死亡的概念,所以还没有求生的欲望,只觉得整个人空空荡荡,混混沌沌。在水快要没到嘴巴时,不知哪里来的意识,他突然就手脚并用游了起来,游了几下后抓到海堤,然后攀着海堤上的石缝,硬是爬上了比他人还要高的堤坝。全身里外都已湿透,在隆冬的寒风中,往家走的路上竟也没有冻僵。母亲乍一眼看到他这副惨样,差点没吓晕过去。三两下剥光他的衣服塞进被窝,用加了热水的葡萄糖瓶,慢慢把他捂热。
十四岁那年,他在镇上读初中。当时学校有集体夜跑的安排。上完夜自修后,全校每个班级都要组织去校外马路上跑步。那时的马路还是泥石路,高低不平,也没有路灯。有几个同学拿着手电筒,跑在队伍的边上,照着路面,防止有人看不清路面摔倒。
他一开始是跟住班里队伍的,跑出一段路后,因为分神听路边的虫叫,不知不觉拉下了。等他回过神来,队伍已跑出很远。没有手电筒照明,前面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为了赶上队伍,他开始加速。虽然看不清路,但他大致知道路的走向,心里还是蛮有把握。
从耳边拂过的风声,和路边建筑物造型的隐约快速变化,能察觉到自己跑得飞快。正想进一步加快速度,这时,漆黑的前方,突然出现一道红光,整个前方变得血红一片,随即迅速熄灭。他着实被吓了一大跳,不由自主地紧急止步。因为惯性,踉跄了好几下才勉强顿住身形。
几道手电光照上来。后面其他班级跟了上来。顺着手电光,他看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场景。
他的前方,竟是一大片嶙峋的乱石堆,锋利的石块向上不规则地矗立着,黑暗中,就像一个插满尖刺的陷阱。而他此刻刚好站在这个陷阱边上。只差一步。
如果不是那道红光,那他将重重地摔进这个乱石堆,按刚才的速度,他根本来不及做任何防护动作,脑袋将直接撞上锐利的石块。
他几乎已听到自己头骨裂开的脆响。
二十岁那年,他出了一次车祸。他坐在货车的副驾驶室,凌晨三点,车子在一个上坡的急转弯处,司机没看清山路,直接冲下路下方的农地。落差很大,车头栽到地上居然没变形,他因此也毫发无伤。天亮后,车里的人都吸了口冷气。没过几步路,就是一道二十多米深的山崖,如掉入这么深的山崖,不可能生还。
更玄的是二十六岁时发生的事。他在工地做打桩机的操作工,每天操纵着轰鸣的机器,把笨重的铁桩头周而复始地打进地里。那天,他刚打完一支桩,几乎是无意识的,瞟了一眼桩管上方的振动器的电缆线。平时,他从不去看这个振动器,更不用说是这根电缆线。就这极其偶然的一瞟,救了他一命——电缆线因高频度震动,外层的橡胶皮已被磨破一大块,露出了里面的铜线,在昏暗的光线中,泛出些许微小的光。这个机器用的是380V交流电,只要这通电的铜线,接触到机器的任何部位,一秒钟都不需要,电流会瞬间要了他的命。
直到今天,他都无法理解,他当时为何会去瞟这一眼,然后随随便便就发现这个致命风险。更无法理解,这根电缆线的外层橡胶皮已破了一大块,说明已磨损不止一天两天,为何这么长时间,祼露出来的铜线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震荡中,居然始终没碰到机器——这里有个逻辑的悖论,能够把厚厚的外层橡胶皮磨破,说明机器的某位部位肯定在持续触碰这个位置,既然是持续在触碰,为何在磨破外层后就不再触碰铜线?
按现有的经验,唯一能解释通的,只有这种情形:包住铜线的橡胶保护层,在这一刻刚好被磨损殆尽,此前虽有磨损但仍具有绝缘功能;这一刻,刚好不在机器平时触碰电缆线的位置;这一刻,振动器刚好下降到他能看见的位置(平时振动器都是悬挂在十多米高的位置,只有桩管被打到地下时,才会随着桩管一起降到靠近地面的位置);这一刻,从不去看这个位置的他又刚好把无聊的目光投向这处;这一刻,昏暗的空间中,又刚好出现了铜线的一小点反光。
“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每一次又都匪夷所思。要触发这么多偶然因素,概率已低到几乎是零。确切地说,就是零。顺带说一句,你们人类发明的概率论真的是很蛋疼的学科。你们试图通过概率来摸清事物的规律,事实上,事物没有规律可言,它只有两种状态:发生和不发生。发不发生,全是因为出于需要作出的安排,所以不存在概率的问题。如果有,那也只是你的猜测恰好跟这种安排吻合而已。而这种吻合,并不是必然性的表现。就拿你自己来说,按照概率,你已死了很多次,但事实上你活得像只新出笼的馒头,戾气腾腾。之所以如此,只因你还没完成使命,所以现在还不能死。”它微笑着说。
“这么说,我是领到免死金牌了?”
“可以这么理解。但使命根据需要会随时调整或终止。失去使命的人,将不再有任何保障。所以,你完全不必陶醉过去的幸运,可能就在下一秒,你的使命就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