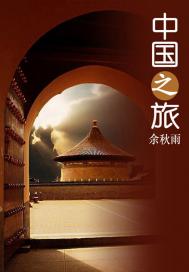我慢吞吞的下了车,往左边走了几步,然后左边的他们跌跌撞撞的往右边挤。我又朝着右边走了几步,原本已经挤作一团的他们,仿佛遇见了极其害怕的东西,挤的更拢了,仿佛笼中的待宰的的鸡鸭。这么说不好,但是真的很像。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左左右右的来回走了好几次。看着他们在车子里慌乱的躲避,挤作一团,我觉得慌乱躲避的不止有他们,还有我的心。当然,前提是我的心还在跳动。
我坐回了我的小电驴上,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12:52,是吃午饭的时间了。但是我应该吃什么?缓慢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我觉得我不饿,嗯,很好,可以不吃了。但是我应该做什么呢,手机不能玩了,没有网络了,还开着省电模式,只能看看时间。
社会纷纷扰扰,终日为任何事情奔波忙碌,一息安宁何其难得。我又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放空了脑子,没有手机,没有疲倦,没有焦虑,甚至没有思绪的静静坐一会儿了?我忘了。
……
也许是我的安静让他们明白我对他们并不具备任何威胁,渐渐也放松了些,不再紧紧的挤作一团,但依旧盯着我。
被他们盯着是什么感觉呢?我想想,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当然,不排除如今的我感觉迟钝,感受不到。
他们是依靠什么来感知外界的呢,眼睛?嗅觉?听觉?还是什么感应之类的?那么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生理机制运转着的呢?说实话,我真的有些好奇,这可能是现今医学完全想象不到的。而我,只是停留于现今的医学刚刚入门阶段而已。
再想想,我自己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最好的观察对象。至于实验对象什么的……,如果有需要的那一天,请原谅我的自私吧。
我有自己的思维,那么他们呢?我看看他们,看了很久,我想,要不,打个招呼试试?
我艰难的做了一下吞咽的动作,试图感受一下我的声带是否还具备功能,但似乎是徒劳的,除了很小的嘶哑的像是风吹过枯树洞的声音外,我没有听见任何声音。
但我还是开始认真的观察他们,希望能够看出他们中任何一个会表现出人的行为举止和眼神,也希望他们他们中的某一个能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人的特性。
人的眼睛到底能不能传递感情这一类不能具象化的事物呢?于医学而言,这是一个得不到肯定回答的问题,更有研究认为,你所看到的眼睛里的情感,是你想象的,认为的情感,也就是你所赋予眼睛的情感。
有些深奥吧,嗯,这种没有谜底的谜题,各种天马行空的论证,用来打发时间是最好的。
7月初,6点多了,太阳还有一半儿没有下山,但是我感觉到了他们的躁动。不止他们,还有我自己,身体的灵活性提高了,视野变得更宽了,听力更敏锐了。
所以,我听到了公路另外一边树林里的声音,也隐隐可以看到一抹蓝色,我有些紧张,依旧坐在小电驴上没有动。
好在,没有出来,或者是从其他地方离开了。我再一次确认一件事,也许我不需要害怕他们,他们不会攻击我。虽然这也让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我,和他们,是同类!
同类啊!多么美好的词,几乎让人想要落泪,它现在明晃晃的摆在我面前,我却哭都哭不出来。我一直逃避这个词,逃避虽然可耻,但是它有用,可是逃避不了啊。
车子里的他们越来越躁动了,但是他们依旧不敢在车子里四处走动,只是在那个角落里,贴着窗子,抓着玻璃,想要出来。没有用蛮力去撞,我想他们应该出不来吧。
我把背包放下,取下车钥匙,不管怎样,我都是要回家看看的,最多不让爸妈发现我就是了。这很简单,我猜,这时候应该是没有人在外面的,所有人都会找一个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躲着,而不是四处闲逛。
转过弯道,我看见了房子,大门紧闭,鸦雀无声,暮色沉沉,宛若一座死城。
其实有些夸张了,死气沉沉是真的,但不是城,毕竟这里只是一个小村落,沿着公路带状分布着住户人家,连一条街道都算不上。
看见的第一家房子,是一个小卖部,还小的时候,经常在这里买零食或是一些日用小杂物之类的东西。大了之后,不常在家,买的也少了,就连这一节路上的人也生疏了。
周围这几家,好像家里都有两三个小孩儿,天热的时候,大人带出来歇凉,既吵闹,也让人羡慕,是整个歇凉团队的核心。
这边前面的这家,我不怎么喜欢,因为他们家里有麻将机,经常喊我妈去打麻将。我妈一走,家里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弄得我经常站在大门口使劲儿喊。
他们旁边就是我婶娘他们家,他们一家人都在外地,钥匙交给了我妈,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婶娘对门的住户,是好几年前高山移民搬来的。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怎么认得亲,反正他们家的小孙子喊我一声姨婆,我把他奶奶喊姐姐。这对于在我妈家族中,即使是个小孩儿都有可能叫舅舅的我来说,很是开心。所以,也对他们家的小孙子尤其关爱,是我家周围所有小孩子中独一无二的关爱。
我可以感觉到,这便宜小孙子也是很喜欢他这个姨婆的,经常问我:“姨婆,舅公呢?”
哦,他舅公就是我弟,他比我弟小三四岁的样子,经常玩在一起。曾经我听到他俩和另外几个周围的差不多同龄的男孩儿相互以哥称呼。
然后就是我家了。
大门前停放着一辆红色的三轮车,花台里的那棵女儿红似乎更茂盛了。
随着我的走近,不远处游荡的的几个,默默的走远了一些。我没敢多看他们几眼,害怕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婶娘他们家大门虚掩着,这很正常,这里还算民风淳朴,经常有人家夜不闭户。堂屋、客厅以及厨房,就一些杂物放着,没什么生活的气息。我上了二楼。
婶娘家两个堂哥,都在外地打工,没有娶媳妇,但是婚房准备的妥妥当当,两兄弟一人一套。我去的是靠近我家的那套,面对公路的客厅,里面沙发都是崭新的,用防尘布罩着。
现在一点儿都不冷,我今晚睡沙发完全可以。但是现在还早,作为有些夜猫子的我,打死也是睡不早的。
窗帘掀开一道缝儿,打开窗子,我一边吹着晚风,一边静静听着隔壁的动静,周围几乎看不见游荡的他们。但是我看见了斜对面一家二楼的窗帘动了一下。
那一家的窗子是关好了的,不会是风吹动的,这让我有一些惊喜,把窗帘缝儿拉着再小一点儿的同时,看的更仔细了。
可惜,我看了半天,天都渐渐暗下来了,还是没能再次看到窗帘动一下。有些遗憾,但也还好。
我拖了一把椅子靠在墙边,坐下,把自己脑袋也贴上去,尽可能的的希望听到一点儿声音。但是,这都是农村的自建房,用料还算是瓷实,隔音效果还算不错,反正我是没能听见什么。
百无聊赖,静等天色混浊。第一次,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太阳落上到完全天黑这段时间这么长,长的让我觉得我度过了整整一天。明明清醒着看着天色一步步的昏暗,却如同无力地的看着自己缓缓沉入黑暗,全世界都是寂静的,寂静的如同被全世界抛弃。
好在,时间有他自己的坚持,就算它走得无比的缓慢,也依旧在走,而没有停下脚步。
黑夜的掩护下,我把窗帘拉开了一大截,把头伸出窗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响,除了虫鸣,什么也没有听见。眼睛适应了黑暗,隐隐约约能看见大概的影子,没有活动的东西。
安静,太安静了,我不知道这算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很害怕,甚至忍不住的想要发抖,但是肌肉的痉挛除了让我本就不怎么灵活的身体更加不受控制以外,毫无作用。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开始思考事情,希望以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之前我看到了,我家的大门是紧闭着的,窗帘什么的也没有打开。楼顶是风貌改造做的瓦,还有够几年烧火用的柴,也就是说,楼顶可以做饭。
没有电,冰箱里的东西会坏,但是只要有米有水的话,还是可以坚持的。水的话,是接的山上的泉水,水管埋入地下,平时也不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关于水的问题。
想到这儿,我开心了很多。接着又想到,顶楼上有个大冰柜,里面放了不少腊肉,都是熏制好了的,放冰箱也只是为了防虫。二楼几间屋子都是前两年装修的,门还算结实。
看看,还是挺不错的,不是吗。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带回来的东西,还在小电驴上,而小电驴还在公交车那儿。
白天去拿,可能会被人看见,会被爸妈看见,而我现在不能被人看见,矛盾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现在去拿?不会被人看见,也不会被爸妈发现。
但是,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