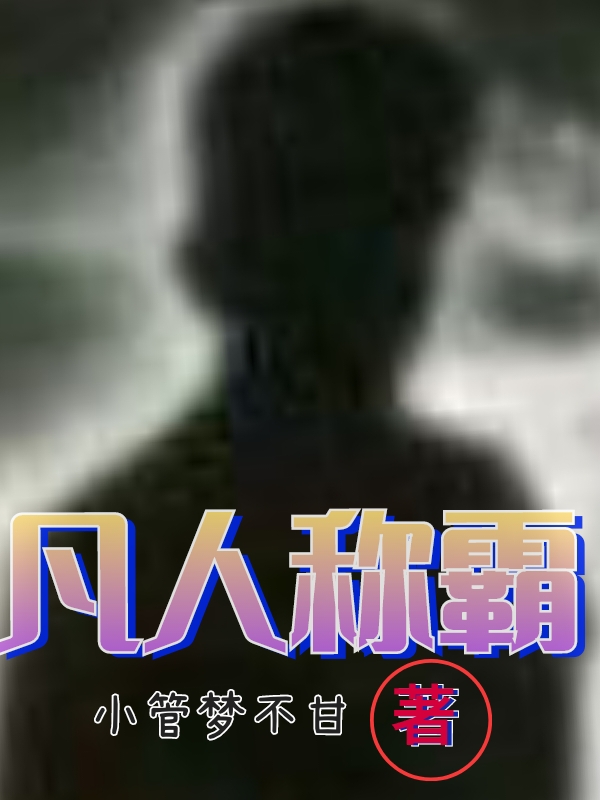傍晚,御史台旁,杨府。
王既独自坐在这个空荡荡的前厅里,身旁连个添茶的人都没有。这红木椅子硬得很,坐得人腰痛。
离开金炭楼已经约两个时辰了,王既还没完全从那场闹剧中缓过神来。
他走下台后不久,周围就迸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什么允州果然才是天下第一棋州,人杰地灵把棋仙引来了,九州棋圣要换人,杨门棋号‘’沉龙”要震惊天下云云,都有人在喊。这些讨论,几乎都是围绕着王既这个最后一天才登场的陌生年轻人的,似是那个外州人连赢十天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
王既暗暗观察那个独自走下来的壮汉,发现他的神色有点出乎意料。原以为此人摆得这么大阵仗,不为利,也总得求个一战成名天下知。如今在最后一刻被自己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连下了十局,就算不生气,也起码有一点伤感才是。
但这人脸上满是春风,步履轻盈如燕。纵然身影孤单有一些落寞,但王既也能感受到他一身的轻松欢愉。
那壮汉下台后,只见他从那盒装满精金灵石的盒子里,掏出一颗扁圆的金棋子,直直放在了杨八通手边的桌子上,看了杨八通两眼,点了点头。
然后把整个盒子放到王既手边,示意他拿走,完全没给他拒绝的机会,转头就消失在吵杂的人群之中。
或许这壮汉,本身就不在意这次胜负。
王既本身是极不喜吵杂的人,被这些直直向着他的欢呼震得头痛难当。当那个先前拦过他一次叫作柳期的年轻护卫,唤来一大堆人,要为杨八通开路,然后往王既招了招手时,王既几乎毫无犹豫就跟了上去。
除了要赶快从这场闹剧中脱身外,他还有充分的理由要跟着。
就像他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要独自坐在杨八通府上的大厅里,等待着他的召见一样。
……
不知过了多久,夕阳似乎降了几分,天色逐变暗黄。
那个叫柳期的黑衣护卫,从内院走了出来,把王既引到了一个类似书房一样的地方,留下一句:“杨中丞仍有军务,公子稍等。”之后,又不见了人。
但这房间比前厅要有意思得多。明亮又昏黄的烛光下,看得四周的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信封文件。房间的正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沙盘。沙盘上的地形山脉栩栩如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红旗子和绿旗子之间的剑拔弩张。结合着墙上那挂着的巨大地图来看,这沙盘展示的,是允州边界的布防。
这房间,显然是讨论军情的地方。
王既此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该看的,但却来不及了,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好得像高清摄像机一样,扫过一眼之后,连沙盘里河流多宽,地图上哪个位置对应哪个点,都记得清清楚楚,想忘都忘不掉。
他立马把头转向窗外,不想再惹额外的麻烦。
正想着,挂着地图那边的墙左侧发出咯吱一声,内室木门被推开,里面缓缓走出一个精壮的白头老人。
正是等待多时的杨八通。
只有他一个人。
王既站了起来,直视着他的眼睛,脑海里响起了这老头白天在他耳边说的那句话。
“你被烙了七阶“寻踪印”,很多人跟着你,允州能解此印的人不超过五个。帮我彻彻底底赢了他,把允州的面子挣回来,我替你解了。”
当时王既一听“寻踪印”这顾名思义的三个字,基本上就对早上费尽心思都甩不开外面那两个黑影的怪事恍然大悟了——身上被装了追踪器!
他虽不知道这“寻踪印”是什么原理,但从他观察到这世界的超自然力量来看,没有类似跟踪器的东西才真叫奇怪。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好的还是坏的,在重要的人物身上安装跟踪行踪的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怪就怪自己还是被这古色古香的世界迷惑了,自己早上心态差点被搞崩,实在是有些滑稽。
在答应上台下棋前,王既就想到,即使帮了这个老头,他的话也是不能完全信任的,甚至乎觉得这种人物说的话基本就不能信。但他又一转念,自己这样孤身一人来到这世上,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他相信的,如此步步为营胆小怕事,最终也不一定能避免什么,倒不如该赌的时候就赌一把。所以他才上场去搞了那么一场,让这老头彻底满意。
正当王既在小心翼翼地衡量着该怎么说话时,杨八通已径直走到跟前,只见他把一块拇指长的木条放在王既右手边的桌子上,面无表情地说道:“别在我这里,你出去找个地方,把这木头捏碎,外面那八个人就跟不着你了。”
有八个人?王既惊了一惊,但面罩的存在让他很好地隐藏住了自己的表情。
他拱了拱手,直接从桌子上拿起那根木条,说了一句:“多谢。”然后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
他想尽快离开。
他完全看不清杨八通的想法做法。
纵使他知道自己先前、现在的表现,还隐藏着身份这些事,必然会让这个老头生疑,之后肯定会带来不少麻烦。
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想隐藏身份的人,在这样的大人物面前,他根本没有手段可以多做些什么。万幸这老头起码表面上做到了能够说话算话,给了一根还不知道有没有用的木头。但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自己假如想耍一些小聪明在他这里套到什么东西,无疑是痴心妄想。
说多错多,想多烦多,不如领了报酬,早走早着。
“慢!”杨八通在身后叫道。
王既停下了脚步,心里咯噔了一下,回过头去。
“已入夜,公子可留下用饭?”
“…”
王既沉默了片刻,扶了扶面罩,说道:“中丞大人,可是要在下把脸容留下?”
这是王既理解的意思,他知道假如这老头想知道他的身份的话,自己无可奈何,什么手段都没有,几个下人上来一摘便是,倒不如自己先提了出来。
杨八通笑了笑,说道:“公子多虑了,若不愿,请便。”接着杨八通从怀中掏出一颗椭圆形墨绿色的玉,放在桌面上,说道:“这个也拿走。”
说完,转身就走回内室,把王既独自留在原地。
王既把那玉拿到手上,借着外头微微的夕阳光一看,玉上楷书二字。
沉龙。
…
书房内堂。
听得门外王既已经走了出去,杨八通才缓缓坐下,掀开了那杯已经放得有点凉的茶,喝了一口,双目依然盯着放在茶桌前的棋盘,一言不发。
棋盘上的局面,是王既最后留下的大雪崩内拐。
这内拐的一步,是用那设下擂台的壮汉留下的一颗金色的棋子摆放的,在那通遍的黑白子棋盘中,这金黄甚是显眼。
那个叫柳期的黑衣年轻人一直在内堂,见杨八通茶不满,连忙上前去添,一边倒茶一边欲言又止。待茶快满时,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中丞,说句题外话,这年轻人身份未明,如……如何能把他带到书房这军机重地来?”
杨八通头也没抬,沉默了半晌。
良久,他摇了摇头,淡淡地吐出一句话:
“那,可是宗主的某位公子爷啊……”
柳期目瞪口呆。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蒙脸的年轻人竟可能是宗门的后人,心里怀疑,说道:“中丞,何以见得?”
杨八通皱了皱眉,显是对这个自己亲手培养的年轻人的观察力和推理力有些不满,反问道:“这么多年,你可见过谁给烙上了七阶寻踪印,还能满大街跑的?”
柳期哑然,他确实没多想一步,这七阶的寻踪印十分不常见,极难炼制,九州之内只有允州离天宗有制做的能力,一般只用于极度重要人物的抓捕或保护。
柳期自言自语道:“确实是,近两年,没有任何一个调用七阶寻踪印作监视和抓捕的申请,仍在使用的只能是允州的贵人了。”
杨八通点了点头,神情满意了一些,继续考问道:“允州有近百个被上了寻踪印的贵人,如何确定是公子爷?”
柳期想了想,回答道:“允州被烙下寻踪印,又符合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不会超过十个,按当前的战局部署来看,只有稍微闲置的公子爷们能在春风街出现了。”
杨八通满意地点了点头,喝了口茶。
“弟子还有一事不明。”柳期问道:“既然是保护为主的寻踪印,公子为何想摆脱?中丞你又如何得知?”
杨八通沉吟一下,说道:“要想到这步,确实是难为你了。这七阶之所以难制作,原因在于其具有延伸性,一旦目标人物多次离开跟踪范围,用灵力看便能看到其自动化作红色,用于扩大追踪范围。”
柳期恍然大悟,说道:“果真那奇异的红色是有理由的。”
说着杨八通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至于公子爷为何想摆脱,就不得而知了,年轻人放荡不羁一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老夫帮这一手,也无伤大雅。让他来书房,重点是要让他看一眼允州战局之紧张,早日收心。”
柳期此刻算是完全明白了杨八通的行为。
杨八通欣慰地笑道:“宗主压下来的死命令,竟让他的一位公子爷替我解决了。”说着松了口气,赞叹道:“不过,允州有此人,真是大幸。”
柳期此刻,更多的是对自己上司这种惊人的观察和推断能力赞叹,不禁追问道:“依先生之见,是哪位公子爷呢?”
杨八通沉吟片刻,说道:“以年纪身段来看,大致是二公子吧。”
柳期点头默然。
杨八通把目光收回到棋盘上,死死地盯着那颗摆擂台的壮汉留下的金色棋子,说道:“说回正事吧。”说完,杨八通把那金棋子拿起,食指和拇指捏着,举在眼前,一字一顿说道:
“这,才是我们的大麻烦。”
棋子的底部,刻着一个字。
宁。
……
……
王既本来脑子里还觉得哪里有一些违和,但他一踏出杨府邸,看到街对面那一座五六层高,大理石做,红木支撑,金瓦点缀的御史台时,顿时就好像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他寻了一个人潮密集的地方,按照杨八通的说法,把那木头用力一捏,整根木头竟碎成了粉末,然后化作一道精光,消失得像空气一样。
但他却没观察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变化。其实一开始,他就看不到什么寻踪印。
接着,他便如白天那样,在夕阳方下的时刻,趁着这暗色,辗转在御史台附近的商区穿行了八条街,又换了三个地方,吃了一份挂面,一份烤牛肉,一份清糖糕,途中还如白天那样不断更换不同颜色的衣装。
当他在一个人烟稀疏的窄巷处停下脚步时,他稍等待了一炷香。回过头去看,那两个明面上一直跟在他身后黑影,已经不见了。
他此时脸色才稍稍缓和。
他笑着摇了摇头,掏出了那块写着“沉龙”玉佩,看了两眼,自言自语道:“这老狐狸……”
话一说完,整个人双脚一软,直直地倒在了巷子里,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