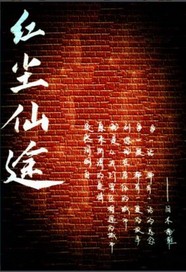孟承珩常年在朝堂上,被以严金锋为首的老臣搅得心烦意乱,他时常想要将这群老臣全都拉出去砍了。可当严金锋真的病死他乡时,孟承珩心中非常不是滋味,近日接踵而来的变故让他烦躁不已。
许久未曾踏入醉杏风的孟承珩,今夜为排解心中烦闷特来此听曲。
琴音渐入佳境之时,“嘣”的一声琴弦应声断裂,琴声戛然而止,琴师与孟承珩皆是一惊。
“弦太紧易断,弓太弯易折。人啊,受的打击多了就像这拉满的弦,张满的弓。一不留神就“嘣”的一声,没了。”
二分凉薄,三分戏谑的声音不适时宜地响起,来者正是宁王孟承琛。
见孟承珩脸色一沉,他依旧笑得十分欠扁:“三弟切莫放在心上,是二哥我胡言乱语了。”
作为不速之客不请自来就罢了,孟承琛反而大咧咧一屁股坐在了一旁空着的椅子上,反客为主对着台上已换好琴弦的琴师说道:“换首喜庆的曲子继续弹。”还顺手拿起桌上的茶点咬了一口,扭头对孟承珩说:“三弟,这茶点味道不错啊。”
看着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孟承琛,孟承珩多一刻都待不下去,他淡然起身道:“即是如此请二哥自便,三弟还有政务在身就不在此作陪。”
孟承琛望着孟承珩嫌恶离去的背影无奈摇了摇头。他这个三弟啊,当了皇帝都不懂得如何掩盖自己的情绪,喜怒仍形于色,注定成不了大业。
又逢十五月圆夜,夜幕万里唯见朗月。今晚月光格外明亮,无需点灯借着月光便可视物。
严媥婉赤脚踏着透窗而入的满地清辉,如同踏过摔碎一地的裂瓦琉璃。
奋力将手中的白绫甩过屋梁,一缠一绕便是死结。
皇后昨夜在寝宫中自缢了,好似万里晴空突然打了个惊天巨雷。
孟承珩的脑子也似被人打了一闷棍,开始生生地疼。昨夜孟承琛那意味不明的话像是预言又像是魔咒,此刻在他耳边不断地回响:“弦太紧易断,弓太弯易折。人啊,受的打击多了……受的打击多了,一不留神就没了……人就没了。”
孟承珩痛苦扶额,久久说不出话。“陛下,可是头疼的厉害?奴才这就去把高太医唤来。”东鹤低声关切道。
“不必了,你让人把鎏云宫看住了,谁胆敢将皇后自缢的消息传出去,格杀勿论。”
格杀勿论的死令一出口,东鹤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心善宽厚的圣上可从未一开口便是这种要人性命的口谕。
“是,奴才这就去办。但长公主那恐怕是已经得了消息。”
“榕姝,朕自会处理。”孟承珩知道严媥婉的死与他脱不了干系,他该怎样面对活着的人。
七日后,旭帝昭告天下本朝皇后严氏本月十五丑时因旧疾缠身,崩。严氏贤良淑德,性行温良,品行端庄,特追封为敬贤皇后,入葬皇陵。
倾州城来使今日捎来了将士们的家书,还带来了当朝皇后病逝的消息。将士们从未见过少将军如此悲伤的神情,那是一种无法掩饰的哀恸。
大漠孤烟,莽莽黄沙,沙海中城墙的蜿蜒盘踞,萧擎戈镇守北漠的每日入眼都是同样的光景。
五年来他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用满腔壮士豪情冲减去心中的思念忧愁。可就在今日的长河落日除了平日里的孤寂,更显得分外悲伤。
萧擎戈翻开榕姝捎人带来的书籍,有一封信悄然夹在其中,“荷戟兄长亲启”。
“一人荷戟,万夫趑趄。” ——“荷戟”对“擎戈”,便是萧擎戈表字的由来,当初少年志气 “荷戟”二字相当合他的心意。
萧擎戈犹记得,多年前自己曾经满脸骄傲的对那少女说道:“严家姑娘,你可以唤我的表字‘荷戟’”。
如今仔细回想,已经许久无人再唤他的表字了。
熟悉的字迹印刻在脑海中,让萧擎戈一眼便认出了出自何人之手,握着信的手因难以置信而微微颤抖。他回忆年少时曾无数次偷偷翻阅着榕姝与严媥婉一同习字的字帖,严媥婉写得一手好字,娟秀方正的字体一如其人。
“风扬黄沙舞,驼铃千古绝。荷戟兄长寄予榕姝家书中所描绘的北漠风光,令人神往。若媥婉能一睹这北漠壮美之姿,必是人生一大幸事。塞外险苦,望君自重。媥婉一切安好,勿念。”
一颗泪无声无息滑落在沙尘之中,瞬间已被蒸发。萧擎戈将只有寥寥数语的信,读了又读,即使是眼泪模糊了视线,即使是几度哽咽。他心爱之人第一次来信,也是最后一次。
萧擎戈给榕姝书信一封不落必在结尾处落上 “代问皇后安”,他暗藏多年的爱恋只能化成一句问安。他望她安好,更期盼她不要将自己忘却。
萧擎戈一身铁甲戎装伫立在城墙之上,眺望着南面那根本望不见的皇城。
淅沥沥的雨夜一抹纤瘦的身影,独自登上拥月台。少女将纯白宫灯紧紧护在怀中,落满细雨湿滑不堪的石阶,令她险些滑倒。
有一双手从身后扶住了她后倾失衡的身子,榕姝没想到如此深夜会有人尾随她至此,惊愕回头看去发现竟是冒雨前来的长音。
“雨天路滑,公主当心。”长音拾起落在石阶之上的纸伞,高举过榕姝头顶为她遮挡去漫天细雨。“公主只管往前走,长音会在后头护着。”
榕姝对上长音清澈的目光,发现这个傻子将伞全都撑在她的头顶,自己却淋着雨。
怀中的宫灯完好无损,他们二人一前一后在细雨朦胧中前行。绵绵不断的雨似乎彻夜不歇,在两人登上拥月台时出其不意地乌云消散,朗月当空。
整座皇城至高点便是像空中楼阁的拥月台,相传拥月台上生长着一棵百年神树,不曾开花结果,四季常青。
每逢月圆之时在拥月台上观望,神树伸展的枝丫形似一只巨大的人手托举着圆月。
世人皆说此树有灵,历代君王信奉其能护佑大简。
先皇后曾有胎梦,神树花开叶落,繁花满树。榕姝的出世之日,霞光万丈,神树竟真的叶落花开。
那一年大简风调雨顺,百姓皆传言长公主仍是树神转世,自带福泽。
长音初见神树时,惊讶于这棵参天古木的高耸庞大。
如今的神树似一棵枯木,无叶更无花,粗壮的枝丫依旧肆意舒展,可想枝叶繁茂之时是何等的遮天蔽日。
榕姝来到神树下轻柔地抚摸着树干,似与多年的老友打招呼。她脱去鞋袜驾轻就熟地攀上神树,长音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只见榕姝越爬越高,在中段枝干上停了下来,取出怀中的宫灯挂了上去。吹燃了火折子将宫灯点亮后,她便在那枝干上坐了下来。
“小时候尚青和我说,爹爹和娘亲会在天上看着我。便想着我要站在最高的地方他们才能看得清楚,还要点上灯,不然夜太黑他们怕是看不清。”
榕姝为皇后守着灵所以是一身素衣,三千青丝只用一根发带束在脑后,几缕鬓发被云雾细雨沾湿不见狼狈更显出尘,清冷的背影似与雨后明月相融。
“爹爹,娘亲,婉姐姐,你们在天上瞧着这宫灯了吗?姝儿还在思念着你们,不要走得太无牵无挂了。”
树下的长音遥望此情此景,暗想或许长公主确是落入凡尘的树神,只为历经人世间冷暖悲欢。
淳霜突然来口信说有要入宫请见时,让榕姝颇感意外。榕姝提起茶壶亲自为淳霜斟茶,“今日怎得有空入宫见我?”。
淳霜瞧着榕姝眼下乌青,难掩的憔悴。“有一事,事关皇后娘娘,如今娘娘仙逝,我思来想去不应再隐瞒。”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淳霜,此时神色严肃。榕姝意识到此事非同寻常,或许与婉姐姐自缢有着很大的关系。
半月前,两位头戴头纱的女子走进“凡庐”,药童见二人均未持号牌,便上前询问:“二位可有号牌?”
其中丫鬟打扮的女子客气说道:“我家夫人与淳霜大夫相识,今日临时来访并未来得及领取号牌。”
药童并未放行,来“凡庐”看病就一个规矩排队领号牌。“请二位见谅,今日号牌已发完,淳霜大夫一直忙着看诊,不妨二位领了号牌明日再来。”
“明日我们主仆二人不便前来,可否我们在此处等候,待淳霜大夫看诊完后,有劳通传一声。”另一女子说道。 药童见二人如此坚持,不好再拒绝,为二人搬了两张椅子,端上两杯药茶,示意两人需要耐心等上一些时辰。
“凡庐”内药香袅袅,三个小药童各司其职,各自忙碌。
“淳霜大夫,外头还两个人一直在等着,说是认识你。”
“等了多久?” 看诊完最后一位病患,淳霜略感疲惫。
“快两个时辰。”
“把人请进来吧。” 淳霜起身来到窗边的净手盆前将双手浸泡在加了特制草药的温水中,仔细地清洗。看诊的偏厅不大,窗户比寻常尺寸更大些,以保证良好的采光通风。进出医馆多是患病之人,保证屋内的通风透气格外重要。
听见身后的响动,淳霜取下架上干净的帕子将双手擦干。转身便看见站着两位女子,身形仅有几分熟悉,“二位请坐,是哪位需要看诊呢?”
“淳霜大夫多日未见了。”女子二人取下头纱,淳霜惊觉眼前二人竟是皇后严媥婉和贴身宫女馨儿。一时堂皇,淳霜行礼致歉:“民女不知是皇后娘娘,多有怠慢,望娘娘恕罪。”
严媥婉微笑道:“大夫言重,原是我临时起意想来趟大夫的医馆,何来怠慢一说。且‘众生皆凡人’,在大夫面前我也不过是一凡人,即是看诊自然是按着医馆的规矩来。”
“众生皆凡人,行医者有救无类。”师傅当年随手所题之字淳霜将它高挂于医馆前厅内。
淳霜自幼父母双亡,由师傅樊仁一手带大。神医樊仁行踪难觅,一生追求自在逍遥。淳霜随着师傅四处漂泊多年后,决心重回倾州开医馆当坐堂大夫。分别时,师傅只留给她这一句话,望她行医济世时能牢记一生的话。
淳霜暗想当朝有此国母如此,乃是大简之福。她嘴上虽不说恭维之词,但心中愈发尊敬,“民女先为娘娘诊脉。”
严媥婉将手腕搭在脉枕之上,淳霜依旧隔帕诊脉,“娘娘脉象虽虚却也平稳,继续静养即可。”
严媥婉闻言悬着的心稍稍安定,收回了手,站在身侧的馨儿为她轻理衣袖。“我将原先的太医给换了,近日新来的太医为我重开了张安胎的方子,有劳大夫过过眼。”
馨儿将药方递上,淳霜接过展开细看后并未发现异常,“此方确实安保之方,且此太医依娘娘目前气虚体弱之症,方中多为温补之物,娘娘大可放心服用。”
“如此,便好。” 严媥婉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为了腹中的孩子她只能多加小心。
淳霜出于对皇后的关心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娘娘莫怪民女逾越,民女尚有一事不明,娘娘长期服用混有番红花的汤药,按理怕是难有身孕,怎会?”
“我不太喜那汤药的味道觉得甚是怪异,已暗中有好些时日都不曾服用。或许也是上天垂怜,让我怀上了这个孩子。”被人当面揭开不愿提及的伤疤确实令严媥婉不好受,她也不过是牵强一笑,并未心生责怪。
淳霜自知不妥,但身为医者知道的越是详细对诊治病患越有帮助。自那日后,皇后便再未来过她的“凡庐”,这段时间严相夫妇二人相继离世,严府衰败的消息淳霜有所耳闻,不曾想再次得知皇后的消息,竟是娘娘病逝的噩耗。
淳霜与皇后相识一场,她真心敬重这位身份尊贵却没有架子,始终以己及人的皇后。即使不知严媥婉实则为自缢的内情,冥冥之中淳霜总觉得皇后的死并不简单,故而她决心入宫将自己知道之事毫无保留的告诉榕姝。
“番红花?”榕姝在淳霜一番叙述中听出了蹊跷,她追问道:“你是说此前曾有人暗害过婉姐姐,险些不孕。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
“皇后曾提及掺有番红花的汤药皆是出自一位姓杜的太医之手,自入宫之日起就有服用。”
榕姝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有一瞬间只剩空白。杜温——三哥一手扶持上来的御医,怎会平白无故暗害婉姐姐,难道他只是听命行事?!
榕姝脸上浮现震惊的神情与那日听闻此事的严媥婉如出一辙,淳霜自知她的决定没有错,也无需再多言。
杜温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皇宫中被人劫持,来不及挣扎就被三个黑衣人毫不留情打晕,不知被带到了何处。遮住杜温双眼的黑布被扯开时,他一时难以适应屋内的光亮,而有些恍惚。
模糊的视野里杜温隐约见着有一男子坐在他的面前,“杜太医可是清醒了?都怪本王手下的人下手太狠,把太医打晕到此时才醒过来”那人说话的语气带着特有的漫不经心。
“王爷将我绑来这是做什么?”杜温认出了是孟承琛,不免有些吃惊。
“瞧瞧老三养的狗东西就是没规矩,都敢质问我了。” 孟承琛笑容中带了些危险的气息。
杜温察觉到孟承琛语气中的不悦,连忙低声下气道:“事发突然,下官不免有些慌乱失了分寸,冲撞了王爷,望王爷见谅。” 这宁王还真是个不讲道理的主,把人绑来还怪他无礼,杜温心中嘟囔。
“杜太医是我那三弟的心腹,本王若是正儿八经请你来,怕太医未必赏脸。”
那也不能把人打晕绑过来,堂堂大简国亲王竟使出这般下三滥的手段和深山的土匪有和区别,他杜温好歹是当今圣上看中的御医,这宁王可真是太过肆意妄为。
屋内的烛光昏黄,对上孟承琛阴鸷的目光,杜温敢怒不敢言只得勉强的扯出一个讨好的微笑:“王爷这是哪的话,您召见下官怎敢有不见的道理。”
“行了,本王也没工夫和你扯这些客套话。近来本王听闻一件有意思的事,杜太医有兴趣听一听吗?” 孟承琛先好似不耐烦摆了摆手,转而又一脸兴趣盎然发问。
孟承琛变脸速度之快,性子阴晴不定让杜温瞠目,“王爷请讲,下官定是洗耳恭听。”
“本王听闻你每回都在我皇后弟媳的汤药中加些‘佐料’,更有意思的是这竟是我那三弟出的主意。”
杜温听了这番话惊出了一身冷汗,脸上血色刹然褪去,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瞧着杜温不打自招满脸惊恐的模样,孟承琛似真心觉得有趣般笑出声来:“哎呦,没想到我那三弟心还挺狠,但太没出息竟对自己的女人出手。”他还啧啧了两声,大有几分对自己弟弟不成器无奈的意味。
“我的弟媳已经怀有身孕,杜太医怎么直到今日都不告知?”
“皇后娘娘并未有孕,不过是……”
“行了,杜太医别在本王面前编瞎话” 孟承琛打断了杜温,他用手掏了掏耳朵表示自己的不耐烦,“既然老三也不想让这个孩子留下,不如本王帮他一把。你就凭着在本王面前装傻充愣的本事让严家那丫头继续乖乖把药喝下去。”
孟承琛笑起来让杜温不禁联想到吐着信子的毒蛇,扬着头乘人不备时用充满剧毒的牙狠狠咬上一口。杜温本能的感到危险想往后缩,但他此时被牢牢的捆着动弹不得。
杜温不傻,听了孟承琛所谓的“帮一把”,便明白这宁王就是想借着他的手害死皇后肚子里的皇嗣:“王爷,这万万不可啊!”
“不可?本王和老三那个容易心软的草包不同,对付不听话的蠢货,他不过是把人发配到北漠罢了,而本王会杀了那蠢货还会杀了他全家。”
孟承琛病态扭曲的笑容,让杜温遍体生寒,如果不照做他和家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公主,属下派人追查至北漠并未寻得杜温的行踪,手下之人多番打探得知此人早在半月前就已病死,人就被埋在边界一带。”丁已受榕姝之命追查杜温,派出的密探追至北漠却只得到杜温的死讯。
人竟然悄无声息的死了,榕姝眉头一紧:“他的家人可还在倾州城内?”
“属下又命人追查其家人的行踪至蜀南,原来杜温早已在蜀南山中置办了一处房屋,他的妻女及老母亲都逃至此处。但属下的人赶到时还是迟了一步,一家老小遭人暗杀。只从屋内搜出一封杜温给他夫人的亲笔信。” 丁已将书信呈上。
杜温家书中写道:伴君如伴虎,为夫办事不力触怒龙颜,此番被流放至蛮荒之地今生恐无法再踏足故土,可怜独留汝等孤儿寡母艰难于世,为夫倍感惭愧,若有来生定加倍偿还。
操纵这一切幕后之人难道真的是她的三哥?! 让自己的皇后服用避子汤药,即使是明知婉姐姐已怀有身孕也不愿收手,而后担心事情败露便将杜太医一家老小赶尽杀绝。
榕姝不明白原本温润纯良之人怎会有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一面,榕姝被巨大的悲哀与寒意所裹挟。
难道皇权真的能让所有沉迷于它的人都变成怪物,没有人间情义只有算计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