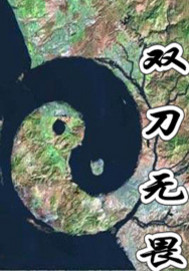大运十七年,十月初四,寅时五刻,从六品监察御史周琼正经过宜德门。这座青色城门乃太祖皇帝时修建,历七年而成,据说是仿唐宫门制样所建,远远望去,大气开阔,竟有几分贞观大治的风光。只是岁月如锉刀,削去了许多气势。今日一看,或是多年未曾修缮,昔日磅礴的宫墙竟有了几分颓势。
如今秋已深,正是霜重时节,哪怕是正当壮年的周琼,也耐不住初晨西风的磋磨,同其他人一般,加快了脚步。
正赶着路,忽觉一阵风从后袭来。又觉有人轻拍自己肩膀,周琼回头,见到了一位身量六尺有余七尺不足的清秀官员。那官员官帽微斜,气喘稍吁,呼出的热雾中,一双明亮的眸子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子岳,”周琼微笑,与他并肩而行。此人姓韩名瑜,字子岳,敦穆侯次子,也是周琼同期之中,交好的友人。(同期,古代同一场科考考中的进士们便是同期。)
“衍之,”韩瑜一脸笑容,双手交叉揣在官袍之中,怀着笏板,朝着周琼道贺,“恭喜周大人,喜得千金啊!”
周琼想到了家中妻儿,亦是心中愉悦,道了句“多谢”。
“咦,周大人真是客气,”韩瑜略微加快了脚步,“若是真想谢,不若我做东去,你出钱,叫上刘彦除他们,去樊楼,好好晏饮一番?这岂不美哉!”
周琼知道他喜热闹,但记挂妻女,婉言推了他,有承诺日后亲自宴请,这才糊弄过去。
二人又扯了些留仙居的酒,相国寺的粥,又绕到了朝政上。
“也不知今日能不能见到官家,”韩瑜收敛起了笑容,正色望着东北方向。那里是宸宁殿,也是当今官家的寢宫。
周琼这次没有马上接他的话,深色也严肃起来,想起了近几月来坊间的传言。今年三月,当今圣上在柳贵妃处突然昏倒,一连昏迷了数日,后来虽无大碍,但官家的精气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糜下去。也正是在这之后,有些来历不明的传言也开始流传开来。
“‘天子不久,立早当继‘“,韩瑜瞧了瞧左右,往宫道两旁走去。又马上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问道:“这首来历’不明’的童谣,衍之也听说了吧。而撒播它的人,衍之心下也有了推断吧。”
立早,立早,章也,周琼叹了口气,却依旧没有说话。柴章,当今圣上第六子,亦是唯一成年的皇子。及冠后,获封楚王,邑千户;其母刘氏,母凭子贵,也被追封了昭仪的位分。这位楚王,和他的同封号的项王一样,好大武功,自矜功伐,几年前还闹出贪赃军饷的丑闻。在官家养病期间,更是私自动用禁军,惹得官家不快,病又重了几分。
而官家侄子,安王,自官家生病以来,左右侍奉,寸步不离,民间大有“安贤王”美誉。因此,近来官家愈发亲近安王,疏远楚王。楚王因此必心急如焚,为了皇位,竟用了这样荒唐与愚蠢的办法。官家虽然昏庸无能,又常常“体弱多病”,但当朝多年,绝不会看不穿这样的伎俩。但过了好几个月,官家仍未对此有所行动,难道是要立安王……
韩瑜见他愁眉不展,倒是有了好为人师的兴趣:“衍之读《史记》,是否记得一只在破庙外,叫’大楚兴,陈胜王’的狐狸?”
“你是说?”
“衍之在想想,秦末乱世结束后,兴的是谁?王的又是谁?”韩瑜继续卖关子,吊人胃口地说道。
“那时候,兴的不是什么大楚,王的更不是什么陈胜,”韩瑜低沉着说道,“楚王动作只是螳螂捕蝉罢了。真正的猎人,还在身后”
周琼不可思议地看着韩瑜,又压低了几分声音,“子岳,慎言!”
他们瞥了一眼周围,临近大殿,周遭的大臣们逐渐多了起来,默契地没有再说话。两人一直沉默地走下去,心里却像沸腾的开水,翻涌着许多思绪。
西风飒飒吹过,就像最开始,原本吵闹的官员也安静下来,只剩下风的声音。不过,他们没有听到,在不远的皇宫之中,有着各种各样、极其丰富的声音。
汴梁是个好地方,春日有牡丹,夏日有青荷,就连肃杀的秋日还有红彤彤枫叶和好看的霜花。郭彤持灯坐在窗边,偷偷打开一条缝,瞧着院子里枫叶和叶片上的霜花发呆。
郭彤是公主府郭家的二小姐,当年世宗皇帝册封的秦阳大长公主的孙女。小时候,靠着父亲的功劳,又得了县主的封号,越发娇蛮任性,闹得公主府鸡犬不宁。可到了如今,出嫁了,成亲了,又生了一双儿女,坐享齐人之福,却又想起了当初豆蔻之时,摘枫刨霜、折荷戏水的天真日子。
郭彤正犯着迷糊,想着过去,就听到一道锐利的声音——
“我的天爷啊,县主,小姐,,您怎么又坐在窗口。”
说话的是秦嬷嬷,是自小陪她长大的奶娘,平时做事雷厉风行,但对她倒是十分温和,不过可能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她越发啰嗦起来。
“您这刚出了月子,怎么受得住这西风?”秦嬷嬷连忙走上来。
郭彤恋恋不舍地合上窗,靠着着秦嬷嬷,回到了床上。可她又实在是睡不着,秦嬷嬷就寻了个软垫,扶着她坐了起来。
郭彤此下心绪万千,半响没有说话。有过了一会儿眼角下垂,作西子捧心之态,声音细细地说道:“嬷嬷,我有些想以前公主府的日子了,好想,好想再当一回公主府的小县主啊。”
秦嬷嬷闻言颇有些心疼,但伺候过公主府两代女主人的她立刻反应过来,这小县主怕是被闷坏了。
也是,做了快十个月水晶人,每天被人用褥子、棉花一层层包着;安胎药、调理汤一碗碗喝着,这自小活泼灵动的小县主,又怎么能忍受的住呢。这想来,秦嬷嬷心里又是一阵心酸,不过,为了县主的身体,她只得宽慰道:“县主怕又是睡迷糊了,好好的,怎么说起梦话来了。”
“难道老爷待县主不好?满京城看过去,就数我们公主府的二姑爷最出众了。”
秦嬷嬷又给郭彤披上一软烟罗外衣,又起身去拨弄炭火,“县主仔细想想,自您成婚以来,咱们老爷待县主可是一等一的好,这满院子牡丹、枫树,哪株不是我们老爷亲自种下的?还有,那次琼林,宴官家在宴上见我们姑爷诗写得极好,要赏我们姑爷。我们姑爷什么也没要,就向陛下讨了两株曲苑新荷,送给小姐当聘礼。”
郭彤愈发羞涩起来。秦嬷嬷虽在外间拨弄炭火,但眼神却一直在郭彤身上,瞧见这种小女儿的羞态,便觉得有效,便将她听来的,全部一五一十,添油加醋地说了起来:“姑爷人好,模样也好,更关键啊,是对小姐好。虽说姑爷家世不显,但我们公主府什么大富大贵没见过,这家世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了。”
“再说了,这姑爷可是小县主自己榜下捉来的贵婿,哪能反悔的啊。”
郭彤听了这些,脸上红晕更甚,十分不好意思,只得娇娇的骂道:“嬷嬷也坏了,又拿我取笑。”
秦嬷嬷见她这样,心里也暗暗松了口气,暗暗想着:男人们只知妇人生孩子是鬼门关,对于妇人生产之后这的调理、舒缓大多一窍不通。幸好这二姑爷和顺,每日下朝之后总能带回些新奇的小玩意来哄县主,才让县主没有什么大的心结,让她这次这么容易哄好。
“嬷嬷,相公出去了吗?”郭彤柔柔地问道,又示意秦嬷嬷过来坐下。
“老爷寅时二刻走的,走前嘱咐老奴,要老奴好生照看小姐”秦嬷嬷坐下,又听她声音里又参杂着一丝疲倦,便苦口婆心道,“入秋了,夜长着呢,小姐再睡会吧。”
郭彤点点头,微微起身让秦嬷嬷拿走靠枕,却不小心碰倒了昨日周琼带回来了的白玉瓷埙。瓷埙倒是无事,却是磕出了一根竹签。秦嬷嬷连忙捡起瓷埙和竹签,在检查之后,便将二者递给了郭彤。
“可吓坏老奴了,”秦嬷嬷感叹道,不过又马上笑起来,“老爷真是把小姐放在心上,这种玩意都能找来哄小姐开心。”
郭彤脸更红了,让秦嬷嬷下去。待她走了,郭彤才拿出竹签,仔细端详。这是一根花签,上面画着一枝紫薇花,下面用簪花小楷写着一句诗“清风拂花送紫气,逢难转安遇贵人”。
郭彤轻轻拂过竹签,这竹签倒不像是竹木所制,倒像是一块厚朴的白玉,倒是上面文理可以看出它的材质。郭彤把玩了一番,揣着这根竹签,顺着困意,沉沉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