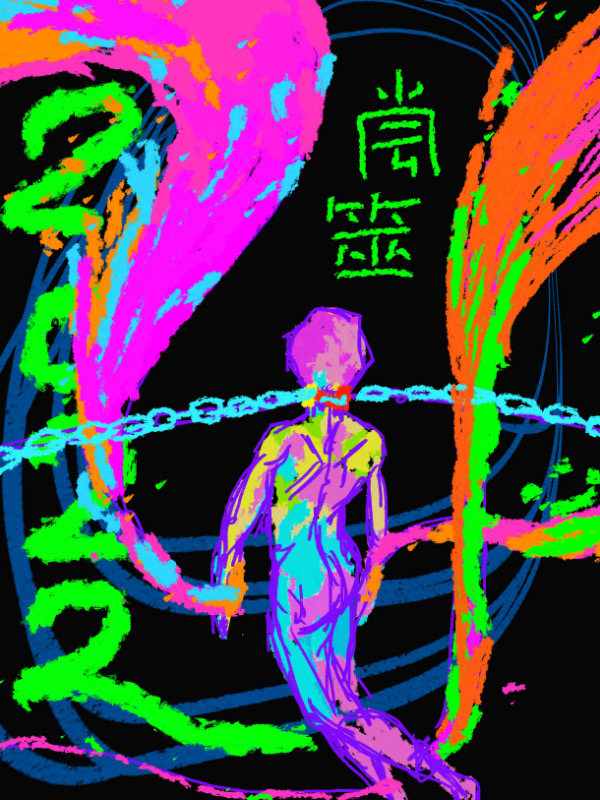李红豆走上前,帮他拍掉身上的积雪,轻轻说道:“哥哥久在军中,有些事可能不知道,今年长江大水,从九江一直到武汉,田地淹没掉十中无剩一,百姓无法生存,饿死的人遍地都是,现如今汉也是遍地灾民,那些人卖儿卖女已是常有的事,原本有些人家和机构以及学校出面接济灾民,灾民也许饿久了,人又太多,屡次都遭到哄抢,失了人心,现在能接济灾民也就那么几家机构了,这会儿也许会儿有灾民在冻饿中死去。而国民政府对这些不闻不问,依然在和学子,工人在对抗,唉。”
听到这里,段逸飞双挙紧握。“长江大水,沿着长江,已经有多个省出现灾民,报纸只是简简单单说过几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想到会如此严重,现在外患有日寇占领东三省,他们手中握着重兵却还指望国联之人,当真可笑。地方政府连灾民都是视而不见,却依然和一群工人孩子在斗智斗勇,可笑我五年的青春,为了这样一群人,丟了我五年的青春……。”
“哥哥,你不要这样,我害怕。”
段逸飞跌坐在雪地上,“五年之中,我为了报效这个国家,偷偷去留学,偷学别人先进的科技,回来后又投身军校,还信誓旦旦的说要效忠于他,我错了吗?”
李红豆急道:“哥哥,你没错,错就错在这样世道,错在这样的国民政府。哥哥你那么聪明,肯定能想明白,咱报效的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府……。”
目光酸沚,很想流泪,却一滴也流不出来,段逸飞象是没有灵魂一样,任由李红豆扶着,空洞的安慰着,也许年纪小,不怎会会安慰人,毕竟她才十八岁,整整小他三岁。
“别怕,我只是感叹我这几年的努力白费而已,你不用害怕我会伤害你们。”段逸飞感觉到李红豆扶他的手在颤抖,仿佛又回神来。“若大的奉天军集团马放南山,刀兵入库,不抵抗政策就让日寇长驱直入进入东北三省,唯有马秀芳带着爱国将士抵抗三天两夜,不敌被俘,真的悲哀。”
“哥哥,你的精神不太好,我先扶你去休息吧,从小你的身体就不是很好,要不是黄德正师父,你身体吃不消……。”
“我不要紧的,现在体质很好。日寇的欲望不可能只有东三省,估计全国都填不饱他们。而在南京蒋委员长却在逍遥快活,不积极备战,指望国联的人,唉,二十九军呀,那里是进内陆的门户,你可得看好了,如果丢了……。”段逸飞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身边的李红豆说的。看着段逸飞伤了心神,李红豆欲言又止,不知道怎么才好。
“红豆,你把逸飞送回房休息吧,让他睡一觉应该没事,他这是劳累所致。”李红豆这时才发现父亲和段荞在大门口看着她俩,脸色微微变红,答应一声,便扶着段逸飞向房间走去。
“唉。”“这孩子就是倔呀,当初我是把他往做生意上面陪养,以后好接下我的生意,没想他却向往军旅,一不溜神被他骗了几年。”段荞扶着额叹息一声。
“段兄,事已至此你现在叹息也没有用,逸飞这孩子好强,自信,又有上进心,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许他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你也不用介怀,他现在虽然经历一些挫折,也许对他将来成长会有一些好处,毕竟他年龄还不大。”边上的李子墨安慰道。
“道理我都懂,只是有些不甘心,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兵荒马乱,东北有日寇,北方有黄毛鬼子,延安有共,南京有蒋,一个不好,那是全家的性命安危的呀。”段荞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说道。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李子墨听到段荞的有些感吾,“段荞兄,现如今这个状况是你我不想看到,也是天下百姓的灾难,你有什么看法?”
“我能有什么看法,我只是个商人,从商人的利益上看,北方的黄毛人虽然虎视眈眈,但他们国家在西方也有战争,估计不会参与我们国家战争里来,日寇虽然占据东北三省,他们扶持满清伪政府,满清政府本来被推翻掉了,现在他们又扶持起来,老百姓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日寇迟早要滚蛋,现在剩下**和老蒋的内战,民心就好比利益,谁能玩得转,这天下就是谁的。”这些见解是段荞这些年积累出来的,这就是常与洋人做生意的好处,也是他看事情的毒辣之处。
这些话也是令李子墨暗暗点头,他很佩服段荞做生意的眼光,精准而毒辣,“虽然话是如此,但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外敌虎视眈眈,而蒋先生现在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而**隐藏在暗处,看不透呀,这场动乱看来要很长时间,老百姓苦呀,唉……。”李子墨叹了口气接着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老爷,吃饭了。”堂屋里传来碗筷声,以及女人呼喊声。
夜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而降临下来,冬天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偶尔有些雪花在窗户的烛光中还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