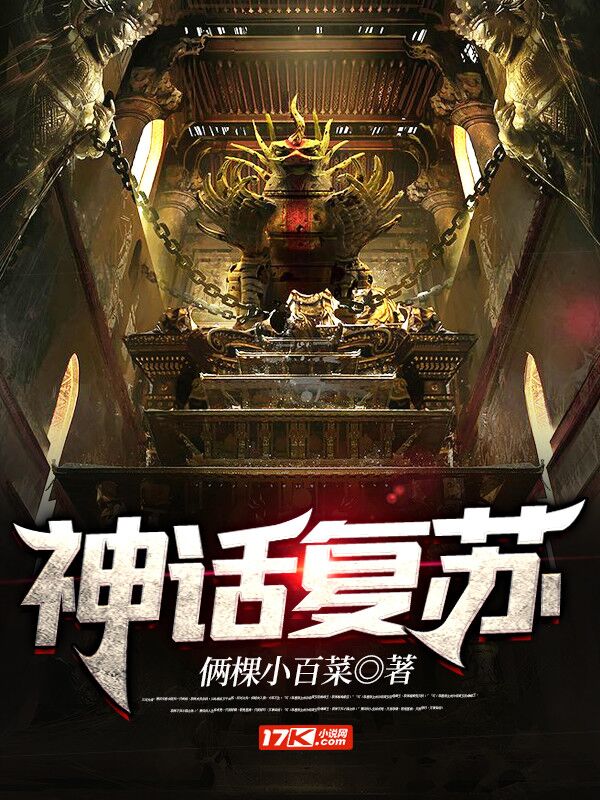今年春天雨水不少,入了夏却像是雨龙王休假去了,竟是一丝雨也没下过,郭老头今天就开始带着儿子们去河里担水浇地了,正是苞米抽穗的时候,雨水跟不上,今年的收成也就没有多少了。离地进的河里也没有多少水了,要是浇不完就得去更远的地方运水。郭家几乎是全家齐上阵,除了留郭老太和老四媳妇在家做饭,郭三郎看着铺子,其余人都去了地里。力气大的推着车,担着水桶,力气小些的就留在地里浇水。郭老三已是跟着推车运了两趟的水,就有些头晕眼花,坐在地头歇了会才好些。
“老三,咋样了,不行回家躺着去。”郭老头带着地里的人浇完了这趟运的水,等水的功夫,走到地头,拿出烟袋吸了几口,问郭老三。
“没事,爹,歇会就差不多了。”郭老三说。
“中,你就在地里浇水,别跟着去了。”郭老头说。
“嗯。”郭老三点点头算是答应。
“爹,有个事跟你老说说。”难得爷俩单独说话的机会,郭老三就和郭老头提起要送郭小虎去学堂的事。
“爹,小虎也十二岁了,在武官里祁馆主也教了他些书本的东西,我合计去学堂读两年,看看能不能也考个秀才啥的。考不上也没啥,上两年学堂也能找个好差事干干。你老看咋样?”郭老三和郭老头说。
郭老头眯着眼,狠吸了几口烟,像是在思考郭老三说的话。过了一会,才磕了磕烟袋锅子。
“老三啊,等浇完了地,我有话和你们哥几个说。小虎读书这事,到时候再虑虑。”郭老头像是终于下了什么决心,和郭老三说。
“那,中,等浇完地再说。”郭老三答应到。
郭老头带着郭家众人,足足的干了七八天,才把三十亩地都浇了一遍。日头偏西,还没落山,郭家终是浇完了最后几垄地,拖着一身的疲累归家。郭老三这些天和大家一起在地里劳作,竟是撑了下来,赵氏不由心里宽怀,自从调换了药方子,三哥的身子更是一天比一天好,她也算放下一桩心事。洗了手脸,郭家人都围坐在桌边,今天的晚食尤其丰盛,每桌都有一盆炖鱼,一盆土豆炖肉。这些天担水浇水着实辛苦,郭家人又不是惯做的,难免更费力些,估计着今天能完工,郭老头早上就嘱咐了郭老太太,晚食做的好些,一是慰劳大家,二是他晚食过后要说事,也算是先给大家伙点补偿。
郭月从十来岁上就每日早起出门做工,月中月末各休息一日,在武官里做工、闲时还跟着镖师们学着比划几下,这些日子干活并不觉得辛苦,略微晒黑了些,到更显得健康。大房的大姐儿郭菊端着饭碗,只觉得手腕都要折了似的,不由暗暗的瞪了郭月一眼,年底就是她的婚期了,这几天下地,她已是晒黑了不少,手也粗糙了,指甲边缘还起了倒刺。几个姐妹每人顺着一条垄浇水,她左边是三房的郭月右边是二房的郭莲,郭月浇到地头的时候,郭菊和郭莲才将将的浇了半条垄,郭菊就让郭月帮着她一起,她可以歇一歇,也不显得干的活少。可恨郭月留了句“大姐,你慢慢干,不着急”就拿着桶又去抬水了。这会看郭月还是很有精神的样子,怎能不让她咬牙切齿。
“都先别走,我有话说。”郭老头说。吃过晚食,儿媳妇们收拾好了碗盘桌子,郭老头发了话。郭家各房人都在主屋找个地方坐下。
“爹,你老有啥事?”郭老大挨着郭老头盘腿做在炕里,他旁边是郭大朗。
郭老头停了一会,似乎是在组织语言,也似乎是不知从何处说起。郭家众人都看着郭老头。
“上个月铺子商税又涨了,听说是到年底还要涨。今年到七月份,咱家这杂货铺子收入还不到四十两。大朗去府城考试就花了五十多两,老四坐馆六郎不要束修。四郎、七郎,束修每人五两。八月份老四去府城秋闱考试,还得准备一百两。笔墨纸费、家里吃饭、穿衣。年底菊儿嫁妆和三郎的聘礼也该准备起来,还有酒席的花费。这两年田地赋税、商税,一直涨,咱家挣得少花的多,我和你娘这也没啥存银了。”郭老头给家里人算了账,说了家里的钱财收入。说了一段话,郭老头点了自己的烟袋锅子,吸了一口。
“咱家就这三十亩地,还有这个铺子,是大头的收入,这些年添丁进口,你们兄弟子侄启蒙科考,家底花的是差不多了。眼下家里这大头的花销就是两门亲事,还有老四的秋闱。我和你娘棺材本都拿出来,还有七十多两,你们兄弟商量商量,接下来咋办。”郭老头一口气说完,又狠狠的吸了一口,把自己呛的一顿咳嗽。
“少抽点吧,保安堂的郎中都说这烟吸的多了影响寿命。”郭老太太给郭老头顺了顺后背。
“讲不了那个,几十年的老烟枪了。”郭老头止住了咳嗽。要是有办法,他也不想把自己无能为力放到子孙面前,可眼下家里花钱地方多,挣钱是越来越少,老三又提了五郎上学堂的事,老四秋闱的一百两还只是路费和食用的花销,前几天他岳家还说结实了什么学正大人,五百两银子能递文章上去,得了学正的指导,秋闱必过的。老四早就拿这事和他商量过了,可这五百两银子,卖了他这把老骨头都不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