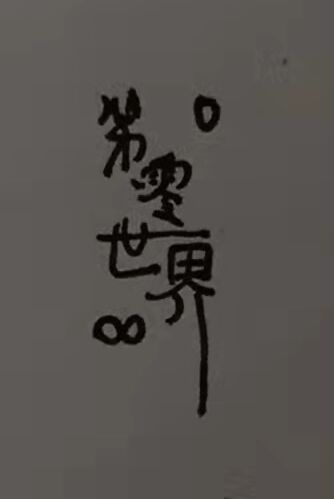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长了十九个年头,不完全地目睹了军阀马步芳残暴统治青海百姓的状况,他为了维护反动地位,就年年拔兵,天天要伕(差役),所摊派的粮、草和税款,多如毛,重如山,公家的员差天天下来催粮要款,保甲长和乡老,日夜来找人的麻烦。先说拔兵,男子一到十八岁就要当壮丁训练,每年拔兵一至二次,年复一年,兵役遍及各家,形成家家有兵或一户两兵,我家兄弟三人,就两人当兵。年轻人赶走后,丢下老弱及妇女种田,许多妇女守着空房,一些许配给兵的姑娘,无法结婚,有的人听到女婿要开发,干脆把姑娘领到营盘里在男人跟前绾上发结,就算为完婚。
更罕见的是,在兵开发时,有一个人竟把姑娘领到兵坐的汽车前,与兵哥完了婚。当兵的人们,没有服役期限,除了伤残以外,都为“气断工满”,如哥哥逃了,由兄弟顶替,户里逃了,由族内顶替。兵们除了打仗以外,一律驻扎在乐家湾集训,常受酷刑毒打和病、饿之罪,时常往家里要钱、要物、要干粮,还要给上司的“礼品”,自杀的兵也多。马家军营,实属人间地狱。百姓常说:“乐家湾,鬼门关,眼泪汪汪淌不干。”再说上粮纳草,当局定给百姓“一籽数粮”的任务,即上缴公粮数超过下籽数几倍甚至十倍,除了“大粮”以外,还有一文不给的所谓“银买粮”,那时我家上缴的公粮达一千五百斤以上,上缴麦草四百多斤。上缴粮的地点,也十分遥远,有时在西宁、鲁沙尔,有时在贵德、湟源。
提起苛捐杂税,更叫人头痛,公家年年在要:兵款、马款、警察款,献金款、慰劳款……等等。月月在要煤车款、民骤款和税款。庄堡上天天还要下乡官吏的招待费、辛苦费、马汗费、送礼费和一切杂费。这样一来,百姓每户每月就得交付银元三至五元(每元值小麦 50 斤)。有一年马步芳刮了一次“丈地款”,百姓每户上缴银元达几十至百元以上,逼得人们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百姓们气愤地说:“公家要这款、要那款,唯独没要放屁款。”
公家摊下粮款时,说风就是雨,百姓哪怕典身子卖命,也得如数完清。大批官吏下乡催收,他们每到村里时,就打的鸡飞狗跳墙,百姓纷只得纷纷逃窜,乡老们赶紧倒马料和杀鸡宰羊。他们把百姓任意捆绑、吊打,甚至拉进班房。此外还有庄上的保、甲长和乡老们,好像“瘟神“一样,他们也腋挟账本,手拿皮鞭,天天挨门逐户地催粮要款。一到”冬至“时,乡老更换、交接手续,对百姓催的更加火急,对粮款不清的人,不是打马步骂挖苦,就是拉物、抄家,使百姓惊恐不安,叫苦连天。对于上述形势,百姓们叫做“不见阎王鬼打死”。有一年的春节前,我家开销很紧张,无奈把一头猪宰了,由大哥运到西宁卖肉,当晚大哥回来了,把肉钱交给了母亲,母亲把那一卷票子刚放到箱子里,正要商量咋开支时,忽听得一阵急促地敲门声,去开门一看时,不好!乡老来了。乡老进来后,就笑嘻嘻地说:“今天你们卖了猪,再莫说没钱的话了。”经他一算后,将肉钱全部拿走了。当时那票子上还散发着大哥怀揣的热气。气得一家人瞪着眼睛不说话,一大会儿母亲才说:“你不知道,今天卖猪之事,鬼孙们早打听好了。”
关于拉伕当差,那是没完没了的事,马家当局一年四季都要民伕民骤,大部差役是:修路、栽树、运输、建筑,还有捻毛线、做军鞋等。每户所摊工日达一百天以上,大部分男子被赶去当伕儿,自带工具,吃的干粮、炒面,睡的潮地,常受打骂、折磨。提起捻毛线,实在煎熬,发来的羊毛掺杂不堪,而且发毛多少,就交线多少,损耗部分由百姓添上。做军鞋之事,当然是女人的份子,一切材料全要贴上,没办法的人,只得拆上衣物来完成。
有一年马步芳调集壮丁数万名,在廓莽寺天然林区伐木。当时把我大哥赶去做壮丁,当“伕儿”(注:伕儿即差役),还把一些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士也赶来做劳役。当局为了提高工效和防止壮丁逃跑,曾派亲信马步銮的一团队伍到现场监工。该部官兵经受法西斯训练,个个凶狠恶毒,对壮丁发号施令,鞭打棍逐。还有那些保长、乡长也来到工地狐假虎威。壮丁们一到后,先在北川河上修了一条长又宽的运木渠道,并在林内修了许多滑木道。工程开始后,工地上人山人海,壮丁们好像奴隶,个个挣扎奔波,人们砍的砍,拉的拉,还有的人在河上又捣又运。无数大松树喀嚓倒下一片,大批木料堆积如山,人、木忽忽闪动,林区乱成一团。还有马家兵的吼骂声,壮丁的哭喊声,以及木头滚动声,不断传入耳边。马家兵们在工地上星罗棋布,十步一哨,百步一岗;除了荷枪实弹外,还拿皮鞭和树棒,对壮丁沿途逐个抽打,强迫大家跑步拉运,丝毫不得怠慢。壮丁们没有拉木绳,只得用山草和树皮拧绳,白天拉断晚上又拧。此外没有休息时间,白天黑夜地苦干,晚上累倒后,又被打醒。吃的炒面,喝的生水,人们个个气息奄奄,人鬼难分,有些人被打、饿、病而死,还有些人被树压、水淹而死。在四十多天的伐木中,马家兵对壮丁搓磨一时未停。一天到晚把壮丁们打得个个遍体鳞伤,动不动还把人吊在大树上。更毒辣的是,把我村的壮丁魏守奎,竟用军阀酷刑来打“背花”,就是把人脱成裸体,用皮鞭在背上抽打,直至皮开肉绽,血肉横飞时方为罢休。我村有个魏占奎,他从十九岁就当了伪兵,身上的旧军坏作风染得很深,正巧也来该工地管工。他对壮丁们的吼骂、殴打比谁都狠。有一天他打人打得眼红了,竟把自己的一个表弟也抽了一鞭子。当时那个表弟又疼又气,但却羞里带笑地对占奎说:“姑舅哥啊,我把你认得呀!”,魏占奎面色阴沉地道:“认得了下去再说,这里我就这个办法”。可怜的我大哥,他和广大壮丁一样,在上述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虽未被致死,但饱受了劳累和皮肉之苦。当父亲去工地看他时,见他面黑肌瘦,发如囚犯,全不像个人样儿,一霎间父子二人的泪珠,都跳出了眼睑。在旧社会里,大哥是一家人的顶梁柱,也是千万个马家奴隶之一,忆起此事,令人心酸。还有那个阳坡台的党成才,在伐木工地被驱赶、殴打后,得下了后惊病,回家后睡觉时常做噩梦。有一个晚上,他梦见伪军手持皮鞭凶狠地追打来了,他立即跳起,拼命奔跑,忽听得脚下哐当乱响,手脚也有痛感。慢慢苏醒后,才发觉自己在做噩梦时跳到了厨房的锅台上。这时他虽然奇怪地笑了,但心还在不断地乱跳。那个黑暗的旧社会,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