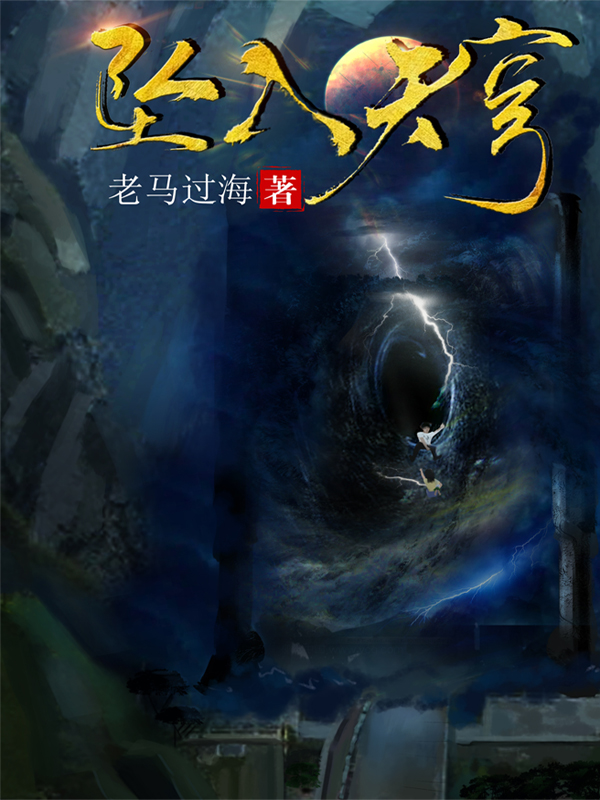“这中间的十九我尚未如何见,便没了踪影。
‘他去哪儿了?”我好奇相问。
‘你说谁?’我的弟弟封顾放我说。
‘那个十九。’
‘送人了。他是个粉白面皮的好看男人。’
‘我只同你寻他的去处,你同我说这作甚?’我疑惑不解。
‘雁过留声,夫子今日教的,人过的话,便是不留名,也该是要给人心里留给影儿的。’
‘那么大约是记不下,府内这样的男人太多了。’
……
“金秋送爽,月朗星稀,王府近日里少有太平。
首先,是那个标号为二十三的男人,猥亵了我的乳母安氏,具体时间不得而知。
只晓得那天乳母半裸着身子从堂屋内跑出来,疯言疯语说下了好一通,脚下鲜血淋漓的,恐是要生了冻疮。
又很奇怪。
我便走上前问询道‘你怎么不穿鞋?’
她答我说,‘以后都不能再穿了。’
摆摆手,一副不欲多言的灰败模样,叫我识趣地闭了嘴。
次日,当第一缕阳光挠我脚心的时候,我醒过来,睡眼朦胧里,我在床榻根儿上发现了吊死的她……
不曾有穿鞋子。
也不知她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迫我替她报仇?还是迁怒怨憎于我。
亦或许是这二者兼而有之?
总之,她走得并不安详。
死不瞑目的叫我看出了她的不情不愿。”
这封email很长,难得得地写了几面屏。
洋洋洒洒千字有余,分了上下两个部分。
许是无课无聊,许是自由散漫惯了,目前的封疆有很好的兴质细细将它读完。
“这一切来的毫无征兆,我几乎就是要疯了。
不,也许征兆还是有的。
可惜被发觉的实在很晚。一切都来不及了。
昨日夜里,她为我偷藏了糖葫芦,红艳艳的,有好几根,味道都不大对头。有些涩。
‘这是哪家的啊?’我扭头问她。
‘西街那家的。’她无比平静而镇定地骗了我。
‘哦,那可好远。’我彼时说。
东西两街相隔半城有余,我早该想到这点的。
那么远啊,怎么会有人为了糖葫芦去呢?
但或许是出于多年的信任与依赖吧,我不疑有他,麻溜地吃了个干净。
吃完整个人精神头都不好了。
待到了熟睡以后,便人事不知……
对于这一点,我早该有所发觉的,乳母怕我坏牙,素日都不肯给我糖吃。
她爱藏我的糖。
也爱管束我。
她的死相很难看。
脸色发青变玄,舌头伸得半尺来长,耷拉着大在白绫之上,眼皮子半睁半合地割裂开来,露出了里头浑浊不动的眼珠子。
这叫我良久才反应过来,怔愣愣地观瞧半晌,脖子都酸疼了,竟然不觉得很害怕。
也没有失声。
大约是觉得她可怜吧。
亦或是她善良,纵然化作了厉鬼也不会害我。”
这个封疆冷静到可怕。
封疆一度腹诽着,感觉脊梁的缝隙里,有穿堂的风簌簌而过。
又拥了些被子上来,盖得更严实了。
到了这周的尾巴,email又有了更新。还是谈论那件事的。
“母亲不出所料的,查出了前因后果,赶走了二十三,我想过要乘机溜出府去的,好棒打落水狗,赏给他那个腌臜泼皮几个耳光子,最好再朝他唾弃几口,就吐在他那张引以为傲的漂亮脸蛋之上。
这可正是疯狂可怕的想法。
但是因为有理智牵拉,未能成行。
还有……
我无意间听到了另一种传言,说二十三其实并没有走。
而是直接被人用半截绳子给摸黑勒死了。扔到了城墙根底下。
是的,就是在王府里头动了手。
当晚给他取下麻绳的小厮用宫灯打眼儿一瞧,这绳痕深可见骨。甚至有的骨头已经稀碎了。
可真是惨。
但是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只这么一想,我又收起了自己那可笑无用的大悲悯之心。
还有一点,说这话的不是旁人,正是我那便宜弟弟——封顾。
所谓童言无忌,也许这些传闻都是真的。”
“乳母没有头七,夫家人都不要她了,乃至不肯施舍一抔葬身黄土。
她被人一袭帘子卷着,三日以内下了葬。
于此前,我为她收拾好了遗容,穿上了漂亮的绣花鞋子。
是正红色的。
但有人担心她因此而变成厉鬼,偷摸着给换下来,我只做不知。
并嘱咐负责此事的下人,要给她安排一个好去处,最好有花有云,有山有月。”
“乳母的儿子还没有来,我在王府等了他足足有四日,寒鸦送走了一波又来一波,也不曾见他的踪影。
‘她的月例银子还没有结算呢,’账房先生如是说‘本来就差那么一两日了。要不直接给她的家里人送过去?’
‘想要便自己来取好了。’我说,语气不善。
言毕,那头母亲停下了侍弄花草,反身奇奇怪怪地飘了我一眼,不疼不痒的,却也很不舒服。”
……
接下来的几日里,email纷至沓来,却平添了几页空白的纸张。
可能是系统错乱的缘故。
待封疆把email全部通读完毕,差不多也到了隔离结束的时候。
那日天乌蒙蒙的,零星飘下几丝雨,不很潮湿,却很寒。
尤其是在她的马丁靴足够单薄的时候。
舍友程曦专程打了雨伞到路口接她。
二人步上电梯。
又走了几条街,穿过热闹的瓦子。
来到宿舍。
推门而入,发觉自己的床边边上,竟已是坐了个姑娘了。
这叫封疆有些惊讶。
“你动静小点,这姑娘害羞,你可别在唬了人家去。”
这方咬文嚼字嗔怪着她的人面色如桃,正是她的舍友念念。
程曦见她疑惑不解,便解释说“念念想要拍一组记录片,作为社会实践的作业。”
“那她呢?又是怎么回事?”封疆了然点头,对着程曦追问。
程曦淡笑,说“纪录片啊纪录片,这没有故事情节还叫什么记录片啊?”
“据说她的故事可是吸引人呢,寻常人都请不到的。”小四抱胸,笑得别有深意。
这么一来,封疆对女孩的故事便愈发好奇了。
讲故事的女孩年岁不大,单瞧着脸孔也不很像是会讲故事的人。
雪白的立领衬衫,灰白条纹的格格棉布裙,一头乌黑的发被束成了规矩的麻花辫,在身后摇摆。
是个会打扮的人。
她们围桌而坐。
摄像机则摆在桌的正中间。
为了制造氛围,她们还关了宿舍里所有的光源,只留一盏小太阳灯夹缝生存。
于采访者于受访者之间。
各人的面容都明明灭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