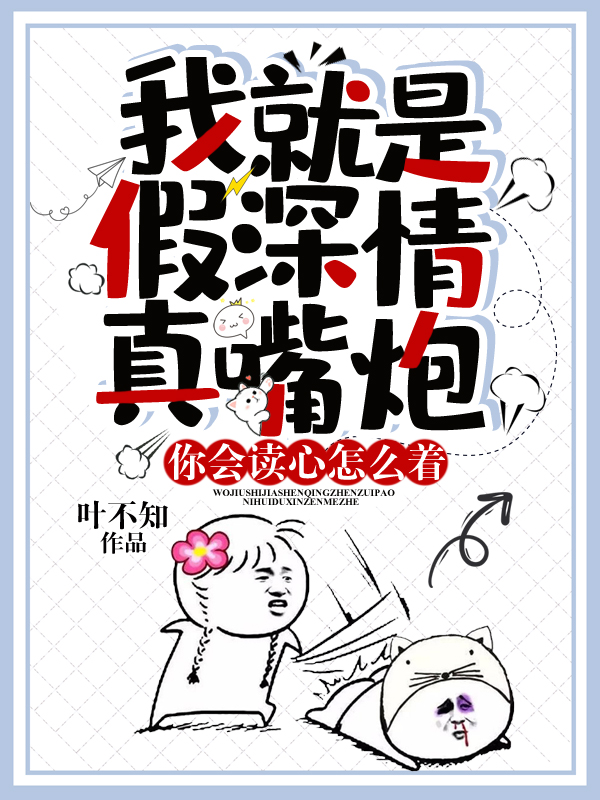4.“谁说不是呢,这搁谁瞧见了不好奇?”
“可不呢。”余敏又细细碎碎地描述着,“这男子还打算将这姑娘抵在这,说是要是等掌柜回来问问,能值几个钱。”
“我们这小地方要那么多伙计做什么?”
“可不是吗,我也这么说了,你知道那公子说什么?”
“什么?”
两人一言一语的话都传入西晚春耳里,她早已跪的双腿发麻,此时又听这二人叽叽喳喳实在心烦,干脆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松松腿。
“看吧,跪不住了。”时刻注意着她的刘二来了句。
西晚春狠狠地看向他的方向,你说就说,能压着嗓子吗?黑心的!从今以后没生意!
“这姑娘看着娇生惯养,能跪到现在也是不易了。”
“那公子说什么?掌柜不收他待如何?”刘二话锋一转又回来了。
“唉,”余敏还故叹一口气,“他说要花钱替那姑娘买口棺材。”
刘二倒吸了一口气,“这玩笑有些过了。”
“我觉着不像说笑,要我说那公子看着病怏怏的,动起手来那姑娘指不定会输呢。”余敏值夜一宿打了个大哈欠,困意也随之而来,“刘二哥,我得先回了,这交给你了。”
“得,你早些回吧,”刘二拍拍他肩膀,“对了,怎不见商大姐?”
“不知,许是昨夜又喝醉了,我不方便去她屋里看。大掌柜这两日该回了吧?”
“说不好,难得出一趟远门,想必要沿途多玩玩,你找掌柜的有事?”
“没事,”他摇摇头,“我走了啊。”
西晚春靠着木栏杆又半跪半坐的磨了大半时辰,肚皮不老实的叫嚣起来,都快晌午了师父还不回来,昨夜还说送她回去,不会自个儿跑了吧?
“傻春儿,你干什么呢?“
师父?!自己这是饿的发昏了?
“你这是被赶出来了?”萧天一一身淡水色薄袄衬得他本不白皙的脸蛋有些发黑,他自己却不觉得,还甚是欢喜地甩了把青丝,”店小二在何处,怎能如此不讲理?“
西晚春有些激动的将脑袋托在木栏杆上的空隙,好心提醒道,“师父,师兄来了。”
刘二应声朝他走去时见那四十来岁的男子脸色由晴转阴,又又阴转晴地对楼上姑娘道,“你少诓为师,那逆徒若真来了,你跑的比谁多快,还会在这等着挨打?“
“徒儿没挨打,就是跪的腿麻。”
萧天一顿感不妙这丫头确不会无故跪着,但他不信柳逆途能下山。他那一掌使了七八成内力换作别人保命都难,别说出门了,“你腿保住了?”
“那要看师父舍不舍得拿东西来保我的腿了,”她盯着他的脸,眼皮都不带眨的,“师父,你拿了师兄什么?”
“没什么,几片金叶子。”她没料到师父回答的如此坦荡,连想都没想。
“怎么?为师养他十几载,用他几片金叶子用不得?”
师父撒谎了,她心想。
“你还不起来,等着为师去扶你?”萧天一板着脸给自己撑底气,纵使心里想一个人一跑了之。
“徒儿不能白跪。”她也是一脸为难,师父不忌惮师兄,是因为他笃信师兄不敢欺师灭祖,她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同门。
萧天一心里骂道,柳逆徒不会为了你一双腿跑去提付,他自顾不暇怎会再去给自己添麻烦?这傻丫头怎么想不明白!刘二一直不走,他不能明说,
只便道,“听师父的下来,时辰不早我们该动身了。”
犹豫间,她身后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师父好狠的心,徒儿寻来不易,怎地连面都不见就走了?”
他竟真来了!萧天一心中五味陈杂,自己终究是老了,一手养大的娃已经不再他的掌控之中。
“为师也是有苦衷,来日定向你详明。先让你师妹起身,她这身子骨哪经得起这般跪。”他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傻丫头还在这,定是要编些瞎话的。
“何必来日?还请师父眼下明示。” 西晚春跪在他身后,见他红袄上散着几缕白发,心想早间似没注意到,师兄也是老了。
萧天一无从编起,索性不理他,将矛头对准六徒弟,“晚春儿!为师的话不管用了?!这男子跪天跪地跪父母,你纵是一介女娃也不可随意跪人,你还不起身?!”
“你犹犹豫豫,反倒显得你师兄心胸狭窄!”这明褒暗贬傻子都听得出来,她也不例外。
“这么听来是徒儿错了,六师妹若不肯起来,只待我跪下求她了。”说罢似真的要在她面前跪下来,她哪敢承他一跪,连忙手脚并用的从地上爬了起来道,“三师兄严重了,是晚春有错在先。”
“哪里,六师妹如此惧我,是我这做师兄的错。”
她一脸疑虑的抬头看向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客套的说辞,只觉得不对劲,这人莫不是旁人假扮的?这话打破脑袋她都不信是出自柳逆途之口。
正当她疑虑之际,楼下的萧天一看她慢吞吞的扶着梯杆下来,恨不得让她快点滚下来。这逆徒定是发现缚炼绫丢了,这回不跑也得跑了。索性他解药未到手,此刻还不会撕破脸。
分神之际,她脚下踩空脑袋就贴着木头而过,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她已经滚到了萧天一脚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