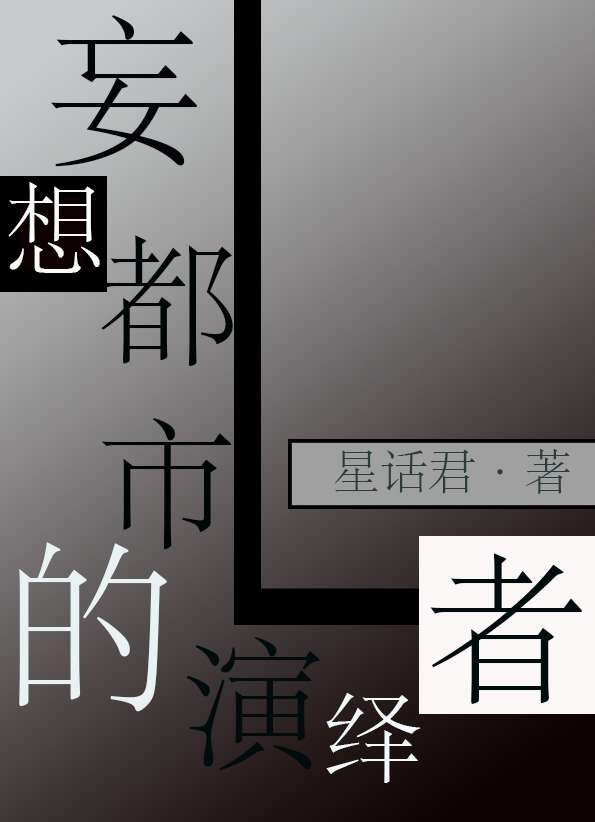我前脚刚进工厂大门,门卫大爷就从门卫室里拿着个破旧的银色手电筒,需要在桌子上敲一敲才能发出昏黄暗淡的光,仔细查看了工牌这才让我进去。
他要是披一件军大衣,长着发白的胡子就有一种沧桑感,特别是寒风瑟瑟的夜晚,哆哆嗦嗦地迈着步伐,开口前还要咳嗽两声,张开那张戴着假牙的嘴来,说话的时候感觉喉咙有一口浓痰卡着,还要硬咳几声,等那口浓痰到了嘴里,砸吧砸吧滋味,你还生怕他不吐出去,眼睛一直盯着他努着的嘴,盯了许久那口不知砸巴了多少次的浓痰,依旧含在嘴里,任凭其咀嚼吸溜,过了几分钟终于听到那口清脆忒的声音,把那口陈年老痰从喉咙提到嘴里再从嘴里吐出来。
这在旁人是断然忍受不了的,巴不得他能干净利索一些,一步到位,可这一过程却要两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最后一步,我一想到这些,直皱眉头,幸好现在是夏天,还未到那个地步,更何况门卫大爷是一个头发黝黑的老者,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我这才松了口气,快步跑进去。
夏天的夜晚还是比较燥热,跑没几步就觉得,浑身出汗,刚好下班的工人比较多,穿梭在楼与楼之间的大路上,只有车间有灯,外面几乎无光,只能勉强靠着月光才能看清路面。
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一想到明天又要上工了,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好像还没好好休息,又要工作了。阿三开着电动车从我身边路过,开到前面不远处,他又掉头回来,把车停在我面前。他认出我来了,朝我挥手。
我坐上车后座,车还没开,就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果敢? 张果敢”
我一回头看到是蔡斯洁,我拍了拍阿三的肩膀,叫他先回去,下了车,走到她面前,她的长发已经扎了起来,手里提着透明的水杯,“这么巧,能在这里见到你!”我说着。
“我刚下班呢!你也这么早下班吗?”
我本想跟她说出实情的,但转眼一想只好应对着“啊……是啊!下班就准备回宿舍了。你呢?第一天上班习惯吗?”
我们两人站在路的中间聊着天,路过的人纷纷走到两侧,避开我们,也有不少人盯着我们看。也有蹲在路边抽烟的,因为看他嘴边冒着冉冉星火。
我尝试跟她边走边聊,是往篮球场方向的,她见我走动,也跟着走了。
“我今天打了两通电话给你,你怎么没接?吃午饭的时候也没见到你?”
“嗯,我刚好被派出去干活了,在外面吃了!”这一下把我整得尴尬死了,因为撒一次谎就要用一百个谎言来圆,还不如直接说,今天休息呢!
“你们还需要出去的吗?”
“偶尔需要。好像没见到你那个紫头发的朋友!”
“哦,你说她呀!她已经回去了。”
“对了,你们都是胡浩带过来的?”
“胡浩是谁?”她眼睛里充满着疑惑。
“就是那个带你们来上班的中介啊!”我的天,她居然连中介是谁都不知道。
“那个流里流气的的人是中介啊!那我知道是谁了,我们都是同一批被他带过来的,你不是吗?”
“嗯……我也是!”挖了个坑自己跳了。
我们来到篮球场旁边的石椅坐了下来,篮球场上正在打着比赛,她像是勾起了回忆,与我说起了她大学里的故事。
“在学校的时候,晚上我经常跟宿舍友走去操场,经过篮球场的时候,每次都有人在打球,有时还会举办篮球比赛,然后每个班要派人去当啦啦队啦……我们坐在这里仿佛回到了学校,真是怀念!”
月光落在石椅旁的地面上,看着她滔滔不绝地与我讲起了学校里的事情,那些美好的回忆我只能凭借着想象尽力地去贴近她此时的睹物思情!
我向着远处望去路上一片漆黑,偶尔闪过几个人影,整片天空除了月亮外别无其他,唯独球场上那一束光勉强可以看到附近的建筑,篮球撞地的声音和她说话的声音似乎同时覆盖住了。
一切仿佛慢了下来,我不知道是怎样和她告别的,也不清楚那一晚上我们聊了多久,只知道当第二天醒来时,我已经坐在床上思考了这个问题足足有半个小时,拍了拍脑袋,这都能断片。
阿三气喘吁吁地推开我的房门,外面一阵热风扑面而来,我受到热气,风一下子把我头发吹高了许多,他带着怒气冲我说道“你知道吗?我们宿舍阳台上的鸟窝被人捅了,两只鸟掉下来摔死了。”
什么鸟窝?我感到莫名其妙……
就在我们阳台上,搭了一个鸟窝里面有两只还未成年的小鸟,我每天都去看的,可是今天去看的时候,那个窝被人捅了。
我坐了起来,穿好衣服,下了床跟阿三出门。
那是他喂了一个多月的小鸟,他每天都在饭盒里留点饭带回去喂给它们,小鸟渐渐长大,每天清晨醒来就张开大口叫着,阿三的舍友不耐烦了,每天都被鸟叫声吵醒,一竹杆把窝捅了。
这时我跟阿三到他宿舍,似乎没有人关心这件事。
等到阿三问起才有人回答道“那些死鸟,我早就想捅了,到处拉屎,一大早就在乱叫。”
阿三气得想打人,“你们有没有良心?那是两条小生命啊!”
“良心?有钱就有良心,没钱就是烂命一条,我可怜他们,谁来可怜我?”抽烟男怒骂道。
阿三攥紧拳头,侧身而站,抽烟男则坐在下铺,光着膀子左手抽着烟,右手夹着扑克牌,面前是一张长方桌,上面放着花生壳,瓜子皮,几瓶未开的瓶装酒,还有几个倒满酒精的大碗,地上也满是瓜子和花生壳。
我似乎看到阿三抡起酒瓶给那个光膀子的抽烟男一个闷头杀,我只好贴近阿三,示意他出去外面透透气,我第一次看到人真的会因为生气而面露青筋的。我用力把阿三往外推,用尽了力气只推了几步,他像是着了魔一般魂不守舍,连我说话的声音都入不了他的耳朵。
我明显感到他整个人的气场变了,变得可怖瘮人,赶紧跑到阳台接了半盆凉水,打算朝着阿三的头上浇下去的,刚跑出一半脚底一滑,不知道踩到了什么,趔趄地在地上摔了一跤,这一摔屁股先着了地。
手中的盆子连同水飞出门外,那塑料的盆子还在门外转了两圈才停下来,路过的工友被吓了一跳,把要通过门口的脚收了回去,站在门边低着头瞧着那个从屋里飞出去的盆子,因为她们离盆子太近,以至于盆子里的水把她们的鞋子弄湿了。两名女生在门外大喊大叫“谁扔的盆子,把我们鞋子弄湿了。”
我双手撑着地,勉强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向着门走去,半哈着腰单手把盆子捡了起来,余光瞥着那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她们穿着黑色的平底胶鞋,里面的白袜子一半已经湿透了。
有气无力地说着“要不进来坐坐?”她们娇羞地往里面探了探头,看到抽烟男半裸着上半身,捂着脸跑开了边喊着“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