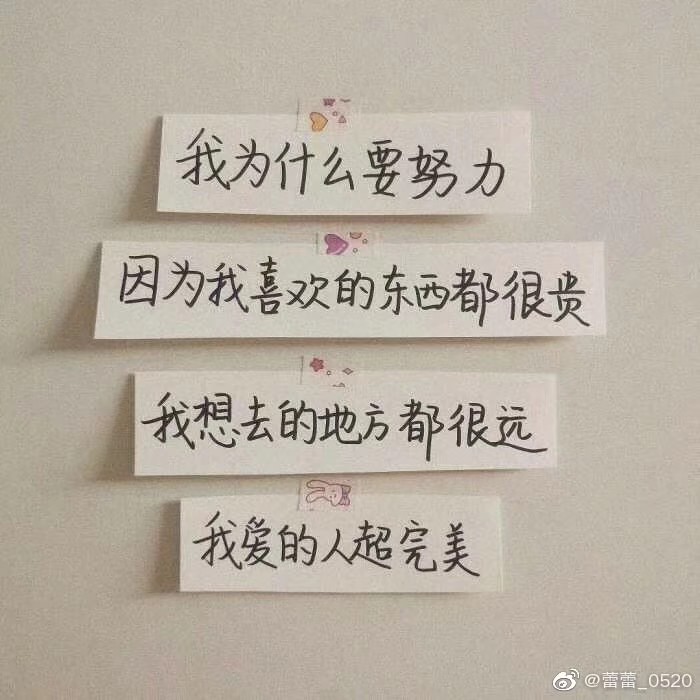快到宿舍楼下时,阿三趁着放慢的车速跳下车,我刚好把车刹住,他从车里拉出那条拴狗的大铁链来,我站在树的一旁,差点笑出声来,见他若无其事地,把大铁链拴在车上,另一头又绕着树围了几圈这才上了大锁头。
他蹲在树旁,抬起头来看着我,那张漆黑的脸,透露出了无奈和一丝窃喜。
“这车要是不锁,明天就到二手市场了,我那天跟朋友到庙里玩,十分钟不到他的车就被偷了,我们跑到大路出去找,所幸看到一群小孩站在虚掩的草丛里拿着几瓶喷漆液正在往一辆摩托车上喷漆。
我二话不说,抡起田里的泥块,就往里扔,跨过沟渠跳到对面田地,只是一群毛小孩,我那朋友已经认不出车的本来模样了,但是我能肯定这就是我们那一辆车,因为后面栓着这一条大铁链子,只是那天刚好没有锁上。于是我们从他们手中抢过钥匙,把车推到路上,开了回来。”
我诧异地听着阿三口吐莲花式地吐槽这一经历,也理解他这么夸张地为了一辆车用上这么粗的铁链锁起来了,后来阿三说这是他从朋友那里花两百块钱买来的,因为他的朋友,辞工回老家了东西带不回去。
我已经想到阿三把那群小孩打倒在地故意留情的冲动和无奈了,那群小孩一定是惧怕两个大人的力量,但又死死地把着车头不让他们把车开走,阿三只好下车用拳头解决问题了。在田里干活的大人听到小孩的哭声扛着锄头赶了过来,阿三已经开着电瓶车溜走了。
我想着,这才过去几天呀,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连那个紫菜头女孩也有男朋友了,真是见鬼了。当人经历了世间的黑暗之后对事物都有了戒备心。
上了楼……没有开灯的走廊一片漆黑,无论外面的阳光多么热烈,阿三手里拿着钥匙开了房门,房间就像小黑屋一般遁入黑暗,我觉得有些疲惫倒在床上就睡了。那是一张只有草席的下铺,上铺没有人睡所以放了一些杂物,整个房间只够放一张床,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人可以躺在床上一伸手就能摸到门的把手。
阿三把钥匙挂在门后,关好门下了楼。
一觉睡到了晚上,这时太阳西斜,走廊开始有轻微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打开手机看了下时间,已经下工了。
小蔡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我没有接到,可能是网络的原因,我没有回拨过去,走到贴在墙上的一小面镜子面前,看着自己憔悴瘦弱的脸庞和杂乱无章的头发,胡乱拨动头发,穿着拖鞋,走进洗手间,洗了把脸,把那张憔悴的脸庞洗得有些红润。
下了楼,踱步走在食堂的路上,一拐角看到一大波工人已经拿着饭盒,跑着,挤着、抢着、在食堂外面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食堂内几十张铁做的饭桌椅,已经坐了一半的人,这种椅子一坐下去,会有一阵阵的冰凉,毕竟是铁做的。
座位上每个人都在埋头吃自己碗里的食物,恨不得快点吃完,结束这场匆忙的进食过程,过道永远有一群人端着饭菜漫无目的地寻找空座。吃饭的人一边要进食一边还害怕站在过道的人把饭菜倒在他们身上,这种事情倒是少见,最多就是女学生盘子端不稳把汤洒在地上。
我站在门外无所事事,看到阿三从人群中端着两个饭盒挤了出来,我们在食堂外面找个空旷地蹲着吃起饭来。夜幕降临,很快周围的蚊子接踵而来,我们飞快地扒拉几口,恨不得把饭盒里的饭,当一口吃了,阿三倒是不怕被蚊子叮,而我却怕得要死,只能边吃饭边拍蚊子,三个女生端着饭盒快步从我们身边走过,可能怕被蚊子咬的原因。
我边吃边走到洗碗间,把饭盒往水龙头一搁,阿三从别人那里借来洗洁精往我碗里挤了些,又往他自己的碗里挤了点,弄成很大的泡沫,又冲冲洗洗,晚饭就结束了。
我休息了两天,觉得没啥毛病,就把头上的纱布摘了,丢到垃圾桶里,站在外面吹着凉风,觉得这一切,既真实又梦幻像在做梦一般,阿三跟学生们还要去上晚班,上到晚上九点半,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像我们时常工作到这么晚的工人来说,也不会习惯这种作息,更何况还没出社会的学生们呢!
我自个出了厂门,在外面完全跟厂里两个模样,一个是繁华的闹市,刺眼的霓虹灯随处可见,另一边却只有单一的白炽灯亮得使人发昏。
每天扎堆在年龄参差不齐的人群里,每天一睁开眼就是工作,领班很轻视学生的价值,毕竟来到工厂,他们只适合做一些流水线的工作,所谓的社会实践只不过是因为缺钱而找的一个“托词”罢了。
他们能在这里学到什么技能?打包盒?钻螺丝?还是印刷?任何一个岗位都能被轻易替代,领班也时常对一些还没上手的学生骂道“不想干就走啊!反正人一大把,一招就有了!”
为了拿点工资而忍气吞声的也有,被气走,但是胡浩要扣三百块钱的中介费用的也有,总之,没有一样是容易的。我不看机器的时候,喜欢到生产间溜达,一群学生模样的人正戴着统一的帽子,一条快速的流水线正从她们手边经过,她们中间要有一人停下来,整个环节都运转不了。
我慢慢走着,路上看到一个人,他背着黑色的双肩包,影子照在墙上,低着头拖着疲惫的身躯走着,此时也许有万般无奈说不出口,只有他自己能体会这段孤寂落寞的道路。他像极了落单的雁子,何处是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