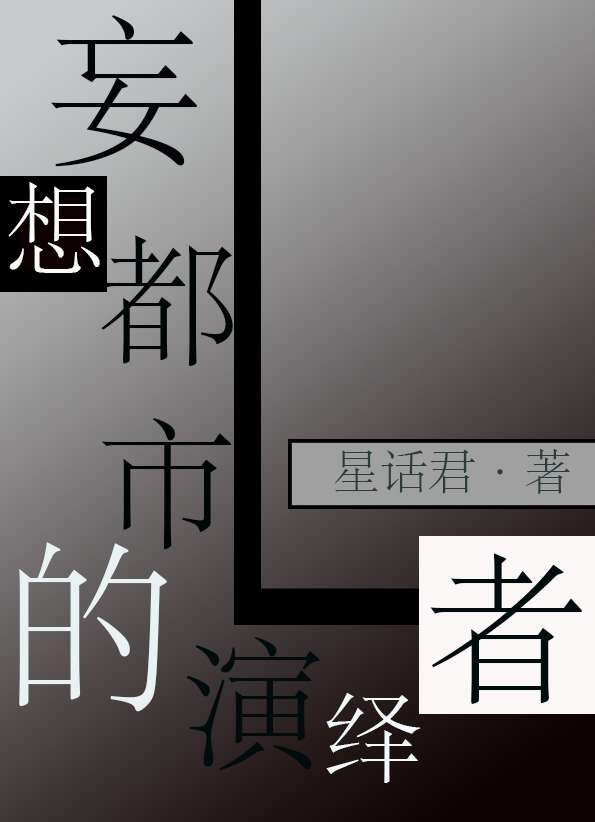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阿三瘸着腿出现在食堂,看着他满脸憔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独自坐在长凳上,手中的馒头只咬了一小口,就呆坐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嘴里的那一小口馒头还没咀嚼,只是单纯地含着发愣,桌上还有半铁盆能看得到底的清粥。我知道他舍不得那两天工资,坚持要去上工,现在他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站一天了。
“阿三”我喊着他。
他每次见到我都要站起来和我说话,我叫他坐下,我有时老是犯嘀咕,我又不是什么人物,干嘛对我这么尊敬?幸好只有他这样,不然被送医院的可能是我!
他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着话,“阿三,听我的去休息两天,这两天被扣的钱,我帮你补上。”
“不用,我觉得我可以上工。”
我见拗不过阿三那股劲,让他先休息一天,他犹豫着,闭了一会眼睛,脑袋向下倒了一下,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点了点头。
他带着疲惫的身躯走向宿舍楼,这次他学会穿上鞋子,窗外刮起风来……
阿三从床上醒来已经第二天,他悄悄地下了床,冰凉的地板让他感到一阵凉意,迅速穿好从地摊新买的拖鞋,买拖鞋那一天,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
他穿上了人生第一双鞋子,尽管花了他十块钱,但他依旧感到这一切就像在做梦一样,绚丽的霓虹灯,闪着他的眼睛,这个拥有5.0好视力的人,眼睛竟然模糊起来,那一晚他提着新鞋回到宿舍,擦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放到地板上,没有工友注意到阿三床下多了一双鞋,只有他自己知道兴奋了一晚。
他走到阳台看着蒙蒙亮的天空,愉快地洗漱,从废弃电线上取下毛巾擦干脸上的水,麻雀在他头顶上叽叽喳喳张着口叫着,他把毛巾重新挂上,回头看了阳台顶上居然有一麻雀窝,是两只嗷嗷待哺的新生儿,他从屋里搬来椅子,又从饭盒里找来几粒米饭,站在椅子上,把米饭送进它们嘴里,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便带着饭盒下楼去了。
楼梯的玻璃渣已经被清扫干净,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要走到阳台做一下拉伸运动,阿三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怀里的饭盒因为里面装着汤匙,而发出一阵阵沉闷撞击的声音。
我本打算喊他等下我的,但是一想到自己脸都没洗,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了跟上阿三的脚步,我赶紧进屋洗了把脸,带上饭盒,连鞋子都来不及穿,胡乱在地上套了双人字拖就下楼了,屋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把一群打牌到凌晨两三点的舍友吵醒了,他们口吐芬芳地在睡梦中说出一串漂亮的中国话来……
我下了楼,打算追上阿三,这家伙才几分钟已经没影了,走到食堂外往里看,一片漆黑,因为屋里没有开灯的原因,我只能看到几个黑影围在一起动着。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大锅清汤寡面,表面上一层浮油,几个人围在大锅旁筷子伸进锅把面卷进自己带的碗里,觉得份量够了,再拿汤勺舀点汤进去,早餐就在这几十双筷子的争斗中匆匆结束了!
我早上喜欢喝点粥所以没有参与这场争夺战,打了碗白粥,拿了两个红糖馒头,找到了阿三。
阿三见我坐在他对面,手中的筷子放了下来,把一堆佐料推到我面前来,
我笑着,“这是面的佐料,我不用,我喝点甜粥就行。”(其实那佐料只是一些红辣椒丝和青辣椒丝配上豆瓣酱、生抽、拌在一起而已)
在外面买早餐,店家通常会用打包盒装一碗白粥再配点腌萝卜干当配菜,一份两块钱。
早上,我常常不知吃些什么,自己带点糖,拌在白粥里变成甜粥,在老家吃甜粥是有讲究的,一个人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家里老人就会准备一碗白粥,拌上糖,给我吃,久而久之,当我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时,总会想念那一碗甜粥,那种用柴火煮出来的粥,是煤气灶替代不了的。
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还记得那个味道。
阿三拌着青红辣椒吃起面来,那生辣味扑面而来,我想着,这黑人也能吃辣,真是见鬼了,印度也有辣椒?
这货要不是皮肤的原因,这口浓厚的湖南口味准能以假乱真,等我埋头吃完那碗粥时,阿三已经洗完饭盒,走到我身边低声说,“听说要来学生了,暑假快到了”。
我愣了一会,看着他黢黑皮肤下,闪着油光的脸颊,那种与生俱来,来自人性狂野的兴奋感,油然而生,他已经控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我从他的眼睛看出了热情的欲火。
你兴奋啥?我打断了他的话……
他冷静了一会说“厂里都是大妈,现在来了学生,肯定有年轻的女孩,自然有些兴奋,还可以分担些工作。”
什么时候来呢?我好奇地问道。
我听大妈们说,过两天就来,包车来的,到时车就停在楼下,我们可以出去瞧瞧。
吃完饭,阿三把饭盒放在洗碗间的铁架上,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方便中午打饭,我洗好饭盒,在铁架上放好,回过头去,胡浩跟我照了个正脸,他身边跟了两个壮汉,并不是说身材有多魁梧,而是他们身上的赘肉显得很壮。
他们那般尊容站在一起,隐隐约约有点像村里的地头蛇,整天无所事事,在村里闲逛,到饭店吃饭赊账,一言不合就叫上几个小弟把他们的摊子砸了,成天就会找人打架,到了晚上,村民把电瓶车锁进屋里,他们还能把锁撬开,把电瓶车偷走。
我只是淡然地抬了下眼皮,就走开了。
阿三趴着墙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见我走出来,他凑了过来,低声说,“还好你没动手,厂长刚好过来。”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工作的车间在二楼,负责开卷帘门的人还没来,吃饱的工友大多站在饭堂外,夏天的太阳起得很早,六点半就已经散发出烤白薯的热量,多数人站在阳光照不到的阴僻处,我也不例外,整个夏天也是每个厂最忙的季度,所以通常都会招一些学生。
阿三倒是不怕热,站在烈日下,等着负责人来开门,眺望贴着马赛克砖的外墙,闪着白光,让人睁不开眼,只能捂着眼睛或者低着头不去看四周,汗珠从我的额头和脖子流了下来,每天还没开工上半身就已经湿了一大半了。
阿三提着我那1.5升的水杯,递给我,我咕咚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再扭紧递给他。每个人都在烈日下煎熬地等待,都卡着时间在等着上工,可卷帘门还是没有人打开。
我腿都蹲麻了还是没有人来,扶着墙角站起身来喊着阿三“操家伙,他奶奶的,我等了一个小时了还不来!”
阿三抱着水杯跑了过来,“知道今天是谁值班吗?”我问道。
“不知道名字,但是见到人,我就知道是谁了。”
行,我们在食堂逛了一圈,工友基本在外面等着,只有打饭阿姨和厨师正在吃饭,其他的就是领导阶层,阿三一眼就瞅中了椅子上放着红帽子的人,那个人背对着我们,阿三认定就是这个人,他边抽烟边跟其他人聊着天。
我走到他们的桌子旁,“天气热,工友都在外面晒太阳等着开门。”那人脸一沉没有说话,伸手从腰间抽出一串钥匙,在十几支钥匙中数出了两支,举着一条大的跟我说,这是最底下锁头的,另一支短的是总开关的。
我拿了钥匙,准备打开大门的时候,所有工友都在慢慢地朝我靠近,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打开了卷帘门,阿三第一个跑进去,从里面把其它三个门一一打开,车间一片漆黑,我找到总开关的盒子,钥匙伸进去后转动了两圈,发现打不开,又往回转了一圈这才开了,一抬闸一道微弱的火光迸射了出来,打开开关后,我把盒子重新锁好,把钥匙丢给阿三,让他去还给负责人。
我接过阿三手中的水杯,他跑进了食堂,我想着,这家伙的腿这么快好了?
不去理他,上了二楼,把杯子灌满水,放到架子上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做的工作就是看着机器上的数据,不让机器出错就可以了。这份工作一旦开了机器,人就不能走开太久,一旦有误差产生就要立刻更改数据。有时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不去上班,睡到下午才去。
我的位置靠窗,可以从楼上往下看到整座食堂,此时阿三正往二楼走来,他穿着一件大红的上衣格外显眼,他的拖鞋在楼梯上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像鞋子进了水一般,走起路来总有一阵水声。不一会已经上了楼,他坐在另一个机房看着机器,与我隔一堵墙,他跟其他工友说话,声音被机器发出的声响掩盖住了。
我坐在凳子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入神;良久,觉得手中一阵冰凉,低头一瞧,原来是阿三往我手里塞了一根雪糕,他和我说,那天晚上找我也是想给我雪糕,中途化了就没有给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