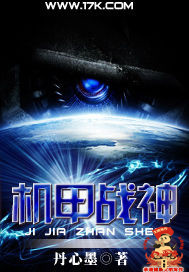“你想好了吗?”萧蕙心再一次重复这个问句。
我已经换上干净的衣服。体力正一点点恢复,虽然仍有难忍的痛楚一丝一丝传上来,但意识已经清晰。
锦时在内殿哄小公主睡觉。
蒹葭宫外迟迟没有传来父亲起兵逼宫的消息。
她知我心意已决,也不再纠结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反而轻笑转移话题:“你诞下公主的消息此刻应该已经传入右相耳中,他等待数月,怕是要失望了。”
她谈论起我的父亲,我父亲的霸道
心计,忍辱负重,手段谋逆。轻描淡写,并没有如何不友好的含义,也不是针对我,不过一点谈资,一份表达。
送我出碧落湖的小舟已经停在蒹葭宫外。
我满身疲惫,咬牙支撑。她从殿中追出来,亲自将一件厚实的斗篷裹在我身上,风帽盖下来,遮住了我整张脸。是去年她生辰时昱辰朔赐予她的那件西番进贡的举世无双的黑狐斗篷,灰黑色的茸毛,柔软的素锦缎面。八月本不该穿得如此厚重温暖,只是我现在见不得风,密不透风的斗篷稍微缓解了我的手脚冰凉。
夜色深沉,一点月色也没有,我裹着斗篷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
浅歌站在一旁,亦是红了眼眶。
我现在的身体其实并不适合周波劳顿,她们均不赞成我的决定。且不论我生产不过两个时辰,接下来的一路颠簸,困难重重,我一意孤行到了衡阳,对战势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我并不能对他有任何帮助,甚至会拖他后退。
但我只想陪在他身边,要死,我也要和他死在一起。
怜儿划船送我,她对这碧落湖的熟悉无人比拟。为了掩人耳目,我们选择的是一条极隐秘的小路。一路的竹影潇潇,压下来遮蔽了视线。
兜兜转转,艰难行驶。不敢点灯,只能慢慢摸索,在染月楼西角一个杂草丛生的沟道里靠岸。
剩下的路,唯有靠我自己。
我小心翼翼穿行在偌大的御花园。
一队一队的御林军来回穿梭。
我藏在假山后,躲避禁军的搜寻盘查。
脚步纷杂,人影层叠。
一身银色盔甲的男子沉声发问:“怎么样了?”是哥哥。
重甲冷冰,这身衣装其实与他的气质并不相称,我还是喜欢他素日里锦袍玉带、风流无物的贵公子模样。
“皇后娘娘与小公主仍在蒹葭宫中。”
“传我军令,所有军士撤出太液池外,谁也不准私自进碧落湖。凡违令者,军法处置。”哥哥一改往日谦和温煦,声音里的决然严厉连我都有些惊讶。我们都是姜氏的子女,身体里流淌着这个权臣世家历代积淀而来的清醒和冷酷。我们可以随时硬下心肠,披荆斩棘,杀伐决断。
“右相大人。”那人还未来得及传令,徒然叩首。
哥哥站着一动不动,迎面瞧见父亲大步流星而来,并没有全副武装,仍旧是那一袭深青色的朝服,周身寒气逼人。
随行的侍卫纷纷识趣退开,只他们二人针锋相对。
瞧得出来,他们之间气氛紧张,彼此气焰难消。
父亲深沉的声音辩不出喜怒:“你是打算与我做对到底吗?”
“儿子无能。”他一如既往地倔强顽固。
“你放她入碧落湖,护她于蒹葭宫,她未必感激你。”
“这是做兄长的义务,我并不求她的感激。”
“兄长?本相只有一个女儿,你哪来的义务?”他说得轻描淡写,如利刃扎在我心头。直到现在,甚至是百年千年后,他都不肯承认我的血统身份,承认我是他的女儿。他的声音冷的骇人,“你知道我做事的风格。”
是一片如死的沉默,良久听见哥哥叹息,有难掩的悲愤:“一个慕玥还不够吗?你可以失去第二个女儿,我不能再失去第二个妹妹。”
“右相大人,在太液池抓到蒹葭宫的一名侍女。”侍卫来报。
定是怜儿落入了他们手中。
有人将我拽进假山石群的暗洞之中,我心惊肉跳,已经按住了藏于腰间的匕首。
“这边。”是谢盼之低沉婉转的声音,她已经攥着我一路躲躲闪闪远离御花园。
她在前面为我引路,我这才瞧清了她,一身简易女装,长长的秀发仅用一条银色发带束起。换下平日里繁复华丽的宫装,去除钗镮雕饰,眉宇间英气飞扬,反倒多了几分英姿飒爽巾帼英雄的风采。
她在前面喋喋不休,也不知是在赞誉我还是在讽刺我:“我今日终于知道为什么总是输给你了。你的亲生女儿,临走你看都不看一眼,这种狠心,我可做不到。”
看来这一夜波折她都了如指掌。
我无奈,难道我就舍得孩子吗?但若我看了她一眼,我就走不了了。
“九门紧闭,戒备森严,岂是凭你这手无寸铁可以硬闯?你再瞧瞧你自己,两袖清风,一副病体,如何跋涉过半壁山河,山长水远?”我从不知道她原是这么唠叨冗长的一个人,但一桩桩一件件皆是为我着想。
的确是我考虑不周,只想着好歹先出了宫门。走一步看一步,其他等出去再想办法。
南门就在眼前。
“肖桦。”我低低喊了一声,已有人影落在三步之外。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只有他苍厚的嗓音传过来:“娘娘,属下拼死护您出宫。”
这就是我原定的计划,靠我自己是根本出不了宫门的,但他可以带我杀出去。以他的武功,我的孤胆,拼死一搏,还是有机会的。
“你不相信我?”谢盼之却忽然怒火中烧,“你以为我们谢氏全是死人吗?”
她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若要害我,高喊一声我便四面楚歌,无处藏身,不必大费周章带我来这里。
徒然间明白她话中之意,这南门已在谢氏的控制之中。
左相蛰伏多年,手下亦有多部效忠,实力不俗。若是真与父亲动起手来,父亲未必轻易能够取胜。
那么父亲迟迟不动手是在忌惮谢氏吗?我搞不明白,我不明白一向果决的父亲还在等什么。
她大摇大摆朝宫门走去,我低头一路紧随。
果然不出所料,守门的侍卫见了她,二话不说下令打开封闭的宫门。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走出了皇城。
回首仰望高耸的城墙,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不合时宜地想起那次昱辰朔带我出宫,在宣和门扯谎,明明牛头不对马嘴,漏洞百出,却蒙混过关,骗过守门的侍卫。
这些微不足道的记忆星星点点涌现时竟全数转化为甜蜜,让人不禁满心欢喜,如沐春风。
这就是命运叫人敬畏之处,它总是让我们在蓦然回首时发现曾经自己认定的悲喜都有全盘反转的机会,让我们一面承认自己的短浅,一面欣然接受它为我们安排的每一处惊喜挫折。
拐过宫门百米外,一辆马车停靠在深巷墙脚,她快步走近,连叩三下车窗,道:“人我给你带到了。”
有人一把掀开车帘跳下来。
谢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