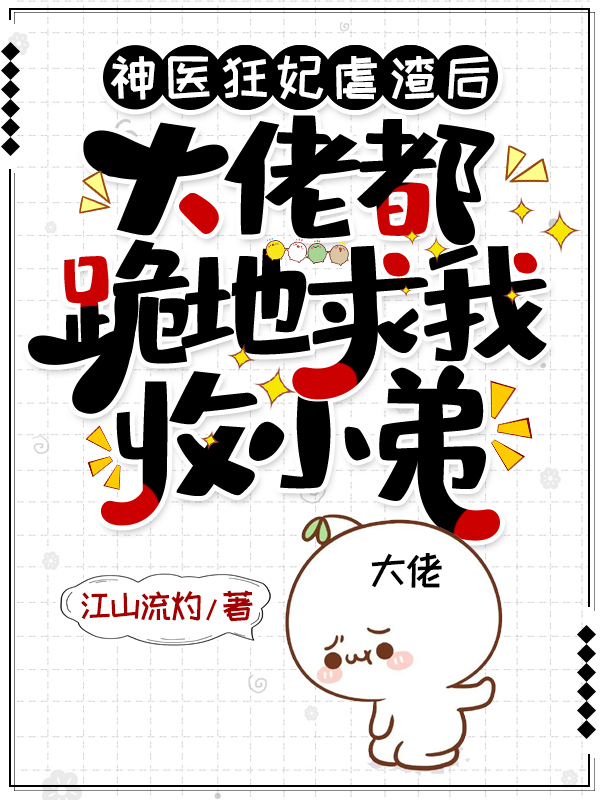一夜未眠。
隔日,云袖姑姑早早便来引我去见太后。
步入庄严繁华的长乐宫,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一切的真实。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见到这个处于姜氏中心的女子,见到这个手掌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太后。她不过是四十七岁雍容华贵的后宫女子,却也是央央宁越天朝真正的主宰。
我见了她,才觉得那是一种无上的权威和尊荣。
她端坐在雕龙镂凤的高座上,深深望向跪在座下的我,神色沉静而威严万分。这个女子她在这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后宫中浮沉四十年,想到这,我不由心中发颤,一时一句话也不敢说,只静静跪在宫殿冰凉的檀木地板上。良久才听她叹道:“哀家不曾想你竟肯入宫来。”
我不由攥紧了衣角,愿与不愿又岂是我能选择,她如今一句话却好像我有多心甘情愿似的。
我正了正身,缓缓迎上她的目光,一字一字吐露:“我也姓姜。”
虽然我生活在姜府的杂役房,远离了朝堂,远离了至尊的荣耀与富贵,但无论如何,我是姜家的女儿。这一点,谁也无法改变。
她依旧紧紧望着我,那双深邃的双眸中却已染上浓重的惊怔、动容之色,甚至更多。
她大抵是想到了这十六年来对我的漠视,或者是我对着她竟敢说出这番话,更或者想到了……姐姐。
她已起身一步步走到我面前问道:“姜念玥?”
她在问我的名字,我知道。我低着头回她:“回太后,是。”
她微微俯身,一旁的云袖姑姑忙上前来扶我,她却坚持着亲手将我扶起,道:“不必如此拘束,如玥儿般唤我姑母就好。”她说着,握着我的手微微一颤,眼底也泛开一层哀伤,只一瞬便又恢复。
我知道,她和我一样,此时此刻,想到的是姐姐。我的姐姐,姜慕玥。
我心中一片凄然,仓皇跪下,强忍着眼泪开口:“姑母,我想……我想去看看……姐姐。”
我知道我如今的身份在这皇宫中多是忌讳。我此时也不敢抬头,良久也未曾听见她的反应。
到底,是没有阻止。
云袖姑姑领着我到了昭阳宫,那偌大辉宏的宫殿外此刻层层守卫,森严戒备。到了宫门前,我却突然迟虑了,只觉得每向内一步都是艰难。
我独自入了寝殿,殿内的白幔捥素还未拆下,光线晦暗,阴气森森。
我站在殿中,目光掠过镂月屏风,绣金龙床,沉香贵妃榻,檀木桌案,似乎一草一花一柄桃木梳也还留有姐姐的气息。
可我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
这奢华晦暗的昭阳殿送走了一个主人,又迎来另一个。
如果这偌大的宫殿也能看能听,那么,它又会记住什么呢?
它看着这宫殿的主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甚至,也曾冷眼看着姐姐,受尽委屈,无辜枉死。
我只觉周身寒意袭来,似要将我吞噬。
殿中罗幔翻扬,恍惚间,我似看到那张宽大的金辇绣床上,姐姐哀怨的神色。殿中有轻微的声音缥缈而来,是她在唤我:“念儿,念儿……”
我终是难以自抑,奔逃而出。
鸳鸯等在殿外,一句话也没说。一路折回,穿过悠长悠长御花园小道。如此寒冬腊月,这里却依旧繁花簇锦,不曾为这国殇有一点点的改变。
隐隐听见有宫人的声音传来,“刚进宫的那位,可厉害着呢?”
“听说还打了贤妃娘娘身边的子鸢。”
“可不是吗?听说是右相之女。”
“右相不是只有皇后一个女儿吗?”
“是庶出……”
接着是一阵窃笑,仿若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表达。是庶出,尖酸狠毒便是必然。
我笑了笑,他们用一种隐秘而迂回的方式在评论我。
那边的声音还未停,鸳鸯显然有些生气了,正欲冲过去。
我止了她,冲她微微一笑,示意我没事。
这宫中消息传得可真快。我不禁感叹,我倒是不在乎他们在背后议论我什么。将我说成洪水猛兽、毒蛇恶鬼更好,这样也便无人敢来招惹我。这于我,未必不是件好事。
回了长乐宫,姑母似在等什么人。算着时辰嫔妃们早省的礼也该过了。我不敢多言,只好坐在一旁的侧座上。
不多时,便有宫人进来禀告,“太后,凌美人来了。”
凌美人,凌烟。
我曾无数次听过她的名字。因她圣宠隆深,乃是这后宫中最得宠的一位,甚至可以说是专宠,是姐姐最大的劲敌,连带整个姜家也对她恨之入骨。
遥遥地便瞧见一个女子娉婷婥约的身影。一身宫锦白袍,只稀稀松松着了三支青玉簪,无更多修饰,宛若纤纤仙子,不染尘烟。
我一时有些呆了,以前在府中下人刻薄的谈论中,我总觉得这第一宠妃该是更繁华、更尊贵、更妖娆的。如今见了,才发现竟是这样柔弱如水,清冷透彻的女子。
她的目光亦向我看来,只一眼便毫无波澜的收回。
她跪下身来向姑母请安。姑母端坐高位,目光已变得凛冽,威严开口:“哀家听说你近日身子不适。”
“只是不慎染了风寒,谢太后费心。”她答得谨慎,但分明已有了谨剔怯惧。
“你侍君伴驾怎的忘了规矩。小小风寒若不小心照料也会成大患,哀家特地让人煎了帖驱寒的药”,姑母的声音一凛,唤了声“来人。”已有宫人端着白玉饮碗进来,碗中液体浑浊,药味刺鼻。
“太后,”她显然有些慌了,低唤出声,又霎时意识到自己的失仪,重重伏身,换了一种平静恭谨的语气,“谢太后隆恩,只是太医已为嫔妾瞧过,并无大碍。”她在拒绝,想来她也察觉药中问题。
“云袖”,姑母不为所动。我知道,今天这药她不喝也得喝。我内心惊怔,座下生寒,不由紧握了不停颤抖的双手。
入宫不到两日便见到这样的场面,我亦是恐惧的。
“皇上.....”遥遥传来宫女惊惧的呼喊声和男子闯入的声音。
只那一刹,随着他夺门而入,正午耀眼的阳光却徒然暗了下去,空气中仿佛骤然有了一种迫人的寒意。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仿佛回到一年前的元宵,我站在宣和门下,抬头仰望位于高耸城楼之上的人。那时烟火绚烂,人潮繁闹,我的目光却只为他牵引。那个人离我那样远,远得看不清面目,仅仅遥遥望去,竟已让我生出压迫窒息之感。
“太后……奴才……奴才拦不住……”一路止着跟在他身后的宫女忙不跌跪下,颤颤巍巍请罪。
拦不住,谁又拦得住呢?他是皇上,普天之下谁敢拦他。
谁也没有说话,整座宫殿都在刹时肃穆下来。
我低着头心中越发紧张,此时此刻,几步之外,我竟不敢直视那个人。那个人身上有一种炽烈而凌厉的光芒,无形中迫得人无所遁形。
男子生生压抑着开口:“太后这是要作何?”
姑母依旧平静端坐高位没动。我抬眸看她,她却像是无形中老了许多,良久才听她道:“皇上难道忘了三年前答应哀家的话了?”
“朕没忘。”他的语气坚决,“但是太后,这些与她无关。”
他唤她太后,不是母后。
他自称朕,不是儿臣。
我似乎开始有点理解姑母急着招我入宫的意思了。十五年前,先帝驾崩,宜妃殉节。她毅然废太子,打败谢氏拥护的二皇子,剿灭陈氏等三皇子党,携宜妃所出四皇子昱辰朔登上帝位,垂帘听政,开启十五年后宫专政的岁月,使姜氏权势达到巅峰。如今皇上大了,她必须放权,必须靠另一个姜氏女子来巩固门庭长盛不衰。
“即如此,”姑母的声音依旧冰冷,“云袖”
他站着没动,似乎并没有因此服软半分。
他不动,自然无人敢动。
“皇上,太后。”僵持不下,殿中气氛异常紧张。倒是跪在一旁的凌烟开了口,“嫔妾愿喝那药。”
姑母的目光冷冷扫在男子身上,不曾动半分,语气坚决、不容忤逆,“喂她喝药。”
他倔强挺立挡在凌烟身前,云袖姑姑端着药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皇上,嫔妾......”他身后的女子还想说什么,那单薄的身子撑了撑又轰然倒了下去。
“烟儿。”他一声惊呼回身将已陷入昏迷的女子揽在怀中。
永乐宫一时乱开了,他满脸痛意,抱起她,灼灼目光却忽地向我望来,那双深邃的眸中已是滔天恨意,像刀子一样剜向我。
我此时倒不惧了,静坐席上,波澜不惊。我不怕他,今日的一切是他与姑母之间的战争,与我并无关系,我为何要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