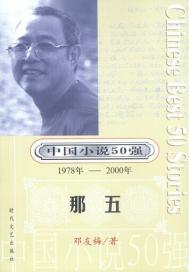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我在部队已经呆了整整两年,这期间连长对我关心有加,指导员司务长对我更是不错,而且我还被提升至士官,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虽说我曾经一度思想消极,打算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混三年义务兵,等复员后回农村种地,娶媳妇抱娃子,今后再也不想别的了。
但被提升士官之后我就有了被提升班长,或再长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还会有被提升排长的机会。
说是死心那只是对以前的我,现在我好像看到前方不远处露出点点微微曙光一样,我要振作起来,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实力在部队发展,不像某些人依仗自己的官老子。
当然我的进步仍然处于普通士兵一名,廖勇当代理排长也已经一年多,班长也幸运的当上了我的排长,假妮子升任班长,副班长由一名跟假妮子兵龄一样的老兵代替。
这期间我经常能在不远处看见廖勇开车过来过去的,好像部队里给他配了一辆车。
听假妮子说廖勇在七连混的风生水起,非常受他们连长的爱戴,我们团长也动不动就找他聊闲天,扯咸淡,好像他们知道了廖勇的根子。
我不想理会孔泽隅,但他是我的班长,我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他,自己只能选择妥协,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会尽量避开与他正面接触的机会。
四月底五月初,我们团被下达植树造林的任务,文件里明确表明每个连每年都要建成一定规模的林区,总的旨意就是想要绿化大西北,减少沙尘暴天气。
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塞罕坝,植树造林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而且他们植树的成活率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塔克拉玛干是个典型的沙质地,这里不适合植树造林,但政府、林业局一直在不断的攻克这一难题。
可以从半荒漠地开始造林,开垦田野,以后再逐步慢慢扩大面积。
我不知道是否将来的大西北荒漠会不会变成一望无际的人工森林,但至少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努力着。
我们连的造林地被指定在距离塔里木盆地的不远处,西邻叶尔羌河旧河床,东临和田河,北邻博斯坦乡和机修连、团部场五连以及畜牧队,另外紧挨着上游水库,当然这些距离都是相对的,真要走起来那也是有段相当大的距离的。
听说还有个老营房在不远处,曾经有多名战士还去过那里,至于到底是个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那时我还没有参军入伍。
植树造林需要建设兵团的老战士和林业局的技术人员配合,其实准确的说,可以说我们是要配合人家才对。
正值植树前期计划和任务时,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帮不了什么忙,都是排长以上的干部级人员配合林业局技术人员和建设兵团的骨干,还有地质勘探家,班长都不用去的。
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动身。
我也一度在想,我们这些战士们会不会被划为建设兵团之列,开始大肆植树造林,不把整个新疆地区的大沙漠变成绿洲就不准我们退伍。
荒漠化地质需要抗旱树苗,都是选择全国各地典型沙质土地培育出来的幼苗运送过来,我们被指派的林场不缺补给水,但一味的施水也不行,得让幼苗自己抗衡一阵,等成活率上来了在进行大范围人工施水。
在选择各地典型沙质培育出的幼苗补给时,技术人员也在攻克塔里木盆地沙质这一难题,希望能在眼下的质地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幼苗,假如成功,可以说这里培育出的幼苗能够适合全国各地沙质地的植树幼苗补给。
但这个具有建设性的实验办法在还没被确定之前就被打消了念头,大部分人说这无异于将幼树苗悬空在一根绳子上,看它能活上几天。
林场年降雨量不足,施水过多只会让幼苗后期抗旱率下降,因此这需要林业技术员亲自栽培、施水和管理。
至于后期怎么样我想我们这些普通士兵也使不上劲,队伍轰轰烈烈的进军新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林业部的优秀技术人员。
虽说目前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训练这事我们这里也毫不耽误。
自从孔泽隅当上班长之后,我跟她算是针尖对麦芒,事事与他对抗,句句话伤他的心,我把我的这一行为都归功与他一年前对我封锁的训练消息,让我本可以立功的机会随着天上的黄沙消散在茫茫荒漠之中。
一年多我从未称呼他一声班长,他也曾经对我献过殷勤,希望我们能够重归于好,不再提及前事。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后来他也公报私仇,专门以我训练不合格给我开小灶,那段时间我吃不好睡不好,真想一巴掌呼死他。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就算吵架,也会慢慢培养出感情的,更何况一吵架就一年多,那感情岂是其他战友所能比得了的!
植树造林计划已经实施,连里下命令,需要抽调几名战士在夜里轮流看守刚植下的幼苗,以免被晚上出来觅食的爬虫给糟蹋了。
本来这些事情都是由班长和副班长配合林业局技术人员完成的,但连部并没有让技术员夜里看守林场,毕竟夜晚沙漠里也会有野兽出没,虽然几率不大但还是有的,糟蹋树苗是小,伤了人就这事就大了。
孔泽隅为了报复我他向连长推荐让我也去,说是我自愿报名的,希望能为部队多做贡献,不然我会茶不思饭不想,如果连里不同意那就表明连里不重视落后战士,管理不够人性化。
连长说为什么我不亲自找他,孔泽隅说我正在积极训练,要把落后于战士的科目练习给搞上去。
连长不信他的,但连长也没办法,全连都知道我的任何训练在连里已经达到数一数二的地步,这明显是孔泽隅在撒谎,但最后连长还是同意了,也许他是想让我守护树苗的同时也捎带上他,毕竟他胳膊腿无缚鸡之力。
第二天排长驱车送我和孔泽隅去往造林场,之后排长就去忙他的了,临走时排长看着孔泽隅依依不舍,但无奈他也看得出孔泽隅跟我关系已经是全连里最好的。
孔泽隅跟在我身后,我们俩像是领导下基层一样在试验田和已规划林区瞎转悠,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正在埋头查看幼苗的成活率,有技术人员看见我们,远远的冲我们喊话:你们一男一女在那儿瞎转悠什么,别碰了幼苗,没事就离开场地,别在这儿添乱。
孔泽隅捂着嘴笑嘻嘻的拉着我往试验田外边走,我想跟林业部那个刚才对我喊话的人理论理论,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是个人就对我大呼小叫的。
但我还没开口就被场地队长给放话了,他让我滚出去。
我说我是看守林场的,这里不欢迎我我就回去,到时候军区怪罪下来你担着。
队长说话态度马上缓和,说大白天的这里这么多人用不着看护,再说这里是试验田,都是技术人员辛苦培育的幼苗,是不允许技术骨干以外的人进来的。
我见他话里有了台阶,干脆就坡下驴别在这里找事了,整不好还得被自己领导给臭骂一顿。
后来我自认为没什么事干,闲的难受,就找了一片空沙地坐下来抽烟。
孔泽隅就像个跟屁虫似的怎么都甩不掉,他见我坐下来也跟着坐在我旁边。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把孔泽隅轰走,也只能无可奈何的任由他跟着我。
我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一口问道:“孔泽隅,人家那大姐刚才喊我们一男一女,你不生气?”
他说:“我生哪门子气啊”说完又低头笑嘻嘻的。
我抬头望向沙漠深处,接着抽我的烟,心里一片空洞,这人要是不要脸了,还真特么是无敌了。
孔泽隅是个很漂亮的假妮子,并且还是耐看型的,我越看越发的喜欢看他,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达到随时吵架且随时能和好的地步。
有时候我就感叹造物主,怎么偏偏把一个男孩子硬生生的拓出了女孩子的容貌呢,鼻子眼睛没有丝毫瑕疵,就连眉毛都是细长细长的,尤其自来红的小嘴那简直叫一个美,皮肤细腻,这绝对不是后天人工呵护出来的,是与生俱来的。
我不敢想象他的双胞胎姐姐应该是如何的美法,肉质肯定不一样,无论怎么说既然是男孩子,身体内的雄性激素就会胜于女孩子,肌肉相对会发达一些,揉搓表皮时肯定手感也不一样。
人常说女人是水做的,估计把玩起来应该很舒服,至少会比男孩子要好玩的多。
我心想也难怪,他巴不得让人家说他是女人呢,后来我想了个注意,打算气气他。
于是就开口道:“泽隅,改明个我送你一件礼物你要不?”
“我要,我要,当然要要了”他犹如得了疯癫病一样欢声笑语“你要送我什么礼物?”
我说:“送你一把刮胡刀,你看你都开始长胡子了,难道你照镜子时没看到吗?”
我这一句话好似在闹市区将他的衣服全给撕扯下来一样,让他难堪到了极点。
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嘴唇有点发抖的说道:“子键,你就那么恨我吗?你知道我性格偏向女孩子,为什么还要故意说这话伤我心?”说完孔泽隅竟然哭了起来,他哭的很痛,哭的很伤心,但没有发出多大声音,好像怕远处的植树人员听见。
我心里好笑,终于想出办法能让他伤心了。
于是我赶紧假模假洋装作可怜相,说自己说秃噜嘴了。
接着连哄带骗,说他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像个女孩子,根本没有任何男人的特征,我还说他要真是女人的话,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娶‘她’做媳妇的。
我话一出口孔泽隅当场就不哭了,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笑道:“鬼才嫁你呢,想娶我门都没有。”
我心说:哟呵!你瞅你那德行,你他妈还真把自己当女人了,我娶你?我又不是搅屎棍的。
可话说回来,孔泽隅这假妮子确实一点男人味都没有,真的跟个女孩子一样,而且还比一般的女孩子漂亮的多,这一点我始终都没有否认过,但即便是这样也照样不耽误我恨他一年前对我所间接性封锁的消息。
烟抽完了,孔泽隅就会掏出香烟给我续上,他一边给我递烟一边说:“子键,我们就这么在这儿歇着成吗?啥也不干?”
我说:“那可不,要不还怎样?去植树苗,你会呀还是我会?根茎埋多深?咱们俩谁懂,既然啥都不知道那何不好好歇息歇息,等到晚上我们可得睁大眼睛,别让什么爬虫把树苗再给糟蹋了。”
一整天我们两个闲着没事干,就开始研究连队里的每一个人,比如谁有什么爱好啊,讨厌什么啊,什么时候入的伍,老家是那里的等等。
谈着谈着,我们就算了算班里的哪位战士入伍最早,当然我以为班长孟子超应该是最早的,当然现在他已经成为我的排长。
但孔泽隅说不是,班里最早入伍的其实是其他两位老兵,班长和副班长也是他们两个,只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连里指派到原来的靶场了,不过那个靶场好像早已经废弃了。
不过那里有几间规模不大但也不算小的训练营驻地,两位老兵就被发配到那里看守废弃物资了,比如被淘汰的枪支,和退役的子弹,一系列被新物资所代替的老旧设备等等。
我问孔泽隅那个被废弃的靶场在哪里?怎么自己来到部队两年了却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
孔泽隅说那个废旧的靶场他也没见过,是听孟子超说的,好像是在沙漠深处,以前是用来训练高精尖部队精英的,因为环境不好,动不动就有沙尘天气,被训练的战士就得在那样的天气训练打靶,训练体能,忍受饥渴,忍受最艰苦的训练条件,一旦训练完成就会被指派秘密任务或者保护重要人物或物资设备。
总之那是一个训练高精尖人才的地方,能从那里出来的战士,他们的条件完全可以挑战我们团里的任何人,甚至一个排的兵力都进不了人家的身。
我继续向孔泽隅不停的打听那个废弃的训练营和靶场的事,关于那里现在都驻扎着多少人,既然在沙漠深处,那补给是怎么送达的。
假妮子孔泽隅表示那就不知道了,自己也是听孟子超说的。
他还说既然已经是废弃了的靶场,还打听那么多干啥!
我们在沙地上坐着聊天,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错过了饭点。
现在感觉肚腹有点饥饿,就起身打算去往林区营地搞点吃的,那里扎着好几顶帐篷,有宿舍办公室和炊事棚,以及一个专门做实验的小地窖。
营地距离林场大约有七八公里的距离,走起来也不算太远。
一路上孔泽隅一直挎着我的胳膊,搞得我俩好像恋人一般,只是都是身着军装,在外人眼里看起来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
我没办法,我摆脱不了他,甚至他的一切外在表现连我们连长都无可奈何!
到营地后几乎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已经奔赴林场和试验田,以及技术人员自己培育的苗圃工作地,当然苗圃目前还处于雏形状态,还没有真正投入使用。
营地里下午多出好些人,这些人都是我们连的战士,他们是来帮着挖坑植苗的。
可能是由于人手不够的原因吧,连长也亲自上阵,看到我和孔泽隅过来,脸立刻就耷拉了下来。
连长低沉着脸,显得脸蛋子灰不拉几的,他用批评的口吻对我俩说:“泽隅,子键,你俩这是干什么,还不把挎在在一起的胳膊给我放开”
我这才意识到我俩的胳膊还缠绕在一起,于是我赶紧将孔泽隅胳膊推开,并撒谎道:“连长,孔班长刚才跟我一起去林场看了一下,不小心崴到脚,所以我才让他挎着我,以免脚伤进一步加重。”
我信手拈来的谎话编的那叫一个顺手,眼睛都不带眨的。
我说完连长当时就换了语气,对我和泽隅关切的问道:“是吗?泽隅,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赶紧进帐篷休息休息。”
为了让我这个谎话能够圆场,孔泽隅继续挎上我的胳膊,假装脚疼的厉害,一瘸一拐的跟我一起进了帐篷。
连长说要看看他脚上的伤势,我怕露馅不知所措,一时竟没能想出对策。
没想到孔泽隅竟然扮成女孩子的害羞状,轻声轻语说到:“连长,不用看了,毕竟男女授受不亲。”
他的这句话搞得我措不及防,太特么让人意想不到了,我好想扬天长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出口的。
他说完连长就弓下腰仰起脸拧着眉头与他面对面,连长咽了口唾沫对坐在临时搭建的床铺上的孔泽隅问道:“什么玩意儿?泽隅,你刚才说的嘛玩意儿,怎么就男女授受不亲了?我说孔大哥,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一遍,我刚才没听清楚你说的话!”
我刚想说话,连长冲我一摆手:“你甭说话,我没问你!”
孔泽隅有点不知所措,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而且说的还是特么的混蛋话。
于是他显得很紧张,脸开始变得越发红润,好像想要哭鼻子。
这时外边进来一位应该是林业部的技术人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她进屋就问:“谁是三连连长?”
连长回过头:“我是,您有嘛事儿?”
技术员说:“你们连派来的人知道是干嘛来了吗!我们树苗都运到场地了,你们挖的坑在哪儿呢?”
连长疑惑的对来人说道:“我的兵不都去了吗,这么长时间了,他们没有挖坑?真的假的?您瞧清楚了没有!”
技术员说:“哟哟哟,还真的假的,你的战士们都在那儿坐着侃大山呢,坑一个都没挖,你管不管,不管我们上报林业部,明天就撤回去,你们自己种你们的树吧。”
连长一听当时就掉脸,起身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时他又回头冲我和孔泽隅说:回来再收拾你们两个!
连长一走,屋里的人也都随后跟着出去,孔泽隅还一脸无辜的看着我,好像再问:这可咋办啊。
我一拽他胳膊,学着连长的口吻说道:“你刚才说的嘛玩意儿,怎么就男女授受不亲了,大哥,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一遍… …还愣着干嘛?挖坑去吧,你不去那我可走了。”
到场地之后,连长大发雷霆。
战士们赶紧拿起锹,抡起来一个比一个快,我和孔泽隅也不甘落后,拼命的挖。
其实挖坑没有技术可言,关键是植树苗深浅问题,因此只要一锹下去挖出的坑能把一只脚放进去也就行了,想挖快点那就得加速了。
当然这些和我一样来自三连的战士们为什么来到场地后没干活,而是坐在地上侃大山,这大都来自于他们眼前的技术员。
这些技术员十个得有九个是女同志,而且一个个长得水灵,跟我身边的孔泽隅比起来除了长相确实逊色于孔泽隅,其他的方面都很吸引战士们的眼球,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女人味。
这人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味道,男女各不相同。
也只能是异性才能嗅的出来,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味道。
在这方面对于孔泽隅这个假妮子来说,他是无法弥补的,也是他根本办不到的。
因此孔泽隅平日里只能用香水的味道来错误的引导大家的注意力,让大家在潜意识里感觉仿佛有个女孩子在自己身边,因为毕竟香水这东西也只有女人才会用。
当然平常大家都会对他以女人的姿态接触,但现在不行了,面前这么多女孩子,一下就都吸引了战士们的眼光。
在我们连一般情况下战士们也不外出,除非轮到哪个班外出时,才会派外出人员替其他战士捎点什么回来,并且外出人员也走不远,顶多在乡镇里串串走走。
眼睛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男人,和上了年纪的妇女老太太,很少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就算有也极少会有汉族人,即便是汉族人,她们也会着当地人的服饰,几乎看不到汉族人的外表。
汉族人对维吾尔族人来说,其实是有一点相貌上的挑剔的,当然在新疆六十年代初期有不少汉族人民为了建设大西北已然扎根于当地,但长时间以来她们差不多已经完全被维化。
因此战士们看见来自大多数汉族的技术人员时会撂下手中的活,以大饱眼福欣赏她们。
此时孔泽隅对三连的战士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几乎没有谁会在这个时候看他一眼。
由于一直处于女性化的孔泽隅为了保持身材娇小,他不会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的,他讨厌自己身上有像男人一样健硕的肌肉。
所以他在训练时成绩是全连最差的,乃至在整个团也是最差的,毫不过分的说他在整个中国军队里应该也是最差的,只不过不至于被淘汰而已,也只是仅次而已。
挖坑抡铁锹虽说不是技术活,但也稍费体力,没挖三十个坑他的手就被磨出一个水泡,在连长的监督下大伙谁都不敢怠慢,因此孔泽隅手上刚磨出的水泡又被磨破了。
疼的他龇牙咧嘴,大伙当中距离他稍近一点的战士都发现了,不过大家并没有显露出同情心,相反的却是以另一种看待他的眼光瞅着他,仿佛大家在此时此刻都很讨厌他,一个好好的男人不干男人的事,非要特么的学女人,该!
孔泽隅此时脸上显出难堪,我多多少少也存在于跟大伙相同的心理,觉得他好像挺讨人嫌的,自己又不是女孩子,非要往女人方面发展。
说实话,真正漂亮的女孩子就是放一个屁大家都不会从心底往外的反感,顶多也就是被看作不雅而一笑了之,过后还会被她吸引,甚至恨不得凑到她屁股前闻闻还是否还留有屁味!
但假女人就大不相同了,你再‘妩媚缭绕’也不行,顶多大家会多看一眼你类似女人的容貌,其他方面是没有人会去看的。
平坦的胸部,一直溜的胯骨,根本吸引不了男人的眼球。
厕所的茅坑肮脏污秽,但路过女厕所墙外的茅坑时大家还是会往脏坑里看上一眼,不知道想要发现什么,但仍然会看一眼的。
毫不客气的说假女人连真女人扔下的卫生巾都不如,由此看来,孔泽隅的美只是大家在看不到真正女人时才会勉为其难的看让一眼的。
这不,在真女人面前他的手受伤了大家都不会理会的,甚至还一脸的厌恶相。
最重要的是连我也有了这种想法!
孔泽隅与我肩并肩挖坑,我发现他总是在卖力往我这边靠拢,好像在整个队伍中我是他唯一的亲人似的,只有我才不会嫌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