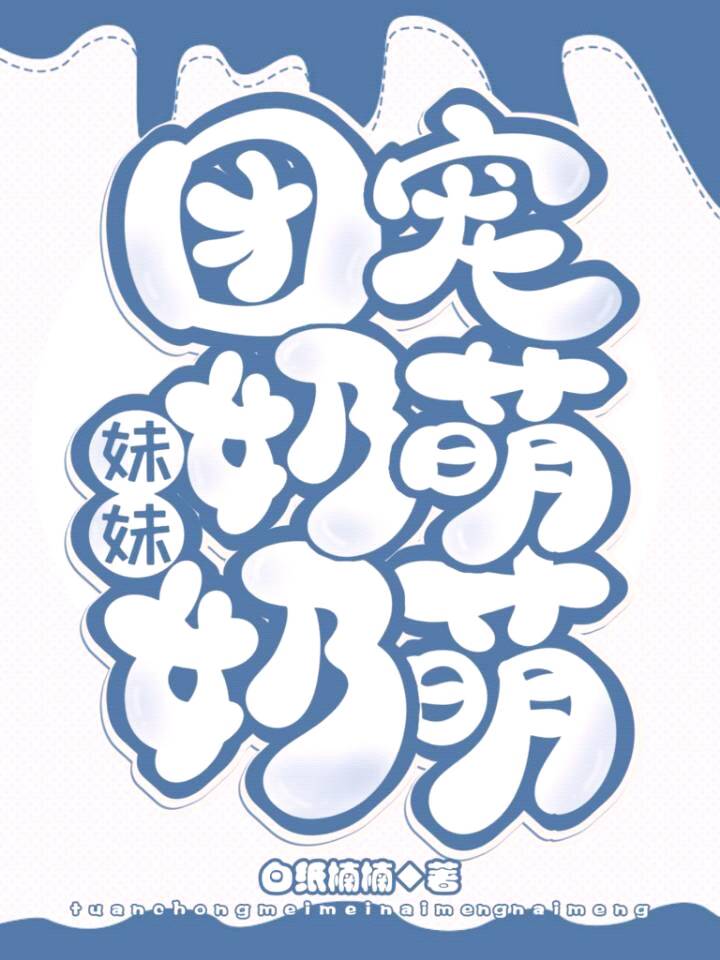贫瘠之地的天空是很干净的,这里没有漂浮的云朵也没有闪耀的雷霆,就算是偶尔飞过一只禽鸟,也是匆匆忙忙地离去,连一声嘶叫都舍不得留下。
没办法,这灼人的烈日带来了太高的温度,任何喜阴的生物都不愿停留于此。
炎热的环境不但使人感到不适,还会令我回忆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到了晚上,这里就变得截然不同了。美丽的黄昏还没完全过去,十字路口的灯火就已经亮起。我从旅店的简易木板床上起身,到老板那结清了费用,然后走向了门外。
赶了半天的路,又在旅馆熬过了一下午的炎热,夜晚,才是我们亡灵的主场。
“旅途平爱。”憨厚的牛头人向我送出了他们种族惯用的祝福,我心怀感激地接受,然后转身出村,继续我的流浪。
经历了无数的战斗,我已遗忘了自己将要何去何从。我只知道这漫无目的的旅途已经失去了重点,除非我能重新找回曾经拥有的信念或者——迎来死亡。
当我路过一个小土坡的时候发现了一堆现成的食物,哦不对,是尸体。有联盟的,也有部落的,但现在大家都和和气气地躺在一起,再也不是敌人了。
在那几具部落的尸体当中,我看见了一副似曾相识的脸庞。一个牛头人,萨满。
我认识他的时候阿拉希盆地的争夺战正打得火热。这位萨满,大地的司仪,部族中倍受尊敬的长者,我总是看见他坐在伐木场的崖边拿着一根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烟枪“啪嗒啪嗒”地抽着。我很喜欢坐在他的旁边向着那富饶的盆地张望,这位牛头人,灵魂的医者,在他身旁我着实能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宁静。
我没有看过他召唤那传送中的雷霆风暴,更没有见过他身边那两头威风凛凛的幽灵战狼,他总是在战场上吟唱着闻之心安的咒语,将一道又一道治疗法术施放在受伤的战士身上。有时我也曾斗胆地问他是不是不想杀人,他只是笑了笑,然后平静地告诉我:
“我少杀一个,他们就多活一会儿,既然我们终将化为风与土,又何需让他们提早面对这灵魂升天前的仪式呢?”
是的,我们终将化为风与土。
萨满的腰间系着一把精致的战斧,若是令它经过平衡石的磨砺与风怒图腾的增抢,我相信这会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器。
可是牛头人始终没有扯开那系住战斧的绳子,它就像自己的主人一样,未曾沾染半点鲜血。
说来可笑,不想杀人,仅仅治疗自己的战友,这不也是一种间接的杀戮方式吗?可这个时候,我却笑不起来。
我叹了口气,跪下身从他的腰间取下斧头,然后向着他的尸体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我不忍用这把利斧撕开敌人的躯体,但我可以把它带回雷霆崖,将这位牛头人祭祀的武器与它的信念一起,葬在灵魂高地。
就这样走完这条路——我们终将化为风与土。
我离开牛头人的尸体走向了那群联盟,带着一份遗憾——不是我铁石心肠,这种诀别在战场上我已遇到了无数次,对于勇士的尸体我们应当致敬;至于悲伤,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多杀几个敌人就是最好的复仇,难道不是吗?我是战士,无法像牧师一样为死者的灵魂祈祷,挥动武器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很快我停留在一具看起来比较“新鲜”的尸体前,这是个面容姣好的女性人类,从她身上所着的板甲来看她应该是一名圣骑士。可是斯人已逝,再虔诚的祈祷也换不回圣骑士的生命,作为一名圣光的引导者,这是何等的讽刺。
我已经忍受不住肚子里发出的“咕噜”声,亡灵是不会饿的,但是面对尸体与鲜血我还是无法抑制,这不是冲动,而是本能。于是我低下身,慢慢靠近她的尸体——肚子饿了,就要吃点什么。
然而当我把嘴凑到她的喉咙处时,一股微弱的呼吸声却传了过来。亡灵是没有呼吸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类还活着。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其他联盟的尸体都已经开始了腐烂,唯独她的皮肤还保持着活人独有的色泽。
我闭上了口水泛滥的嘴,又将头缩了回来。我不敢吃活人,不像某些过激的被遗忘者一样,趁敌人还没死绝用自己的尖牙撕开对方的喉咙,享受活人在死去那一瞬间的新鲜感。但是我很反感这种方法,我们是被遗忘者,不是亡灵天灾,不应该做那种残忍的事。
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这个人类的伤势后,我又不得不感叹她的生命力之强。先不说身上那些细小而繁多的伤疤,光是她背后那道十几公分长的大口子就足够使一个普通人失血致死了,更要命的是,板甲的连接处的细绳紧紧勒住了她的伤口,使鲜血在更短的时间内染红了原本是土黄色的地面。
让她解脱吧,再这么下去她会死得更加痛苦。
我取出的匕首慢慢抬升,对准了她的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