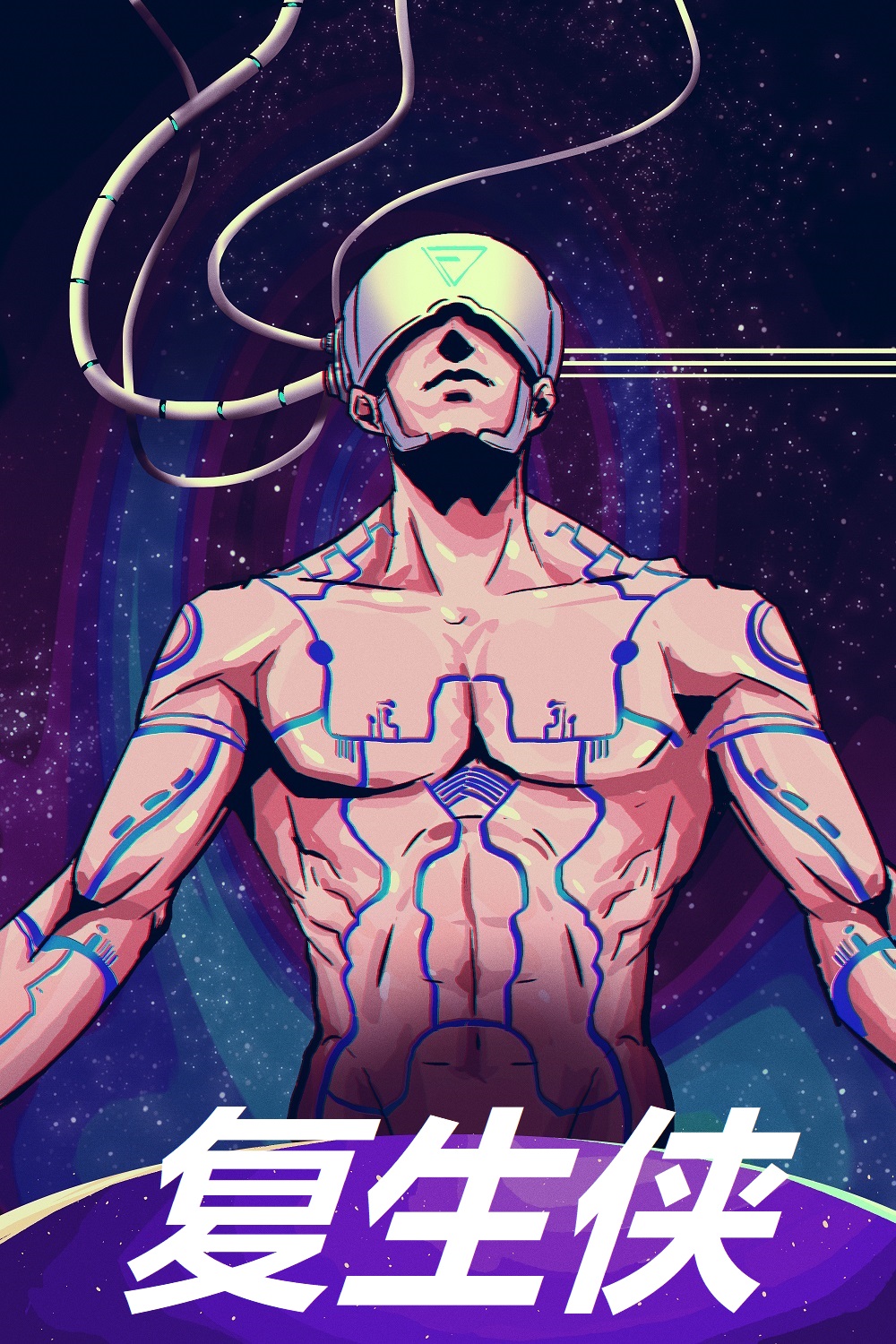清道光二十五年初秋的一个清晨,盛夏刚过,神州大地处处透着一丝丝宝贵的凉意。四川省川北道潼川府蓬溪县城厢镇县衙内宅,新到任不久的知县徐杨文保,正端坐在书案旁,聚精会神地看着昨天送来的邸报,时不时地露出愉悦的笑容。新知一县,事物繁巨,邸报到了马上翻阅的习惯也只好扔到一旁。昨天的邸报上一条石破天惊的消息,是林则徐大人被圣上召回京城,要重新启用了。前些年,由于虎门销烟,大英帝国发动了对我大清的战争。洋人妖术太过厉害,导致我大清战事失利。圣上迁怒于林大人,把林大人一贬再贬,流放到天寒地冻的蛮荒僻地伊犁。一向对林大人敬若天人的徐杨文保愤懑不已,在传出王鼎大人因此而自杀进行尸谏的消息时,自己也差点追随王大人而去。好在这些年自己四处打探到的消息都还不错:举朝钦佩的林大人到新疆后,甚受各级官差敬重;去年圣上甚至下旨让林大人查勘回疆。当时就纷传圣意已回,林大人即将再获重用。但天威难测,也不能太当真。没想到不到一年光景,传言成真了。徐杨文保看得心花怒放,一只手忍不住轻轻地叩起了书案。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击鼓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徐杨文保的怡然心境。
各地衙门虽然都有登闻鼓的设置,但各个地方、各行各业,都有相应官吏代天宣教;各种民间纷闹,也都各有处置之道。是以,登闻鼓基本上就是个摆设。但凡登闻鼓一响,一定就有大事发生。徐杨文保听得
心惊,赶紧从椅子里站起身来,看到夫人已经急步走了过来,问道:“老爷,这个声音是?”徐杨文保缓缓道:“有人击登闻鼓,必是有重大告诉。”夫人听得心慌,急急走到衣帽间,取来素金顶戴的官帽,鸂鶒补子的官服,给官人穿戴上,一众仆役早已团团围了上来。徐杨文保着好穿戴,迈步出门,刚到二堂,只听一阵碎碎的脚步声急速而来,却见典史刘文定推门而入,急急地欲下跪行礼。徐杨文保摆手道:“罢了,快说吧。”刘典史垂首急道:“谢谢老爷。出大事了老爷!”徐杨文保淡淡地道:“不必急,慢慢道来,说得清楚些,简短些。”刘典史道:“是老爷。今天凌晨,曾天佐老爷把江家湾江大黄的房子烧了,把江大黄打了个半死,抬着江大黄,捆绑了他的女人孩子,拉到城里来游街示众!江氏族人纠集了二百多人,夺回了女人孩子。但曾家放出狠话:再夺江大黄,谁去打死谁!现在双方人马在鳌峙阁下对峙。听说曾家老爷已经派出拜贴,四处纠集人众,要把江大黄的女人孩子再夺回去,把三个人全部打死!江氏族人来了二三十人,在衙门外击鼓告诉。”徐杨文保听得勃然大怒,狠声道:“本县初来此地,尚以为此地民风淳朴,人民良善,不曾想竟有如此土豪劣绅!”这个曾天佐是蓬溪有名的大乡绅,在朝廷捐了个正七品员外郎的虚衔,也算朝廷命官。徐杨文保就县后,曾天佐是第一位为他设宴洗尘的乡绅。当日不仅蓬溪县名流尽出,就是邻县的同侪乃至潼川府的僚属,也到了好些,诚然是高朋满座,珍馔毕阵。曾天佐本人也举止得体,极尽礼数,是以徐杨文保本来对他印象颇佳,不意今日竟闻此恶行。刘文定见县尊盛怒,扑通跪了下去,叹口气道:“老爷息怒,那曾老爷也是被惹急了。”徐杨文保冷声道:“如何惹急了?”他想来,这江大黄从未听说过,自是一介村夫,曾天佐乃是蓬溪县数一数二的大势力,江大黄再恶,又岂敢招惹曾天佐到何等地步。必是这典史经常受曾天佐的好处,自然说话上要帮衬些。却听得刘文定说道:“曾天佐老爷一家是三代单传,谁知江大黄用药竟把他家男胎给打了下来,所以曾家上下全红了眼!”徐杨文保听得心中骇然,情知刚才内心错怪了刘文定,寻思道:“这江大黄必定不是真名,多半是个郎中,因擅用大黄而得名。想是曾家有六甲之妇得疾,延请江大黄诊治,被其误用大黄而打下胎儿。大黄本是妊娠禁药,曾家偏生是一线单传,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麻烦!”对刘典史道:“起来说话吧。江氏族人在衙门外是何情形?”刘典史站起身来,垂手回道:“江氏族人来了二三十人击鼓,为首者全是老者,其他人都整齐地排在老者身后,把江大黄的女人孩子围在中间。卑职已经让他们在大堂候着,只有那几位老者和江大黄的女人孩子进了大堂,其他江氏族人没有进来,都在月台上站着。很多老百姓已经赶了来,围在外面看热闹。”徐杨文保心下暗想:“江氏族人这些表现,步步都含深意,不像寻常村夫的作为,里面必是有见识的人存在。曾江二族,一家势大,一家人众,偏生事情的曲直,并不分明。这事儿须得谨慎处理才是。”计较已定,遂对刘文定道:“你且先去大堂,说本县即刻就到。说话和气些,不可生出事端。”刘文定道:“卑职理会得。”急急打躬而去。
徐杨文保问门外道:“谭先生来了吗?”只听门外谭师爷的声音道:“学生在这里了。”徐杨文保当即迈出门来,阻止了谭师爷的行礼,问道:“事情的经过想来先生已听闻了。”谭师爷道:“学生听说了。那江大黄是一郎中,百病皆用大黄,这次误用大黄把曾天佐老爷的媳妇儿的男胎打下来了。”三言两语,把刘典史没交待的都交待清楚了。徐杨文保听得暗暗点头。他知道本地风俗管儿媳妇叫媳妇儿,与北方大是不同,说道:“本县已推想到了。此事眼下第一急务却是什么?”谭师爷回道:“学生想来,应是先保住江大黄的性命。”两人边说边走,向大堂而来。徐杨文保道:“先生所说极是。眼下急务,需得以审鞫名义把江大黄抬到县衙来。”谭师爷道:“但是东翁要是亲自前去,一则衙门脱不开身,二则江氏族人见东翁与曾员外寒暄,势必认为官官相护,恐怕当场激起民变;如东翁不去,捕头自己前去,曾员外则会认为东翁意图偏袒江大黄。曾家偌大的家业,却独苗被拔,曾员外恐怕连自己死的心都有了,见此如何不恼?轻则不肯交人,重则当场就把江大黄打死了。”徐杨文保道:“正是。”谭师爷接着道:“而东翁初履此地,众百姓尚不知详情。学生要是前去,与曾员外交通,则曾员外知道东翁赏识学生,此去如同东翁亲临;而江氏族人则以学生一县衙僚佐,参见曾员外自是寻常礼数,也不以为怪。所以学生须得陪同刘典史走一遭!”徐杨文保道:“正当如此。”说着话,脚下丝毫不缓,从宅门进入了大堂。堂下皂役齐声地吼起堂威来。
徐杨文保缓步登上台阶,徐徐走到公案后坐下。抬眼望去,只见月台上挤满了人,把大堂围得水泄不通。堂下跪着七八位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头前却跪着一个妇人一个约莫十来岁的孩子。那妇人浑身泥尘,披头散发,目光呆滞,额头嘴角都是血迹;那孩子始终埋着头,全身还在簌簌发抖。二人身上的绑缚都尚未解除,这绑缚自是曾家人干的,徐杨文保佯装不知,一拍醒木,怒对堂下皂役道:“一个妇人一个孩子,能有多大过恶?你们绑缚人家干什么?如此混账!”语音刚落,月台上嗡嗡声立即响起,人人交头接耳。刘典史正要跨出回话,中间的一个老头却立即叩头道:“禀县尊大老爷,这事和差爷们无关,是回龙场曾天佐曾大老爷干的。”徐杨文保知道围观人群中必有曾府耳目,一言不慎就会对鳌峙阁下的局势火上浇油,遂和声说道:“老丈年事已高,站起来说话吧。”那老头并不站起来,叩头道:“谢谢大老爷。草民等冒死击鼓,惊扰县尊,实在罪该万死。但郎中江大黄现在命若游丝,事在紧迫,不得不然。曾府有内眷身怀六甲,因为有恙,延请江大黄诊治。江大黄歧黄之术,名传四方,所以曾大老爷才不惧路远,重礼延请。不曾想曾府那内眷不耐药力,当晚却流了产。大老爷明鉴:自古医者仁心,但纵使华佗再世,扁鹊复生,也绝无包治百病之理。退一万步说,即使江大黄用药有甚差池,也自有官府明断。但曾大老爷身为朝廷命官,却指使曾府上下,火烧江大黄私宅,毒打江大黄一家三口,又把江大黄全家押往城里游街示众。草民等族人实在看不过眼,冒死抢回江大黄的妻儿,现在江大黄还在鳌峙阁下示众,即将被折磨致死了,恳请县尊大老爷公断!”
这老头一说完,叩头如捣蒜,其他几个老头和江大黄的儿子也立即不断地叩头,大堂外也早已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气氛悲壮。反倒是江大黄内眷,没有任何动静,显然是惊吓过度了。徐杨文保见那老者谈吐不凡,句句在理,不由暗暗称奇:“早闻自古蜀中多才俊,不想本县乡野之中,也有这等人物!”生恐江大黄在街上丢了性命,内心焦急,遂说道:“此事是非,跟江家母子毫无干系。来人,立即解去江家母子绑缚。江老丈,岐黄之术,非常人所能知。现在当务之急,须得立即拘传江大黄到案解明情由。江老丈,你可明白本县的意思么!”说完,徐杨文保不管大堂外一片哗然,也不管差役去解江家母子绑缚,只是定定地看着江老丈。那江老丈见知县下令为江氏母子解缚,又一口一个“江老丈”,再看知县望向他的眼神,立即明白了县尊之意,毫不迟疑地叩头回道:“但凭县尊大老爷区处!”声音说得特别地大,月台上的声音突然就静下来了。徐杨文保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吩咐道:“刘典史,你且带上四个衙役,火速前往鳌峙阁,拘抬江大黄到案。谭师爷,你一同前去,务必拘传江大黄到案,不得有所差池。”谭刘二人行完礼,挑了四个精干役卒,到刑房拟了差票,立即飞奔而出。
谭师爷一行六人急急往鳌峙阁赶去,一路上只见街面冷清,几乎见不到人影,与平日人来人往的景象大相径庭。还没到鳌峙阁,就早听得人声鼎沸,混乱非常。谭师爷对刘典史道:“我去参见曾老爷时,尊驾对江氏族人领头的私下交待,就说江老丈告诉到县尊老爷处,仰恳县尊拘传江大黄到衙实证情由。切不可再说别的。”刘典史道:“卑职理会得。”他知道县尊对这师爷倚重非常,说话就分外客气。
到了现场,只见鳌峙阁下人山人海,里里外外水泄不通。刘典史扯起嗓子大声吼道:“县衙办案,闪开闪开。”见到突然出现六位官差,人群先是一阵骚动,接着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沿着六人前进的方向,众人自动让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六人在周围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急速向鳌峙阁脚下行进。正走间,突然人群一阵大乱,只听得阵阵惊呼:“曾大老爷的亲家族人赶过来了,怕不得好几百人,全抄着家伙,不得了啦!”“曾大老爷的岳家也来人了,好大的排场,要出大事了!”“曾大老爷的姨表兄弟全族人都来了,蓬溪的地皮这次都得翻起来了!”“曾大老爷的同年王老爷也来了”......本来已经自动形成的通道,在人群一场混乱后,又重新堵得水泄不通。几位衙役何曾见过这个阵势,包括刘典史在内,人人脸上变色,胸中全是怦怦乱跳,只想着:“完了,完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谭师爷见事态危急,瞅准一个哄闹声稍小的间隙,对四个衙役中唯一的一个皂役吩咐道:“立即鸣锣。”那皂役双手乱颤,好不容易拿稳了锣和锣锤,终于“咣”地一声,重重地敲了下去。一声锣响以后,本来魂不附体的皂役突然来了胆气,“咣咣咣”地又是一连串的爆响。在富有节奏的激昂锣声中,人群渐渐安静下来。谭师爷立即抓住这一瞬,高声喝到:“奉徐杨县尊大老爷令,即刻缉拿江大黄到案鞫明案情,闲杂人等,即刻回避。”他声音洪亮,话语威严。片刻静默以后,人群如潮水一般向两边分开,齐刷刷空出一条通道来,直到鳌峙阁下。刘典史看得大为叹服:“刚才挑役卒时,我还对他竟然挑了个敲锣的皂役大不以为然。没曾想此人一介书生,谋划竟如此周密,胆气竟如此慑人!”谭师爷举步先行,五人紧随其后,向鳌峙阁走去。接近阁前,情势又自大为不同。只见约二三百人紧紧围着鳌峙阁,老弱在前,人人神情紧绷。众人的眼睛本来都盯着阁子,这时又不约而同地往官差看过来,多数人脸上都隐隐透露着悲愤和敌意。谭师爷佯作不知,对刘典史道:“典史和差哥们且留步。”然后独自向里面走去。只见最里一层,约摸着六七十人,有男有女,个个脸上都是杀气。曾大老爷身着便装,被一群人簇拥在鳌峙阁的台阶上。走近了看,只见他虽然衣衫整洁,却双眼通红,一脸憔悴和悲愤。再一扫旁边,谭师爷不由大骇:只见旁边一门板上躺着一个人,浑身是血,头脸也都已经不成人形。门板上插一竹竿,竹竿上挂着一白布,布上书着血红大字:“杀人恶医江大黄”。谭师爷心念电转:“这江大黄已经是活不成了,万万不可抬到县衙。且现在抬出去,江氏族人要看得真切,易激事端。再加之曾家的亲友正往里冲,一旦冲到江氏族人防线处,立时便会发生群殴,死伤必重;就是被他们见到江大黄,凭着刚来的新锐之气,也立时便打死了。”
一念及此,谭师爷即刻起步到曾天佐的台阶下,也不上去,长揖为礼,沉声道:“学生奉徐杨县尊命,参见曾大员外。”他身为幕宾,见徐杨文保也不用下跪。曾天佐知道这个师爷与一般师爷不同,极受徐杨知县的信任。但他万念俱灰,只是手虚抬了抬,嘶哑道:“谭先生免礼。”谭师爷知道江氏族人听不到他的说话,遂拱手道:“县尊对当日大员外款待之殷、讲论之欢,一直念念不忘。今日一早闻大员外遭此大变,老爷勃然大怒,对江大黄痛恨已极,严令刘典史立即缉拿江大黄到案究治,并命学生代他来此地向大员外致痛切之意!”曾天佐到底不肯失了礼数,双手拱了拱,道:“多谢徐杨县尊抬爱。”谭师爷听得人群哄闹的巨浪越来越近,知道曾氏亲友一旦冲到江氏族人防线处,大祸将立即酿成。他脸上神色不变,续道:“学生临行前,徐杨县尊说道:曾员外几代富贵,积善有余,总听各处乡民称颂员外种种善举,上苍有眼,必不致其断后。本县知道一郎中,妙手回春,善繁人子息,吾本家多人受益。本县当代为招致。”曾天佐一听此言,突然哽咽下泪,道:“徐杨县尊天高地厚之意,曾某没齿不忘!”谭师爷立即低声道:“曾大员外,学生初通岐黄,我看这江大黄熬不过一时三刻了。曾大员外金贵之身,不宜与此等村夫攀扯;曾大员外贵戚高友皆为大员外高谊而来,也犯不着涉此无妄之灾。大员外宜速离此地,学生和县尊自会斟酌善后。今晚深夜,学生将赴贵府,协商处置之道!”曾天佐抬眼看了看江大黄,情知谭师爷所言非虚,又听得哄闹声如潮水般涌来,明白一场大祸迫在眉睫。他的心被谭师爷说活了,也就有了顾忌。想了想,向谭师爷拱手道:“那在下先行告辞。县尊和先生的成全之德,敝人容后报答。”谭师爷立即长揖相送,一边说道:“这人也不能往县衙抬了。”他是为接下来的处置给曾天佐打个底。曾天佐对周围沉声道:“走吧。”有人目示江大黄,曾天佐微微摇了摇头,向外走去,立即有人冲前带路,其他人皆跟随曾天佐身后,长长的队伍鱼贯而出,所经之处,人群都立即向两旁散开,到得远处,只闻好一阵吵嚷,显然是曾家援兵跟曾家会合了,一只庞大的队伍逐渐从谭师爷的视野中消失。
谭师爷惊魂甫定,才发现全身内衣已经湿透。随着曾家人众悉数撤离,江氏家族的人都冲了过来,围在江大黄的身边。看到江大黄的惨状,顿时嚎哭声、怒骂声响彻四方。刘典史等人也冲了过来,围在谭师爷身边,个个内心都钦佩无已。谭师爷向江氏族人看过去,刘典史立即指了指其中的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谭师爷在衙役的护卫下,挤到了那中年人身边。中年人已有察觉,回过头来,也没法下跪,只得垂首说道:“草民见过老爷。”谭师爷拱手向天道:“感谢上天!总算不负徐杨县尊所托,把江郎中救了出来。尊驾赶紧把郎中抬回去,立即延医诊治,晚了恐就来不及了。”那中年人见衙役并不拘传江大黄,益信谭师爷之言,含泪道:“草民及江氏全族人叩谢县尊大老爷和官爷的救命大恩,江大黄蒙受此等法外大刑,尚请大老爷等务必为他伸冤。”谭师爷暗想:“他们与县衙那老丈必定计议过,所以分辨得如此明白。”说道:“不消说得。徐杨县尊爱民如子,自当为江郎中全力周旋,赶紧救人要紧。”他用“周旋”一词,自是提醒对方,曾大员外势大,并非一县之主所能定夺。江家一干人等,含泪谢过,抬了江大黄自去了。人群也逐渐随之散去。
谭师爷与众官差回到衙门,只见在大堂外围观的人群反而倍增。进得大堂,却见官堂上除了徐杨县令外,居然还有那江姓老丈,且也已被县尊赐座官堂!徐杨知县正对江老丈言道:“我大清地域辽阔,方圆难知,不曾想全国二十四孝,竟有两孝在本县,实在是神奇之极!”话声轻松淡然,只有谭师爷才能感受到那刻意掩盖起来的巨大不安。一转头,看到谭师爷等人空手而回,徐杨县令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谭师爷紧赶几步,长揖下去,道:“江大黄性命危在旦夕,学生已体察县尊爱民如子之心,着江氏族人抬回家去,立即延医诊治。曾天佐员外经学生转达县尊晓谕律法的话语,也已经率同曾氏族人以及新近赶来的亲家、岳家、同年等所有人等离去,静候县尊裁决。闲杂人等也已经散去。”徐杨知县控制不住地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自然知道谭师爷一句“新近赶来的”蕴含了多大的凶险,忍不住道:“先生辛苦,可以歇歇去!”谭师爷长揖退开。徐杨文保道:“江老丈学识渊深,对蓬溪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方才一聊,本县受益匪浅!”江老丈道:“草民乡间粗野村夫,得蒙大老爷不耻下问,何幸如之!”徐杨文保神色一整,说道:“江老丈,这城厢镇左近,除了江大黄以外,是否尚有其他知名的郎中?”江老丈道:“自然是有。这城厢镇里就有李黄这二位一个城东一个城西的郎中,虽不如江大黄,却也是城厢镇人尽皆知了。”徐杨文保道:“既是如此,那就有劳老丈。对六甲之妇用大黄,世人皆言其非,但岐黄之术,非世人所能知,请江老丈再约上江家一位精干的小哥由王捕头和差哥们护卫,去逐一向两位大医家请教,这大黄用得是耶非耶?”江老丈迟疑了一下,只得应了。徐杨文保低声对江老丈道:“江大黄妻小,须留衙中以策安全。”随即正声道:“江老丈请下去吧!”
江老丈叩头后,走下堂来,在大堂中间跪好。徐杨文保一拍醒木,人群肃静后,知县说道:“曾江二家讼案,案由复杂,须逐一厘清后本县遵朝廷法度禀公办理。现着由江老丈及江家随伴人员,前往访问本县知名郎中,了解处方是非,着由王捕头率同衙役一起前去;江大黄妻小暂押羁候所,候本县了解详明案情后着衙役送回;江大黄由江氏族人及时延医诊治,待案情大白后,一总处分。”月台上人群一阵喧哗,只听得江老丈等叩头谢恩。县尊再一拍醒木,喝道:“散堂。”走下堂来,迈步向内宅走去,谭师爷紧紧跟了进去。
走进宅门,徐杨文保回过头来,满脸笑容,对谭师爷道:“今天若非先生,想来鳌峙阁下要尸山血海了。”谭师爷拱手道:“都是东翁思虑周详,措置得当,才能化险为夷。刚才着令江老丈去访问郎中,真是神来之笔啊!”徐杨文保微微一笑,道:“愿闻其详。”谭师爷道:“本公案,曾家几代单传的血脉,被江大黄断送,其放火打人,虽在国家法度之外,却也在世道情理之中;江大黄,虽酿成大祸,但其只有取利之意,却无作恶之心,加诸私刑于其人,终为国家法度所不容。曾家势大,有必死之心,江家人众,有难让之困。所以本案措置,稍有不慎,即成火上浇油,酿成重大血案。故此,县尊立足于先化解双方的锐气。江氏族人,显然以江老丈为首,江老丈挫则众人挫。县尊知道江大黄用药,犯了医家禁忌,但却不能由县尊直接说出来,以免激怒江氏族人。是以,县尊让江老丈亲访医家。自古同行相妒,想那江大黄平日何等风光,必定早遭同行妒忌,又何况他用药本就不循正道。江老丈此番只消前去,那两个郎中必是对江大黄用药大加挞伐,说得一无是处,以出胸中憋了多少年的恶气。当着众差哥的面,江老丈自是愈听愈丧气。东翁这番调度,真是神鬼莫测啊!”徐杨文保笑道:“那江老丈精着呢,好像有所明白,但苦无推脱之道,勉勉强强应承下来了。你那边呢?先生是怎样化解曾员外的锐气的?”谭师爷道:“曾员外家大业大,本来不敢干犯大案。他的锐气来自于必死之心,必死之心来自于绝嗣之想。学生就想起了东翁以前讲过的一个医家,颇能调人精血,所以就擅自帮东翁做了一回好人。”就把当时的说话讲了一遍,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徐杨文保道:“现在还有两件事急待处分:一是着人盯着江家湾,一有动静,立即上报;二是咱俩转往羁候所,需要向江氏母子打听些情况。先生猜猜是要打听什么情况?”谭师爷凝想了一会,问道:“东翁要打听的情况,是作何用处?”徐杨文保道:“要进一步消消曾员外的锐气。”谭师爷道:“学生明白了。”彼此相视一笑,回转身,向羁候所走去,一边吩咐人去江家湾窥探消息,并给江大黄送了些上等的三七等专治跌打损伤的良药。
到得羁候所,刘典史等人都站在一旁候着。徐杨文保见那江大黄的女人还是神情恍惚的样子,心里着实有些可怜,但知道衙役中曾家耳目不少,却也不能给予什么关照,遂对谭师爷道:“师爷你来问吧。”谭师爷拱拱手,趋前说道:“江氏妇人你且听好了,有一些问题徐杨县尊需要知道缘由,事关你男人的生死,务须如实回答。你男人以前可对怀儿婆用过大黄么?”那妇人迷迷糊糊的,并不作答。谭师爷又问了一遍,那妇人恍若未闻。正没理会处,突听一个童音道:“家母惨遭大变,心神昏乱,无法回复老爷的问话。但小人知道,家父以前也常对六甲之妇使用自家秘制的大黄,都是药到病除,却并无一例有甚变故!”说话的却是江大黄的十来岁的儿子。徐杨文保和谭师爷皆是听得又惊又喜,惊是惊这孺子年纪虽小,却如此聪慧过人;喜是喜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徐杨县尊细细打量,见小孩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衣衫皆是绸缎所制,只是手脸有些微伤疤,想是曾家族人动手时到底对孩子没有太下狠手。徐杨县尊问道:“你这孩子,叫什么名字?”那小孩道:“回禀老爷,小人名叫江正品。”徐杨县尊颔首道:“想是你父亲希望你人品正正当当,所以给你取这么个好名字。你父亲用大黄治六甲之妇的医案,病人是何方人氏,所患何病,所拟何方,你还能记得一些吗?”江正品回复道:“这三年来,除曾家外,家父治疗六甲之妇十一人,皆用大黄,这些医案小人全部记得!”徐杨文保心下大喜,却是不动声色,道:“你可能一一写下来?”江正品道:“能,小人都能详细写出来。”徐杨文保道:“记得确切的才写,可不能写错了。刘典史,且将这二人带到二堂,给予笔墨,让江正品把医案都写出来。”刘典史等人自去了。
徐杨文保带着谭师爷,漫步向大堂方向走去,一路上对江家小子江正品的聪敏赞叹不已。登上月台,谭师爷道:“东翁何时枉驾前往回龙场呢?”徐杨文保道:“在等能压倒西风的东风啊。”谭师爷道:“东翁要的东风,一个是江家小儿写的那些医案,须要一个个核实;另外一个,想来就是江大黄的死讯了。”徐杨文保问道:“那江大黄当真没救了?”谭师爷道:“学生看来,神仙难救,恐怕死讯今天就会到,只在早晚而已。”徐杨文保喟叹了一番,道:“江大黄若侥幸能活,曾家还不会善罢干休;江大黄若死,江家就剩这一母一子,曾家一则理亏,二则也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也就罢了。所以这江大黄的生死之间,去回龙场的说话可是完全不同的。”谭师爷由衷道:“东翁高明!”
正说着话,那刘典史把江正品写的医案十一则已经拿了过来。每一则医案的患者姓名、居所、诊治时间、症状、诊断、处方、疗效都一清二楚。徐杨文保和谭师爷看完,立即着刘典史安排人去逐一核实明白,取得供词。回到二堂,徐杨文保问江正品道:“你所述十一桩医案,件件都是杏林美谈。但大黄有破瘀散结之功,本是产科禁药,难道就没有发生过意外?这其中莫非大有隐瞒不报之处?”江正品叩头道:“自打小人跟家父学习岐黄之术以来,对六甲之妇施药,委实就只有这十一桩,并无瞒报情事。家父用于六甲之妇的大黄原是秘制,用十缸醋,九蒸九晒,最后得一缸醋,稠如蜜,亮如镜,再与雅黄合制成醋制大黄,和别人所用大黄完全不同。这本是家父天大的秘密,如今也不得不说了。老爷请想,要是家父以前用药有过差池,这曾大员外不是寻常人家,家父岂敢造次!”徐杨文保听他分辩得如此明白,说道:“江正品,你跟你母亲赶紧回家去见你父亲吧。你天生聪颖,多一些人生磨难,未始不是上天对你的一番美意!”那江正品才十一岁,虽然聪明,却哪里听得出这话中的深意。但他也知道这知县似对他怀有善意,叩头谢恩,扶着母亲去了。徐杨文保见他身小力薄,又恐途中撞见与曾家有牵连的人,遂命捕头安排了人一路送回去。
这边才走,那边陪同江老丈去访问郎中的差役却也回来了,说道李黄二人异口同声,把江大黄的处方说得荒谬之极。江大黄空有大名,实在是人们愚昧,也是江大黄运气好,才没有早出事,说他杀人恶医,那也是恰当的。说得江老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那江家小伙更是一头大汗。不过两个郎中也把曾大员外骂了一通,说眼瞎怪自己,怎么把气都撒到郎中头上,而且还殴打女人孩子,也忒狠毒了些。等等。江老丈和那小伙听完两个郎中的言语,也不肯回县衙,已经自去江家湾了。
到得入夜时分,江家湾传来消息,那江大黄苦撑到老婆孩子回来,也说不出话,就手拉着儿子,两行清泪下来,很快就没了气。徐杨文保遂安排可靠人员,到各处酒楼茶肆,四处散播消息。不到一个时辰,整个城厢镇都在谈论一件事:江大黄已经被曾大员外活生生毒打致死了。七品命官的曾大员外摊上人命大事了,不知头上的顶子是保得住保不住。
徐杨文保一直坐在二堂的官椅上,不断听得这些消息传来,对谭师爷微微一笑,道:“可以去曾员外家了。咱们今夜来个夜访回龙场。”谭师爷道:“山路可不好走,东翁何不明日再去。”徐杨文保道:“夜间才能秘访,而且得赶上曾员外惊魂未定的时候。”吩咐杂役道:“备轿;去找夫人,把家里珍藏的那枝百年老参带上。我且去更更衣。”最后一句话却是对谭师爷说的。
待得徐杨文保换上便装出来,一行人轿子火把早已准备妥当。二人坐上轿子,便连夜往回龙场而去。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续集:转胎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