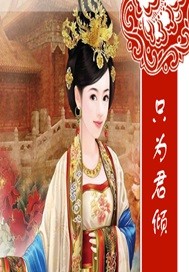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老板您误会了。”小笛子赶忙解释:“我离家数月,一直联络不到家姐,实在担心,我得亲自回家一趟看看。”
“奥,原来是这样。”李大年长舒一口气:“回家探亲而已,准你的假就是了,何须辞工这么严重。”
“是这样的。”小笛子据实以告:“我曾托故人前去探看,说是家姐已经将房舍转让,不知所踪,所以,我先回去看看,若真如故人所言,我就得去追寻家姐踪迹,时日长短,不好断定。为了老板生意,我也不好空居其位,所以思虑再三,觉得还是辞工的好。”
李大年闻言,凝眉沉默良久,问道:“你这捎信的故人可靠得住吗?他确实是亲眼所见你家境况吗?”
“是相熟的故人,靠得住,他确实亲眼所见。”小笛子心急火燎 ,情绪低落:“所以还请老板快快核查账目,小笛子实在归家心切,请老板见谅。”
“既如此,”李大年若有所思:“三天,三天后账目交接清楚,就放你走。”
“多谢老板体恤。小笛子告退。”小笛子如释重负,告辞出来,天色已晚。小笛子没顾上回自己住处 ,而是又挨个商铺巡查一番,直到宵禁,各个店铺上锁完毕,才在街头小挑儿吃了一碗馄饨后回了李老板给他安排的暂居住处。
自从他住到这里来,住在一墙之隔院落里的李老板的侄儿李舂山就总是针对他。
他本来是和商行的伙计们一起住大通铺的。三个月后,李老板非得让他搬到这个独立的院落里来。说是顺便帮他看着这处宅院。
起初只是院门锁眼被堵,或者院子里被扔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以为是哪家顽童所为,都没怎么在意,后来逐渐发展成泼屎泼尿,他才意识到是有人故意针对他,特意蹲守了几次,终于抓到了始作俑者,正是李老板的侄儿和他那帮整日混迹赌坊的狐朋狗友所为。
他也不是逆来顺受的性格,这些人再一次被他抓现行的时候,他毫不客气的将他们狠揍了一顿,打这以后才算太平了。
他不去找李老板告状,他那侄子更是不敢去。据小笛子所知,李老板的哥哥瘫痪多年,他们全家的生活开销都靠李老板供给,李老板曾多次安排侄子到自家商行工作,想培养他成器,可他偏偏嗜赌如命,不肯务正业,手脚更是时常不干净,偷偷摸摸。时间一长,李老板也就懒得管他,听之任之了。
虽然很久以来李舂山都没再来找小笛子麻烦,小笛子还是养成了每次回家都里里外外先检查一遍的习惯,确认没有问题了,才回房间沐浴休息。
“什么?都进去内宅了?”李舂山听李大年府中一个和他一样喜欢混迹赌坊的家丁说了当日所见,李舂山牙齿咬的咯咯响:“老不死的,我看他真是老糊涂了。自家子侄好好的不重用,倒是把商铺上上下下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李舂山当即决定,既然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当晚,李府起了一把奇异的大火。
李家小姐也不知所踪。
小笛子被破门声惊醒的时候,梦里还在惦记两位姐姐到底去了哪里。
衙役们不由分说,直接将一脸茫然打开房门出来查看的小笛子摁倒在地,呼呼喝喝押往衙门。
衙门大堂下跪着的李老板满面灰黑,哭的涕泪横流,被李舂山搀扶着,才勉强跪在地上没有瘫倒。
小笛子大惊,赶紧跑上前,蹲下去掺李老板:“李老板,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李老板只知道哭,李舂山一把将小笛子推开:“你还有脸问?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马上有衙役抢过来,将小笛子摁着跪倒在地。
小笛子一脸茫然看着狼狈不堪的李老板:“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时官老爷升堂了,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堂下所跪何人?”
李舂山替泣不成声的李老板回话:“回大人的话,草民李舂山 ,陪我叔润丰商行老板李大年,状告润丰商行伙计小笛子 ,夤夜纵火,劫掠少女。”
官老爷又看向小笛子:“你就是小笛子?”
“是的。”一脸茫然的小笛子老实答道。
“李大年状告你夤夜纵火,劫掠少女,你可认罪?”
“我,我没有啊!”小笛子满目惊慌,赶忙解释,又对着李大年连连摆手:“李老板,李老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啊!不是我,你要相信我。”
官老爷一拍惊堂木:“你应该自称草民。”又转向李大年:“李大年,你何以一口咬定是小笛子所为?”
李大年闻言,勉强收了眼泪,恨恨的看了小笛子一眼,哽咽道:“今天下午,小笛子拿着润丰商行的所有铺面总账册来府里寻我,说要交账辞工,我也没多想,可是入夜以后,书房就着火了,偏偏哪都不烧,就先烧了他送来的账册,草民这才起了疑心。谁知火尚未灭,丫鬟又来报,说小姐被一群黑衣蒙面人抢走了, 草民才确定是他。”说着李大年又抹起眼泪,恨恨的对着小笛子:“我如此信任重用你,你亏空款项怕被发现,烧了账册也就算了,下午小姐是说了几句瞧不起你的话,可你也不能,也不能……呜呜呜……我可就这一个女儿啊!你把她怎么样了?你把她还给我吧,求求你了,你就把她还给我吧……”
小笛子终于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着撕心裂肺哭嚎不止的李大年道:“李老板,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
接着,官老爷又传唤了李府门房,管家,丫鬟,家仆等一应证人,矛头皆指向小笛子。
“小笛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官老爷冷冷瞪视着他。
“我,我……大老爷,草民冤枉,草民没做。”小笛子脑中混乱,胡乱辩解着。
“那你可有证人?”官老爷又问。
“证人?什么证人?”小笛子茫然。
“夤夜子时,你在哪?”官老爷提醒道。
小笛子想了想:“草民,草民在睡觉。”
“也就是没有证人喽?”官老爷问。
小笛子无措的摇摇头:“没有。”
李大年闻言忽然暴起,扑过来撕扯他:“你说,你说,你把我女儿藏哪儿去了,你快把她交出来,交出来……”
这时有衙役上前呈上一物:“大老爷,这是在小笛子居住院落里找到的。”
李大年一看到衙役手中捧着呈在官老爷面前的物件,马上更加失控起来,撕扯着小笛子:“这是我女儿的簪子,你把她藏哪了,你快说,你快说啊!……”
小笛子整个人都蒙了,只知道喃喃的说:“我没有,不是我,我没有……”
“肃静……”官老爷一拍惊堂木,衙役马上去拉开撕扯住小笛子不放的李大年。
“小笛子,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要说?”官老爷冷冷的问。
“我,我,草民冤枉,不是草民干的……”小笛子无力的辩解,事发太突然了,他完全脑子里一片混乱,什么也抓不住。
当板子狠狠打在身上,他才反应过来,官老爷已经决定给他用刑逼供了。
他没有做过,又让他怎么说出小姐的藏身之处呢?
小笛子咬牙忍着,听着板子扑通扑通打在身上的声音,逐渐冷静下来。
一定是李舂山搞鬼。
可是知道又怎样,他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