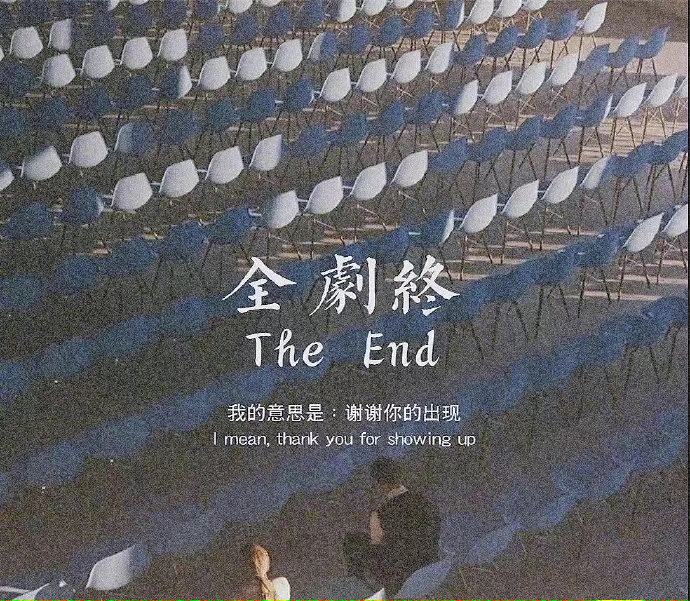旧历十月初一,是杨琳的生日。作为对方的好朋友,安漓很自觉地从九月开始攒钱。杨琳生日前一天放学后,她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水晶球。球里面站立着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女孩,金色白色相间的细屑在里面浮浮沉沉,拨动底座下的黑色开关,水晶球还能发出五颜六色的微光。
安漓没见过什么稀奇玩意儿,对自己准备的礼物颇为满意。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赶去学校,把仔细包装过的小盒子放在了杨琳座位上,期待着对方惊喜的模样。
七点、七点半、八点…手腕上塑料做的电子手表不停跳动,像是在把时间往前驱赶。可一整个上午,杨琳都没有来学校,老师对此事已是习以为常。安漓隐约记得,班主任一开始总会打电话去问相关的情况,每次通话时间都得近十分钟,透过窗户,没人知道走廊上情绪激动的陈老师到底在说些什么,老师不主动提,也没人敢问。
杨琳自己也不肯说,面对年龄普遍比自己小两三岁的同学们的关怀,她永远只是笑着回答,没事。
下午第一节课下课后,有人从教室外跑回来,一边大声嚷嚷着:“我看见杨琳了,她和她爸爸在陈老师办公室。”
安漓犹豫片刻,正欲拿起那份礼物去办公室外等她,预备铃又响了,只得作罢。
这节是音乐课,还是学上周那首学了一半的《外婆的澎湖湾》。安漓的外婆离开得早,她脑子里没有外婆的概念,也体会不了音乐老师所讲的“三温”,温暖,温馨与温情。于是一整堂课她都在开小差,快下课时,她看见了走廊上杨琳的背影。
尽管将平日里的低马尾换成了披肩发,但凭借着高挑的身形和熟悉的粉外套,安漓还是能一眼就将她认出来。
下课铃一响,人和礼物就抢在老师前面夺门而出。安漓拍了拍杨琳的肩膀,将系着蝴蝶结的盒子递到她面前。
“生日快乐。”
杨琳转向她,迟疑着接过礼物,安漓才看清眼前好友通红的眼眶。以前,从没见过她流泪。
“谢谢。”
两个人都转身面向教学楼前的小操场站立,有足足一分钟,就沉默着,站着,视线游离。
“我以后都不会来学校了,对不起,之前一直没有跟你说。”
安漓有些意外。尽管在建安乡,甚至自己身边,也有过因为各种原因转学或退学的同学,但多数都是男生,且好些都是退一阵了,下学期又来了。但她始终没有想过,杨琳会退学。
杨琳是个对知识有着极度渴望的女孩,她家比一般农村家庭还要困难些,总有干不完的活,家里的兄弟姐妹总是轮流请一学期或半学期的假在家帮忙,这也是她15岁还在念六年级的主要原因。
和杨琳做朋友以来,在生活上,对方对自己总是处处照顾,而在学习上,两人则会角色互换。杨琳算不上聪明,甚至有一些呆板,但胜在刻苦和好学。每次大小考虽然拿不了高分,但能保持在85分上下,在班里也算是中上的成绩。
她想考大学,这是她在安漓生日那天写的信上的内容。
“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上大学了吗?”
“我爸爸让我回去结婚。”杨琳哽咽了,“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争取,陈老师也帮我劝过他,可是他铁了心要我退学。今天,我们是来收拾东西的。”
安漓脑海里形成了一个画面:在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她身穿铠甲,骑在一匹骏马上,手握红缨枪,指着面前被逼到悬崖边的杨父。
“把杨琳放回来!”
铃声再度响起,打断了她的思绪。小学下午只有两节课,这次的铃声是给初中生的信号,但也提醒着她该收拾书包回家了,天最近黑得早,她一个人回家太晚总会害怕。但今天,她铁了心要拾起将军应有的气魄,决心在这里陪好友待到最后一刻。
她不是个擅长说安慰话的人,12岁,对于婚姻唯一的概念就来自父母。然而,为人长者也没有做出好的表率,记忆里就只有无休止的战火和弥漫的硝烟。作为战争非完全意义上的旁观者,她需要做的,只是在战后打扫一片狼藉的战场——收拾碎碗碟留下来的瓷片。
家里完整的碗碟只剩四五只时,他们也都走了。
因此,在安漓的概念里,结婚算不得喜事。一个多月后的周一,安睨听见张国培在教室高声谈论喜宴上的见闻时,她就更加确信了,结婚是可怕的事。
张国培和杨琳是同一个村的。杨琳先前频繁请假的事,他向父母打听过,却只得到了一句“别人家的事,别瞎打听!”的敷衍。张国培对此事好奇,与其说是关心同学,不如说是为了回学校故弄玄虚,向大家显摆。
这个年纪的男生特点就是,调皮捣蛋,渴望吸引人注意,多数还有点没脸没皮。
“我吃完饭悄悄溜去新娘子的房门口看了一眼,你们猜,杨琳在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等新郎官呗!”
“也有可能在吃糖,我表姐嫁人的时候,她房间就特别多糖,我装了好多回家。”
…
吃完午饭,大家端着空饭盒你一言我一语地配合着张国培的卖弄。
“都不对!”
“那在干什么?”
“她坐在床上哭呢!谁劝都不听,她爸都急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被我妈叫走了,没见着。不过听别人说她后来又闹了两次,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消停了。”
安漓的新同桌姚凤叫她去洗饭盒,她这才从脑海里强抢民女的民国大戏中回归现实。
2010年,义务教育法早已出台。手机也不再是稀罕物,哪怕在乡里,寄宿的同学也几乎都是人手一部。社交工具腾讯QQ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社交平台,乡里热闹的地方有了网吧,学校也在这一年开了电脑课。
可是,杨琳受教育的权利依然得不到保障,无法顺利完成本应该完成的学业。安漓也不知道杨琳家的电话号码,她们俩更没有加上好友。
明明客观条件都有,但主观意愿却无法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