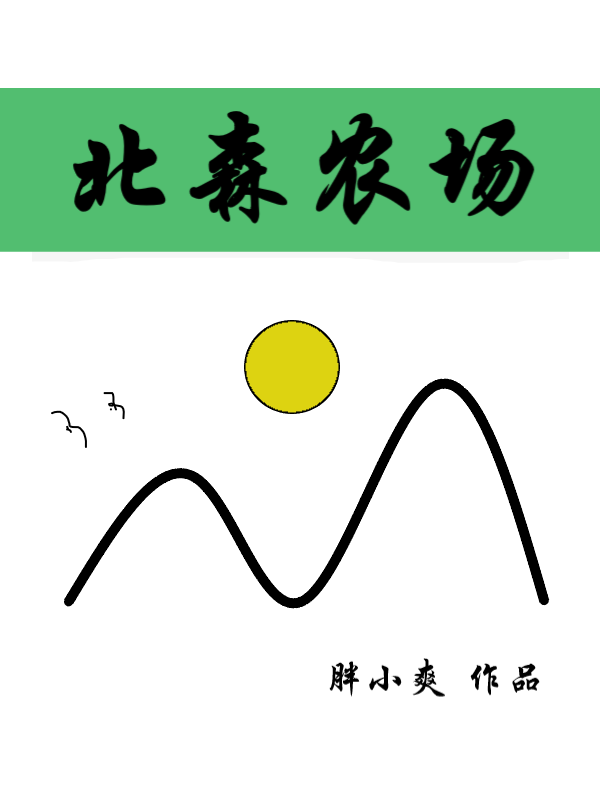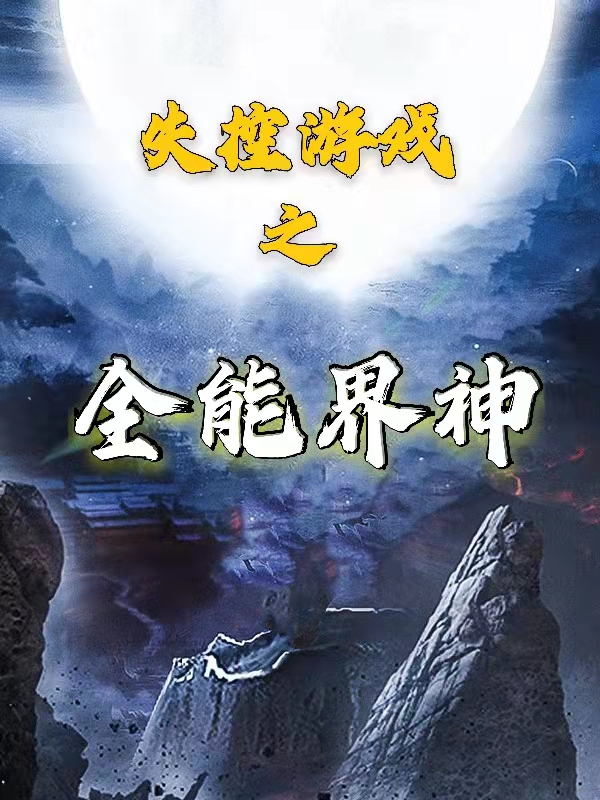“娘,回吧。”
王招娣和初春寒风中的婆婆挥了挥手,婆婆矮小的身躯佝偻着,凌乱的白发在风中飞舞。
“我挽挽袖子撸撸拳,一定上关东找到陈继元,不一男一女不回还”
招娣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毅然转身踏上北上关东寻夫的道路。
关东,千里之外。我的心上人哪,你到底在哪儿。
1920年的山东胶西县,乍暖还寒。村庄蛰伏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开始渐渐苏醒过来。庄户人睡得早起的早,虽是清晨,路上已经有了稀疏的行人。
招娣一身土布棉衣,挽着红色碎花包袱。包袱里面是她的全部家当,五块银元、几件换洗衣物和三双自己亲手为结婚六年相处时间不足一年的男人做的布鞋。
身后是自己生长了二十三年的家乡,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旁边的草垛和路边连成片的粪堆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是自己家的;天知道那一垄垄刚开始返青的小麦在去年秋天天旱的时候自己挑了多少水才种下的;那一群正在河里觅食的鸭子肯定是赵家的,想起自己家多年来被他们欺负招娣气得恨不能把河里的鸭子一只只连毛拔起。
“宝贝,这么早进城啊,怎么一个人,要不要哥哥陪你?”
赶着粪车的二狗挥舞着鞭子一脸坏笑。
“死狗,等俺男人回来打断你的狗腿”。
二狗是赵家老小,大名赵连意,二狗是外号。由于从小一肚子坏水,他本名倒是知道的人少。二狗上面还有三个哥哥,赵连吉、赵连祥、赵连如,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这二狗,仗着家境殷实,上头哥哥多,庄里大姑娘小媳妇没少受他欺负。招娣娘家是邻村,家里姊妹七个,她是老大。17岁嫁进陈家,陈家兄弟两个,老大早些年已经分家单过。男人陈继元小招娣两岁,打小体弱多病,大些时候除了读书地里活很少插手。
“宝贝儿,你男人都跑了多少年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跟俺好吧,保你不受罪。”
“我呸,就算天下男人死绝了也轮不到你。”招娣俯身摸起一块石头朝着二狗扔去。
“臭娘们,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回去守你的活寡吧。”
二狗赶着牛车慢吞吞消失在晨雾中。
招娣委屈的眼泪顺着俊俏的脸颊流下来,六年前的那一幕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打,打,给我照死里打!”
赵老四指使着大儿子赵连吉二儿子赵连祥朝着躺在地上的陈宏生一顿猛踢。陈宏生念过几年私塾,在庄里算是文化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过年写个对联啥的都请他去执笔。平时家里六亩地四分菜园大都是他和儿媳招娣侍弄着,偶尔老大和老大媳妇也过来帮帮忙。
年逾五旬的陈宏生哪是赵家两个如狼似虎大小伙子的对手,没几下就被打得抱着头满地滚。
“继元继元快去看看吧,你爹要被赵家人打死了”
好心邻居陈德来也是陈继元发小,不敢劝架只好给继元来报信。
陈继元扔掉手中的书从柴房冲出来,跑了两步又回头抄起一把锄头。
“走,快走,在哪?为啥事?”
“还不是因为嫩两家地界的事!”
陈德来和陈继元同岁也是同学,不过他念书比吃药还难,好歹头脑还算灵光,勉强学会写自己名字后就跟着他大哥在镇上给人家饭馆当伙计了。
陈德来大哥陈德才人老实,早年间也是跑堂的。几年下来,饭馆王掌柜看德才人厚道,长得又是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就给招了上门女婿。现在已经是掌勺师傅了。
今天饭馆空闲,德来回家看望爹娘。恰巧碰上赵老四因为地界的事殴打继元爹,这才紧忙回去报信。
赵老四堂兄八个,其中亲哥赵老二早些年参加过革命,还混了个不小的官。后来听说犯了错误被部队开除了。
吉人天相,回家务农的赵老二做梦也没想到当年被他救过命的上司当上了大官。人家为报恩把赵老二安排进镇政府吃国家饭了。
赵家祖坟冒青烟,多年后当年打杂的赵老二竟然混上了镇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时间赵家在这方圆几十里竟是无人敢惹,连保长都不放在眼里。
陈家和赵家地块紧挨着,起先界石两边各留30公分距离,走人过车都方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赵老四就把田埂一点点往界石那边做,直到原本60公分宽田间小路硬生生窄了一半。走路推车的人不敢压了赵老四家的田,结果把陈宏生家的田一小部分当成了路。
为这事陈宏生没少和赵老四交涉,赵老四是蛮不讲理并且是寸土不让。言称,自己家种地并没过界,你要是愿意也可以往这边种。
今天一大早陈宏生推着车子去地里上粪,刚到地头就气不打一处来。原来多年未动的界石竟然被人往自家这边挪了一拃,不用想就是赵老四干的。
“赵老四,你你太过分了!”
陈宏生红着脸,胸口剧烈起伏着,由于气愤说话都有些结巴。
“咋了,你老婆跟人跑了?”
赵老四仰脸望着陈宏生,撇着嘴,眼里全是嘲笑和不屑。
“你老婆才跟人跑了呢,我来问你,界石是不是你动的?”
“是我动的,怎么了,放你家地里了?”
“你去找保长啊。”
“你去告我啊。”
“怎的,你还想动手?好啊,你来打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