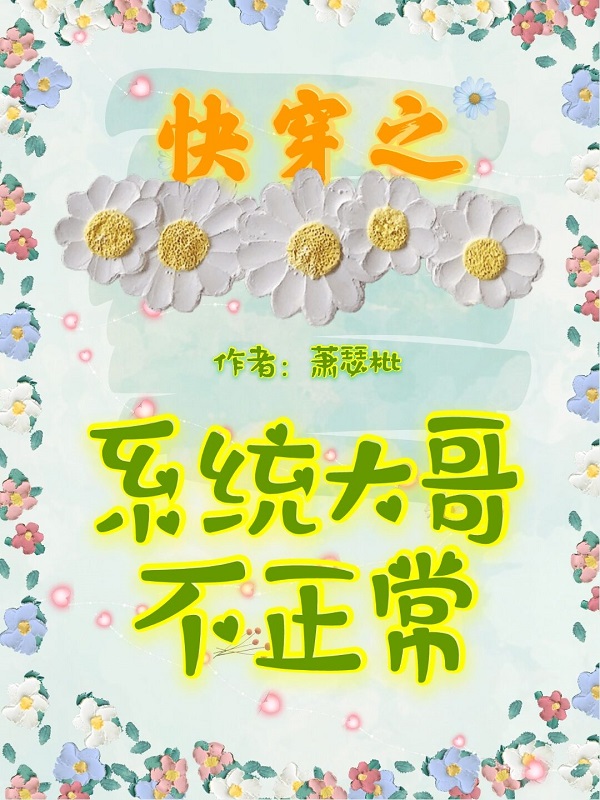转眼间又过去了十载。
都城不远处的郊外,两位神采飞扬的魁梧男子骑马并进,一位鬓发如霜,大抵刚逾知命之年,一位朝气昂扬,正值弱冠。
二人前来京郊,只为拜访一位多年未见的故人。
溪边的一栋竹楼上,一位身着素缟的妇人临栏眺望,看着卸甲归田的荆亩和接任大统领之衔的亭午朝自己挥手。
“娘亲!”亭午笑着冲上竹楼,与热泪盈眶的景臻相拥良久。
三人相聚,浅酌一杯,把酒言欢,全然忘怀过往的是非颠沛。
荆亩似是想起了什么,三言两语便支开了亭午,独与景臻共饮。
他见亭午走远,才低声开口道:“您当初曾与我说,郦兄为人凉薄,可那日实在情急我来不及与您细谈,但我深知,他绝非如此。”
“儿女情长、天伦之乐,他都不在意,只一心挂念着对北齐的恩义,这些我都看在眼中,也理解他。”
“可实际上,郦兄是因为知道夫人的身份,才不敢越界。”
“大人说什么?什么身份?”景臻心头突然一抽,声色却皆平静。
“您是北齐的公主,武成帝与一位宫娥所生。”
“大人说笑呢。”
“不,夫人自己原也是知道这些的吧?可过了这么些年,您怕是自己都快忘记自己是谁了。”荆亩放下手中饮净的白瓷酒杯,身体微微向前倾,目光咄咄地正视眼神涣散的景臻。
的确,这数十年的光阴,她自己都快忘记自己是谁了。
当年武成帝将她暗中寄养在一位忠诚的老臣家中,无名无份,如同庶人,豆蔻之年以婢女景臻的身份被迫嫁于老臣暴躁的瘸腿长子,不出两年便育有一子,而没过多久老臣之子却因故去世。
谁知后来北齐为北周所灭,太后与皇后穆氏遭流放,穆氏为复辟北齐,命令即将逃窜的老臣将带有北齐血脉的幼子交予她,谎称为先帝的遗腹子。
而景臻却为了陪在孩子身边,宁愿屈身为她二人所驱使,以此来照顾她自己的儿子,即是亭午。
“是啊,当真快要忘净了。如今想来,似是前尘往事,一片浑噩污浊罢了。所幸,我能遇见郦官人,是他让我明白人世间竟也有这般的良善美好,叫我明白自己原也可以一往情深。”她轻抬起一只有些烫手的紫砂壶,仔细地将茶倒进荆亩面前的瓷杯中,“不知大人,何以闻知这些?”
“皆是他传书告知我的,我与他本为同门,也是他唯一可以安心倾诉这些的人。”
是北湍被那老臣临危受命,一路暗中抵挡北周派来的杀手,护景臻一行宫人逃至一处县城直至她们在当地开起馥禧楼安顿下来。
是北湍与江湖兄弟买下馥禧楼附近的铁铺经营,以护她与亭午。
也是北湍为了让她少吃苦头,给她制作不伤皮肉的藤鞭,并不断传出流言逼得胡氏与穆氏主动放弃将他母子二人囚于楼中的念头,放心地将二人交给他看护。
他给她自由,给她尊严,给她新的人生。
“公主,”荆亩年迈的身体缓缓离座,恭敬地行礼道,“微臣必须唤您一声公主,却唯这一次了,您的身份,天下只能有我二人知晓。郦兄曾与我说,为了保全你们,这些事本该死死咽下去,只是我不忍看见您再误解过去郦兄的种种,误解了他对您的一片真心。”
真心?
窗外刮过一阵山间的清风,她却仿佛听成了一声耳语——“景臻姑娘也随了我。”这宛如一句来自前世的旧语,于她脑海中良久回荡。
她终于醒悟过来,那无数个共处一室却不曾圆房的夜晚里,忧虑与失望交错的矛盾内心,与那时那刻的他相比,是多么可笑。
他知道她是公主,知道她已非处子之身,却不敢揭出真相,只能选择冷漠相待,被迫压抑住自己与寻常人无异的狂热情感。
荆亩望见窗外远处扛着一大捆柴火向竹楼缓缓走近的亭午,不禁笑道:“您可知亭午一名的由来?”
郦兄曾说,亭午,原该是您的封号,是武成帝崩逝前拟定的,老臣知晓,便都告诉了郦兄。
而他搭上性命护住的,不只是一个亭午,
而是亭午母子二人。
她侧过脸,盯着悬挂于墙上的那只陈旧藤鞭,忆起过去被它抽打触及时那种柔软酥痒的感觉,仿佛是那位清秀温润的红袍男子,正用一只大手轻柔地抚摸慰藉着她。
一刹那,她呆滞的双眸中泛起一片晶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