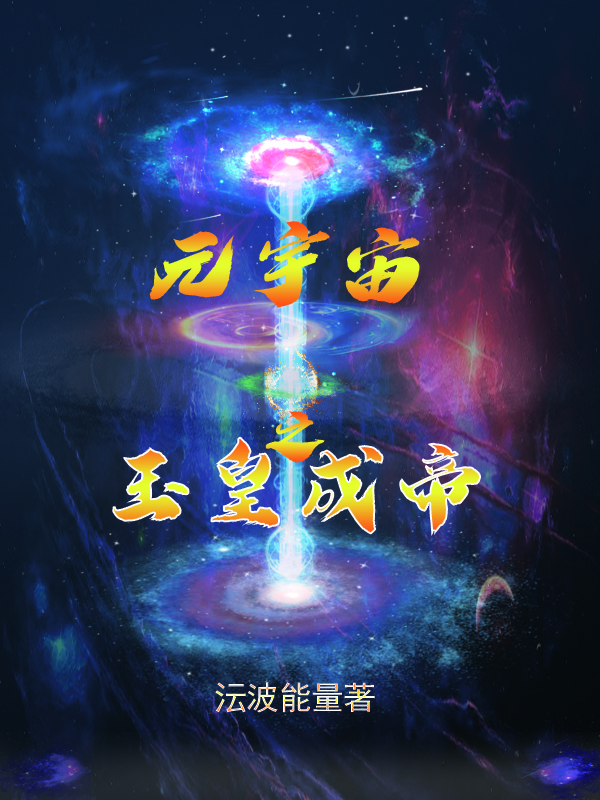天空才刚透出了淡淡的柠檬黄,鱼肚色的窗纱被清晨的风撩起,人群稀稀疏疏的声响传入房中。北海的初晨,永远以一种最为完美的方式开始。
而我,袁果仪,第一次在闹钟响起的半钟头前张开眼,并以一种最丑陋的面貌,亲吻了北海的空气。
走进洗手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双眼空洞无神、皮肤干枯发黄,想起高中时那圆润的面庞,相比之下,想想过去自己曾因胖而自卑还真是愚蠢。
余佳莉对我说过:“你现在和我一起去逛街越发能衬托我的年轻貌美了。”我白了她一眼,毕竟她从没带我逛过街,但想想看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确实和五十岁的女人差不了多少。
自从他去了深圳,一切都变淡了,生活成了一杯纯粹却无味的蒸馏水。
我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是不是偶然,因为生活变得太快,不觉之间便失去了很多很多值得珍惜的人和事。
回想起过去种种,我只觉得心口酸楚堵塞,却没有半点挽回他的冲动......
......
高一那年,我第一次离开了家。国中三年的挥霍,致使我毫无悬念地考进了一所郊区的高中,保姆孔姨带着我,住进了学校后门口一套租来的房子里,一年一万,价格适中。
那栋房屋总共是八层,农村人盖的,而我,则选择住在较高的六楼,毕竟爬楼梯消耗卡路里,对于这种颇有赘肉的姑娘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我爸每月都会抽空来这边看看我,辅导我功课,所以高一时的成绩起色很快。余佳莉说了,如果期末考试我能排在年级前五十,就立马给这整栋楼都连上wifi,当然,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总而言之,在高二之前,我的生活都行驶在正常的轨道上,直到他的到来,开始微妙地改变了这一切。
那是高二学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孔姨买完菜,拎着手里的大包小包、穿着厚重的绒靴子冲到我面前,认真地说:“果仪,听房东说,楼上被租出去了,而且......”
“先把鞋子脱了再说,我到时候是不会帮你拖地的。”我一脸嫌弃地看着她。
等她关上门,换好鞋,紧接着就冲进了厨房...没错,她向来这么健忘,不过对于七楼的出租,我没有半点兴趣,只要不是给精神病或是羊癫疯之类的人住,我是都能接受的。
当天晚上,我沉浸在万恶的数学海洋中,再次听到了底楼的房东奶奶用摇水井时“咿呀”作响的刺耳声音,虽然早已习惯,但依然不解底楼安装的那几个高级水龙头是房东买来做什么用的。孔姨说,省水电费是老一辈的通病,农村尤其严重。
这时,那原本要持续半个钟头的噪音停了下来,我索性放下笔,歇了一会儿,陌生的脚步声穿过墙壁入了我的房间,孔姨早上说的那位七楼的住户,已经来了。
终于明白什么叫暴风雨之前的彩虹,之后那一整个晚上,楼上传来连续不断的凄厉歌声,折磨得我翻来覆去、痛不欲生,在极度的困倦中,睡了俩小时。
早上,我顶着一头杂乱的卷毛、挂着一对青黑的眼圈、鼓着一肚满满的起床气,踹开房门,准备去七楼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冤家路窄,刚一出门就撞见了从楼上下来的那位“仇家”,正准备开始我口轻舌薄的理论,却被他抢了先:“...什么啊?六楼原来住了......”
“你丫的是精神病还是羊癫疯?!大半夜鬼哭狼嚎个毛线啊?!看你这样的就知道,你的智商绝对是和你的身高成正比!老娘见过得病的,没见过病得这么深入脑髓还不去治的!你住七楼呀?你哪绕梁三日不止的魔音干脆睡在顶楼平台才更加符合你的高档品味!”
我嘶吼着打断了他的话,那气势,犹如大江东去......
第一次发现秋天的气候也能转变得如此之快,爸爸告诉我,郊区的天气无论四季都是会偏凉些。
一年堆积下的短袖也到了清洗整理的时候,但最可怕的是,恰在这个时候,孔姨这位洗衣能手请了两天的病假,所以处理这些堆山的衣物,将近占据了我一整个美好的周日。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抱起一篮半干的衣服,晾晒它们绝对是一件体力活,我拼死拼活地完成了这项伟大工程,拭汗走进卧室小睡了一个来钟头。
稀疏的水滴声将我惊醒,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去阳台,却发现窗外依旧阳光明媚,但我千方百计洗干净的衣服们却被莫知来处的水滴不断“抚爱”着。我心塞,把头探到窗外往天上仰,看见了七楼的......
“真遗憾你没有智商,但弱智也一般不会把洗衣服和泡衣服弄混淆,自从上星期看见你以及你的智商,现在眼睛都在痛!”我一脸友善地告诫着那位七楼的男孩子。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的衣服都太厚了,实在是拧不干啊...”一副清脆却略带奶气的嗓音刺入我的耳膜,突如其来的“阿姨”俩字深深地刺痛了我...弱小的心灵。
“什么鬼?!谁是你阿姨,你见过我这么年轻的阿姨吗?要么叫我姐姐,要么抱着你的湿衣服滚回家读书去!”
“呀...原来是你呀...对上次的事我很抱歉...因为房东奶奶和我说六楼没人住(我此刻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向一楼)所以我才唱歌的,她大概记错了,”他浅笑,两个小梨涡瞬间点亮了他的整张脸。我愣住了,因为第一次有男生受了我两次毒舌猛攻还能毕恭毕敬好声好气的来道歉,所有的气一时间都咽了回去:“噢...嗯...知道了,没事。”我的初次谅解,献给了一个陌生正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