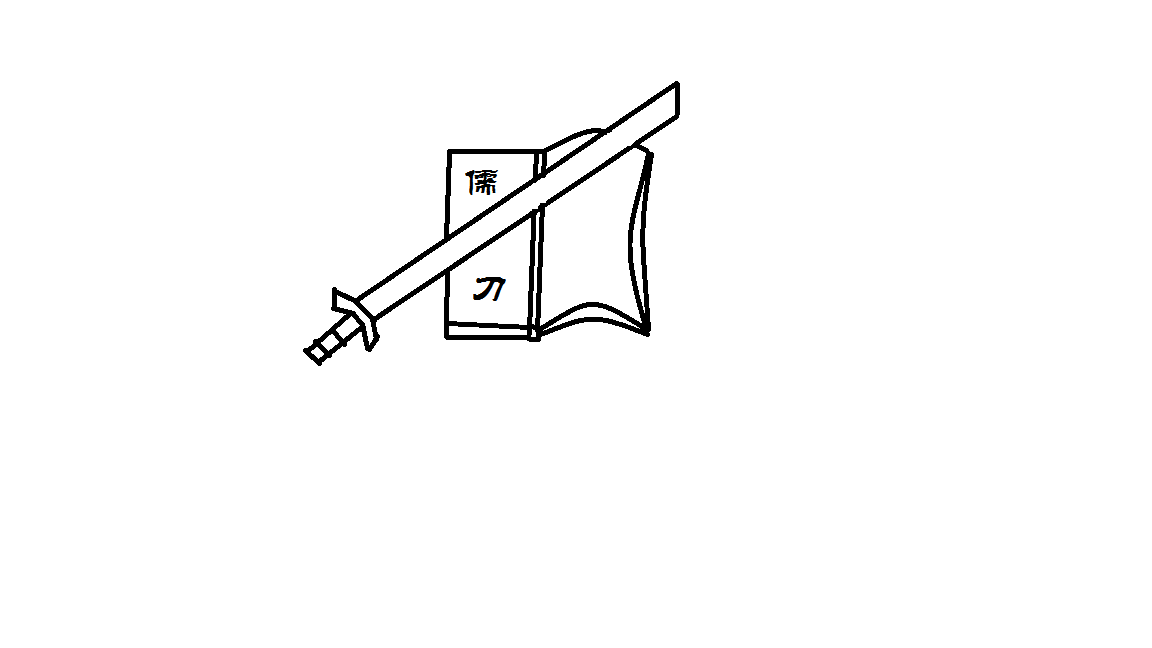数年后的一个深夜,已近子时,空旷的院落里不时回转着阴湿的冷风,稀疏低矮的榕树无力地随风摇晃不止,“簌簌”震动的枝叶声兑着挥劈砍刺的尖利响声一齐打破宁静,却在空气被夜风刮鸣呼啸时,被隐盖了大半。
景臻的卧房内依旧灯火通明,她正焦虑地朝窗外张望,耳边依稀传来刀剑厮磨的打斗声,每传来一声,景臻的心口便刺痛一分,焦虑忧思也更甚一分。
也不知这样煎熬了多久,打斗声渐渐淡了去,随即传出踏步砖瓦的清脆响动,步伐的节奏与重量,都是景臻所熟识的。
她连忙拉开房门,将门口斜倚木栅、浑身是血的郦北湍扶进房内。
“此番竟伤得这般重!”多年的经验教会她镇定冷静,可她内心却仍会不住地疼痛,只得深吸一口气好不让自己流出泪来。
“我没事,亭午的安全重要,放心吧,我的弟兄们都在守着他。”
她把北湍扶到座椅上,从角落里端来一盆热水。
“本庆幸这北周宇文氏一族终于被灭,怎想得到这隋朝的皇上也容不下亭午,都六年了,前前后后咱们搬了这么多地儿,这皇上还是不死心。派来的杀手也是愈发强劲了。”他粗重地呼吸着,以减缓景臻帮他清理伤口时的疼痛感。
“您原可以不用如此......”景臻哽咽,轻缓地擦拭着北湍的身子。
“北齐皇室曾对我有恩,即便我深知武成帝与后主的荒唐行径,但拼死护住高氏的血脉,不过也只是为报恩罢了,我本......”
“您本不求复辟北齐、更不求虚荣名利,只为安心。这些话您都对妾身说过无数遍了。”景臻柔声接上他的话,语气中带着一分轻微的责备,“无论如何,妾身到底都会支持您。”她随手撩开自己鬓角的杂发。
似是因心疼她此刻这般辛劳疲惫的模样,他蓦地紧握住她的手腕,将她拉到自己面前,用正经肃穆的眼神对上她忧虑无奈的目光,缓缓将脸向她凑去。他双目中的严肃渐渐淡释,她明眸里的哀伤也渐渐隐去,二人的呼吸声在彼此耳中愈发厚重起来,却在双唇即将碰触的一刻,他霎时止住,停顿了几刻。景臻目光不禁低垂下来,鼻腔推出一股长气儿,随即别过脸,端起被血染红的脸盆起身,走去换水。
她心中早已清楚,北湍对她并无感情。
从她知晓他伙同江湖兄弟刻意在馥禧楼周遭开间铁器铺,故意散布诛杀遗腹子的江湖谣言给穆二娘,为的都只是便于守护亭午的安全开始,她便明白,二人之间的一切都无非是由亭午在维系。
而她嫁于郦北湍后,二人更是从未同房,她不提,他也从未谈及,只是相伴彼此,相互扶持。
只是她全然愿意如此陪伴他左右,为他打理一切。相较于过去那般的“苦苦远眺”,如今共处一室的距离已然令她满足至深、不再奢求。
“再这么下去也确不是个法子,咱们是时候将亭午送去兵营了。”他叹气道。
“那兵营当真安全吗?”
“边境军有荆大统领关照着,安妥无疑。”
“明白了,那我即刻去筹备。”说完,景臻背过身去,深吸了一口气,眼眶刹那湿润了起来。
她走到柜前,整理起北湍和亭午的衣物,小心翼翼地翻出北湍常带着的刺绣香囊——是她初嫁来时亲手为他做的。趁他不注意,将压在酒坛下的一小卷黄纸抽出,悄悄塞进了香囊里......
荒郊野外的一道狭窄泥径上,一行人马匆匆前行,灯笼火炬的赤色光芒成为黎明前夕的荒野中最灼眼的亮点。
其中一辆马车的门帘被牢牢封住,里头透出微弱的光,将两幅不同年岁的女性身影勾勒投射了出来。
“这老妇都年近花甲了还这般风骚?当真是桩奇闻逸事!”
“可不是吗?这揽起客来那嘴皮子别提多利溜了,不愧是前朝太皇太后啊!”
“倒是那个穆黄花,还知道摆皇后架子呢,一天天地装病不出,真是娇贵。”
“哈哈哈你们可小声点儿吧!校尉不让咱瞎议论......”
“知道就好!都给我闭上嘴!”阵仗最前方的一位虬髯校尉用一副震天嗓门大吼一声,把这些个说闲话的小卒吓得一怔,纷纷低头不言。
校尉得意洋洋地大迈步子,背后绑着的那副形体巨大的龙纹砍刀一颠一颠,上任四年来,他终于盼来了去向皇上交差的日子。
他幻想着自己将来加官晋爵的画面,已然放空思绪,忽视了前方正等待着自己的一行人。
从这一行人中窜出了一个小士卒,冲至大胡子面前,跪地禀事:“禀校尉大人!北齐皇子已被捉拿,一众包庇人等也都在此处。另外,因这顽童太过狡诈,揭发者将其锁在此柜中,等大人过目。”
郦北湍也立在这人群里,与众人一样被铐上了刑具,他担忧地望了望拖车上的那只小木柜。
“好!极好!”校尉抚着虬髯放声大笑,随即指着面前一行人道。“说!你们谁是那位有远见的勇士?居然懂得迷途知返帮助陛下捉拿逃犯,不错!站出来,本官重重有赏!”
人群里冲出一个身型矮小的秃头弟兄,点头哈腰地对校尉说:“大人,是小的,是小的揭发的!”
校尉随手扔出一袋银子,秃头慌忙接住,道谢后,转身就往旁侧的灌木丛里走去,并用余光和人群里的郦北湍使了个眼色,不用一会儿功夫便消失无踪。
“把那俩娘们儿带下来!认认人。”
在一众士兵刀剑的环绕下,穆邪利搀着胡氏缓缓走下马车,二人皆哭得花容失色。
“不不不...这不是,这孩子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