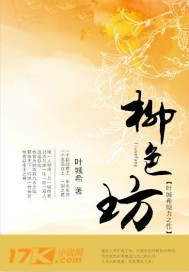热腾腾的烧饼出炉,老板直觉眼前有乱影晃过,紧接着,台上的烧饼就不见了三个。
“哎呀呀,饿死我了,这个可真香!”
老板目瞪口呆的看着不知何时出现的女子,粗布麻衣,头发松松垮垮的挽着,容貌还算俏丽,一双乌溜溜的眼闪耀着灵动的光。此时此刻她正捧着三张烧饼,一副馋出口水的模样。
“喂!你……”他刚刚激动的扬起手一声吼,肩膀便被一只修长的手按住。
“这些够了吗?”
几块布币放在了他手上,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呃……够了……”烙饼的大汉愣了愣神,一抬头与来人目光相遇,顿时他一个哆嗦,脚都不由自主往后退了一步。
这人眼神阴郁,阴沉沉的好生可怕!明明午后的日头照的街头巷尾都明晃晃的,却似怎么也照不到这个人这般,他整个人就如阳光下的一片阴影,浑身都散发着诡异森冷之感。
正这么想着,那人却如鬼魅一般,不声不响的放下布币,转身便与那姑娘走远了。
“这个人是什么来头?江湖脚商我也见过不少,这种邪门的人倒是从未见过。”饼家老板喃喃自语,“那姑娘倒是毫不避讳,真是叫人吃惊。”
几个常客过来招呼,待人散开,老板再向街上望去,那二人的身影已完全不见,仿佛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个梦。
“喏,你不吃?”走在乡间的林荫小路,祁央举起饼在他眼前挥了挥,“你不吃我可要全吃啦!”
“随你。”祁修瞟了她一眼,轻启薄唇吐出这两个字。
“你还真是几乎不吃东西啊!怎么扛得住的?”
“习惯了。”他轻描淡写的说着,忽而话锋一转,“你的工钱讨完了?”
“哎呀,你可别提了。”祁央叫嚷起来,“你不说我都忘了。瞧他们欧阳一家子小鸡肚肠的模样,亏得本姑娘大度,还答应大小姐把他情郎找回来……”
“情郎?”
“欧阳家最得意的匠人钟盛。我做工时和他交情挺好的,也见识了他不少铸兵之法。我离府后,听欧阳景儿说他就失踪了。你说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还就在我前脚走后,那家子人就全把矛头指向了我。我倒想找到那钟盛问问,他凭啥就这么害我啊?”
“钟盛么……”
“怎么,你有他的线索?”
“你就那么在意那个家伙吗?找到他有什么好处?”
“你果然知道些什么。”她心下似渐渐卷起波涛,但却好像并不是十分意外,“我只是奇怪,你怎么会和他扯上关系?”
他侧目,目光扫过她时有些复杂,有些锐利,说出口的话却是压抑着的,不似往常讥诮戏谑,而是难得温和平缓,“你又是如何和他有所牵扯的呢?”
她神色认真起来,知他心下怒火愈盛,面上反而愈发平静,语气也愈发温柔。和在曲沃塔上时不同,所以那时他不论如何阴沉可怕,她也没有胆怯之意。而今她却突然觉得有些不同寻常,心下愈来愈惊,甚至比那时雨夜还觉得更加发冷了。
“既然那欧阳小姐那么在意他的情郎,我何不卖给她一个人情呢?”她一挥衣袖,似想挥去那从他而来的不舒服的感觉,“至于他是死是活,自是由他,我管那些干嘛?不过是给欧阳小姐一个口信罢了。再说,你也不想这种污蔑我和他私逃在外的鬼话在市井里流传吧?”
“呵。”他短促一笑,“谁嘴巴不干净,我见一个杀一个。”
她被那话语中隐藏的狠厉惊了一下,却愈发有些奇怪,“看你也知我和那人不过是泛泛之交,那你究竟在恼我什么?”
“我并不是在恼你。”他终于叹口气,有些无奈的看着她,“我不过是在恼那个钟盛罢了。而有些时候,我甚至更恼我自己。”
“你……”她一愣,看他那悔恨交织的神情终于确认他说的不是假话,终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祁修,你是认真的吗?这真的是祁修,真的是那个神鬼不惧的‘邪教余孽’说出的话?”
笑了一阵,她瞥见他的神情,连忙板脸正色道,“我错了。”
“看到前面的中条山了吗?”他忽而仰头望向远方,祁央闻言也不由得抬头望去。
觧池就在中条山北麓,此时虽然天气甚好,山上却是风起云涌、云雾缭绕,仿若不可触及的仙境。
“你从外观之似已了然它的全貌,但其真实内在却藏在云雾之中。”他的语声淡淡传来,却如山中之风一般冷冽,“你口中所说的钟盛,当真是你所认识的钟盛吗?”
她神色一凛,似明白了什么,却又不似全然明白。
“你若想知道,我便告诉你。只是……眼下,你真的想听吗?”他忽而面色一沉,“如你听了,便是想从我这里逃开,你也休得想跨出觧池半步。”
“我不听了。”
“怎么,怕了?”
“便是你说自己是邪教教主,我也不怕的。”她忽而转头朝他正色道,“我知你做事自有自己的道理。这么多年了,也不要小瞧我在你身边的日子。马上要到觧池,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大煞风景的话,我宁可天地间只剩你我,再无世俗纷繁芜杂乱耳扰心。”
“邪教教主若是听了这话,估计得感动的流泪吧。”他的面上看不出喜怒,与她缓缓向中条山的方向走去。
…………
“怎么,还没有找到吗?”
曲沃伯府里,那个一直以来神情寡淡的男子依旧波澜不惊,仿若私逃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小女和养子。
“没……有。”几名下属声音有些抖,本以为曲沃伯会大发雷霆治他们的罪,这副样子实在让他们摸不着头绪,心底下更慌了。
“父君!你怎么还能沉得住气!”祁鳝又气又急的在大堂上走来走去,“小妹平时性子野就罢了,如今有婚约在身,竟跟个男的跑了,这叫我府的颜面何存啊!而且父君,那个祁修,他绝对是下了什么咒术……”
“住口!”曲沃伯忽而出口训斥,语声少见严厉,把祁鳝吓得一哆嗦。
“父君?”
“你是在说我被那小子下咒神智不清了吧?”他瞟了一眼想说的话都写在脸上的祁鳝,冲下属挥挥手,“你们先下去。”
“央儿这性子倒还真与我年少时颇有几分相似。”曲沃伯竟心平气和的讲起祁央来,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派出人去找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祁修那小子哪能有让他人找到的道理,否则,他也别是邪教……咳咳。他们以前出府那些事我都懒得管了,让央儿陪着他倒是一种牵制,要不然的话,就凭你,恐怕就要给我府捅出个天大的篓子来。”
“我?”祁鳝愤愤的一声疑问在堂上都有回音了,“我可是一直都为府里着想,何来捅篓子一说?”
“别以为你私下里与祁修动手的事我不知道。”曲沃伯叹了口气,“你三弟尚在襁褓,你作为大公子为府里着想我自然甚是欣慰。但我也警告过你私下不要与祁修闹事,我看祁修是顾及央儿才没真正伤到你,否则整个府上是何状况都难说。”
“父君。”祁鳝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究竟是怎么回事,您一直不告诉我为何收养那个小子,那小子分明就不是个善类,是我府的祸患,您缘何养虎为患?”
“鳝儿,在你看来,你父君是不是成天只醉心刀剑、歌酒与书画,是个不问政事的闲人是不是?”
“儿明白,父君是大隐之人。”祁封慌忙低头,“父君心中的大志,儿心里最清楚!”
“哦?”他的目光带了几分趣味,他知道自己这个儿子并不差,只是偶尔有些意气用事,毕竟年轻气盛。因此也未全告知他实情,“你清楚什么?”
“父君这是在以退为进……”祁鳝声音里充满兴奋,“是蓄势待发的弦,在待时而动!因为以父君的武功才略,绝不是屈居人下的泛泛之辈,因此才会遭人妒忌。毕竟,父君大德,在征讨天归邪教的事上可是立了大功的!是民心所向!”
“哼,你这小子,又怎知当年之事。”曲沃伯语似不满,却流露出笑意。
“所以……这个祁修,父王……”
“我不过是也想给晋侯提个醒。”曲沃伯端起茶杯轻轻摇晃,看着里面的茶色渐渐变浓,“当年派我去随王师征讨天归,未尝不是有人从中作梗,害我命险些丧于北漠。他想要我的命,我便要好好活着,让他想下手也得顾虑一下,究竟是不是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我要让他心中永远不得安宁。”
“父君是说当年征讨漠北戎狄乃是遭人陷害?!”祁鳝大惊,“我还以为是晋侯荣赐……”
“鳝儿,你把邪教想的太过简单了。”
“我是相信父君战神的名号,我……”
“我懂,你从未上过战场,又怎能知铁马金戈流血漂橹的惨烈。为父也少与你谈心,怕不是在你心里还是个大义凛然的英雄。如若不是这次晋侯许婚,诸多险恶,我不得不坦白一些事情于你,防你蒙于鼓中再入歧途。本我也不想让你惶惶度日或是心怀愤恨,也希望我一直在你心里是个英雄。”
“父君……在儿心中您永远都是!”
“不必多说了。想必聪慧如你,听完这些话也能猜透我为何不急于找寻央儿和祁修二人了。”
“伯让将军是晋侯许婚,定是晋侯心腹,说不定就是派来监视我府的。”祁鳝思索着,“小妹逃婚,父君不过是顺势而为。至于祁修……父君,难道祁修真是邪教之人?”
“你只知他是我府这边的人便好。”曲沃伯抚了抚胸口,似忆起什么旧事一般,心思重重。如果全部让祁鳝知道,以他的性子,定会无法接受徒生事端,“有他在,宫中还有潘父在,晋侯不会轻易对我府下手。”
“而有央儿在,祁修也不会对我府不利?”祁鳝眼珠一转,“父君高明!只不过……眼下情形,父君又如何向晋侯交代?”
“来人!”曲沃伯看了他一眼,突然高喝一声,“把柳如嫣带上来。”
“柳如嫣?”祁鳝愣愣看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子怯怯的走出来,缓缓向他们行了一礼。
“这便是伯让将军的心上人。”曲沃伯露出了一个暧昧的笑,“怎么样,容姿出色是吧?鳝儿,我吩咐她去你那里服侍,你可愿意?”
“这……这……”祁鳝一时反应不过来,“伯让将军心上人,儿愚钝,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嫣是我府的细作,曾伪装过乡野村姑救过伯让将军一命。她自己又被伯让将军救过数次,二人因此结缘,岂不美哉?”曲沃伯就像是一个看好戏的观众,“最近西北又有战事,想必他看到这一番场景,定会主动请缨,也定不会再念着央儿的婚事了。我想,晋侯那里他会解释清楚的。”
“以此要挟,伯让将军岂不会杀了我?”祁鳝喃喃自语,只觉得头上冒汗,禁不起拿出扇子摇了摇,“我本就武功落于他下……”
“也好借此机会督促你好好练武。生在乱世,更何况是,别想着总让我罩着你。”曲沃伯毫不在意,某些神态祁央简直是他的翻版,让祁鳝禁不住愣神,“有时我恨不得也将你赶出去学学央儿,她那疯性子,有时候比你更适合生存。”
“父君……”祁鳝惨兮兮的叫出声,他不过就是武功差那么一点点嘛,谁叫遇上的都是这群超出常理的高手,斜眼一看柳如嫣正神情恍惚的站在一边,看样子也是个麻烦人,禁不住一声哀叹,“老天可饶了我吧……我现在情愿刚才是一场梦。”
“我相信你的忠心。”曲沃伯悠悠道,捧起一本剑谱看了起来,“为父的大业少不了你。期待你的表现。”
“父君,您当真就这么放着小妹和祁修不管了?”祁鳝忍不住问,口气是满满的难以认同。
“若是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央儿早晚有一天会知难而退吧。”曲沃伯浅啜一口手中的茶,“不过他也不可能一下子都告诉她,毕竟,那人是那么在乎央儿。可央儿,绝不能和他真正在一起,那可是我曲沃伯府的公主。眼下……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儿明白了,儿定会早日助父王谋得大业,让小妹寻得良人。”祁鳝咬咬牙。
不错,权宜之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他祁修也不过是曲沃伯手下的一个棋子,终有一天……
他抬起头朝柳如嫣温柔一笑,“如嫣,春寒料峭,别站这里太久了。跟我走吧,我让人给你挑些好衣裳。”
多少年后,后人回顾这段曲沃代翼之争,都不由得想起唐风里的那首诗。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也许早在最初,结局便已然注定。
----
轰隆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中条山山顶似已雷雨交加。
“这里有还未变干的脚印。”祁央弯下腰拿树枝戳了戳地上的一串脚印,它清晰可见,慢慢延长向觧池的方向。
虽然山底依旧晴朗,空气和土壤却都十分湿润,地上的脚印应是在不久前留下的。
“是个女子。”祁修只瞟了一眼,便断定,“看来有人比我们先走了这条路。”
“可只有一人的踪迹。”她摇摇头,“你说,我们去到那里,她还会在吗?”
“此路并非官路,可谓人烟罕至。如此崎岖之路她竟一人前来,依我看……”
正说着,前方突然传来女子的尖叫声。
祁央面容一紧,刹那间已然直冲过去。祁修见她如此,叹了一声,终是不放心她,紧随其后。
待二人赶到后,地上一片斑驳的血迹,只剩下几缕破烂的衣服。
“是猛虎!”祁央望向道旁的密林深处。
“那女子怕是凶多吉少了。”祁修也随着望过去,“我们现在是在它的地盘上。”
她站在那呆立了一会儿,“还是没能赶得及。”
“你不会是想进去追那猛虎吧?”他拉住她后退几步,“如果有这种想法,我就把你捆起来。”
“你也知是凶多吉少,我怎不知,我还没自负到偏要去和猛兽斗。只不过,若是你没能捆住我呢?”她收回目光,眼神落在他身上,“如果我说不管是龙潭虎穴,我都要去闯闯看呢?”
“你若是真想看着我把这片地给毁了,也大可以试试。”他拇指抚了一下腰间的刀柄,“虽然拿些野兽开刃着实逊色许多,不过我也就不计较了。”
她微微一笑,任由他拉着远离那个地方,“这里临近中条山,猛兽多的是,你能砍的完?”
“谁说我要一个个砍了?别说野兽,就是荡平整个中条山,都有的是法子。”他看她突然低下头去,不由道,“可怜那个姑娘了?先氏惨死那么多人都没见你怎么样,如今怎突然心肠这般软?”
“我只是有些感慨罢了。”她摇摇头,“在江湖行走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看透许多事。这个未曾谋面的女子只有一个人,说不定她所念的人已经不在了。走这样的路去觧池,也多半不为求生,只为和那人黄泉相伴吧。越是想到这些,我就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她感觉到他目光深沉的凝视着自己,但她并没有看他,而是伸出双手轻轻握住他的手,“我要珍惜眼前的一切。倘若你的真心予我,刀山火海,我也必不相负。”
他的眸色一沉,看着她的眼也愈发深邃起来。
“即便我是个杀人如麻罪大恶极之人?是在他人眼中避如蛇蝎般的存在?”
“你是要说钟盛的事吗?”她喃喃道,“我知你从不欺骗我,不仅仅是不愿,而是你根本不屑于这样做。是你杀了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而轻笑一声,“你既已知道,又何必问我?”
“为何?”
“他接触你,不过是看中你内功深厚,想杀了你祭剑罢了。”他眸底似燃烧着熊熊烈火,“欧阳家所铸兵器虽然正气在外,却也不是没有阴邪之道。欧阳礼那家伙也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鬼事。钟盛站在顶点,谁又知道他最后追求了什么?”
“所以你杀了他,那时你与我相约原阳,我便离开了欧阳府,缘由竟是这个?”
“如若不是顾忌你与府中有些交情,还喜欢他家的刀剑,我倒想让欧阳府也尝尝第二个万家的滋味。”他极其轻蔑的笑了笑,“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如此极恶,怎可不留着为日后所用。”
“可你救了他家三子欧阳观……?”
“欧阳三子嘛……”他扯开一个极为阴森的笑,“我只不过让他回家了而已。”
“什么意思?”她心中一抖。
“他已没有阳息,不过是个行尸走肉罢了。”
“你对他的尸身施了术法?”
“若非如此,我又怎能得知钟盛那小子竟对你起了歹意。欧阳礼那老家伙也不是省事的主。”祁修慢慢抽出腰间的长刀,眯了眯眼,眸中深处却隐隐透着一抹血光,“杀他莫过于便宜了他,那日我将他怨魂封之于刀中,刀身因封印而碎裂,外形似一把废刀。如今因缘际会这把刀又被我挑之于手中,钟盛这种人,就这样永远和自己心心念念的兵器在一起,岂不是幸福快乐?”
“钟盛……在这把刀中?”
祁央脑海中闪过欧阳景儿焦急担忧的脸。尽管知他残忍,但实际听闻时她还是不由得从心底生成一股恶寒。
“钟盛为恶,自然要由我这种极恶之人来惩戒他。”他沉声道,目光没有一丝温度,“所以,即便我是这样的人,甚至是个超出人伦常理的怪物,你也会说出必不相负这样的话来吗?”
怪物?她一愣,忍不住抬头,一下子便陷入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那种神情她从未见过,是陌生的,仿佛她从未有真正认识过这个人一般。莫名的,心头竟涌上一股无法探知的茫然与无措,甚至是惶恐不安,如突然面临巨大的黑洞,无底的深渊。
“你……”口中竟一时语塞。
“不用说了。”他抽出手背过身去,“有你之前所言,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