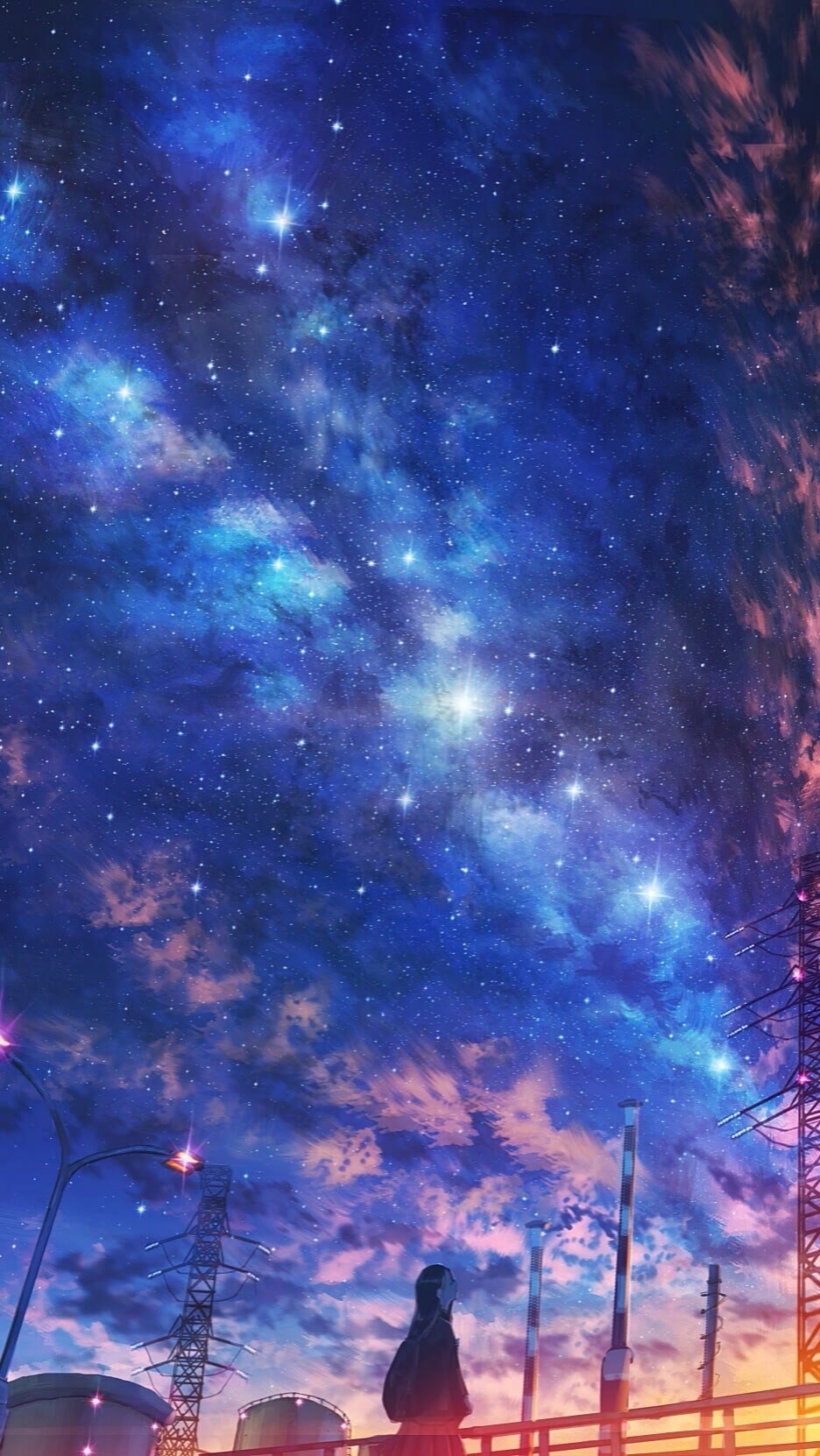“姑娘只是感染风寒,服下几味药,近日里多作休息便好。”
安邑驿站,祁央看着祁修颇为客气的恭送郎中出门,郎中面上挂着极为勉强的笑,分明是在畏惧这个似从黑夜里走出来的人。
即便他现在换了身粗布麻衣,头发也简单束于脑后,可那阴郁的眼,充满危险的目光,似讥非讥的唇,还有浑身散发的生人勿进的气场,都让人觉得十分不友好。
本来他也不是个善类,祁央闭目养神,回想起刚刚相识没多久就见过他的狠戾与狂暴,父亲似乎利用他这点暗中灭了一个仇家。不过那都是暗夜里发生的事了,她也只是听说。
“听见郎中的话吗,乖乖呆在这儿,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我出去给你买。”他回身一手撑住门框,高大的身子堵住整个出口,颇有些警告的意思。
“你什么时候认为能关住我了?”她慢悠悠的瞟了他一眼,“我又不是大病不起,让病人吹吹风才有利于好转吧。”
“你若不想在驿站住十天半个月,花光我身上所有的布币,就乖乖养病。”他蹙了蹙眉,许是顾及她的身体,还算心平气和的和她说话。
她心中一动,声音也柔软下来,“我什么也不想吃不想要,我讨厌一个人呆着,你陪我好不好?”
他一愣,神色颇有些不自然起来,别过头轻咳一声,“你是故意的吗?”
“虽然城中没半点关于抓捕我们的消息,不过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她自顾自说着,却忍不住偷乐,“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吧,我没有那么娇弱。”
闻言他转过头深深看了她一眼,眼中混杂了一些她看不懂的情绪,还未待她细想那是什么,他便抬高嗓门高喊一声,“伙计!”
驿站立马有人应了,气喘吁吁跑上来。
“你拿这些布币,去街上买几张当地的葱饼回来。如果碰到有卖好扇面的,也带回来一个。”他思忖着,“再备些小菜和粥,病人要吃的。看你最后办的如何,工钱我会另外再多赏你。”
伙计刚想说什么,遇上他的眼神,立马把话憋了回去,应了一声赶紧跑了。
“你不怕他一去不回?”她怔了一瞬,很快强装淡定的望向他,“你还真要陪我?哎呀呀,真是难得……”
亏他还知她想吃当地的葱饼,安邑的字画也非常有名,因此扇面也颇具特色,她曾提过一回,不曾想他还记得。
估计再往下想下去她就要再次发热了。晕乎乎的沉到被子里,听他不屑一顾的嗓音响起,“一去不回?量他也没那样的本事。信不信到时我把驿站拆了。”
“信,你说诛他九族我都信。”她哈哈笑着,在被窝里一滚,“我知道修公子最记仇了,全天下人谁得罪修公子谁倒霉……哎呀!”
他不知何时到了床边,压身下来,她吓了一跳,不通气的鼻子都瞬间好了。
“知道的话就好。”他捉弄般的在她耳边低语,“那你可要小心了,别让我记仇。”
“修公子真狡猾,专门欺负病中的弱女子,也不怕被人笑话。”她侧头躲闪着,用手使劲把他推开,看他直起身,坐在旁边眼中满是笑意,有那么一瞬,她觉得那样的神情是少有见的温柔的,意识到这点,她不由得看呆了。
在客栈休息了三日后,祁央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早上神清气爽的醒来,见祁修还在近处的桌上打瞌睡。她有些愧疚,也许是自己的一席话留住了他,自己又害羞又玩闹般的不让他近身,三日来,他便一直在那里休息了。
其实她知道他是修习过禁术的,如说那禁术对身体究竟有何影响,怕是无法想象。如果这副一直以来她所依傍的身躯倒下了,她不知自己会什么样。
思及此,她慢慢起身,刚想叫他,却见那双眼突然睁开,迷离一瞬便复清醒。
“醒了?”他起身坐到她旁边,“身子可有好些?”
“好多了。”她忽然一把拉他凑近,“瞧瞧你都有黑眼圈了,要是被谁看见还以为是本姑娘在虐待你呢,快来休息一下吧。”
“可不就是虐待。”他顺从的被她拉近,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是谁说要我陪着还不让睡在床上的?怎么,现在起怜悯之心啦?”
她忽的放开他,轻轻一推让他倒在床上,自己一个旋身便披好外袍,盈盈笑着站在那里。
“看你这几天照顾本姑娘确是尽心尽力,本姑娘准你好好在床上休息一下啦。”说罢,她便一下子拉开房门,料峭的风灌入,她深吸一口气,顿觉骨子里的不安分又蠢蠢欲动了。
他一反常态也不恼,反而撑手支起半边身子,悠悠道,“想去觧池吗?”
她一顿,偏头看向他,沉默了半晌,忽而笑道,“好啊。”
他定定望了她一会儿,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而是缓缓起身步至她身后,伸手环住了她。
中条山北麓的觧池相传是涿鹿之战后蚩尤喷涌而出的鲜血遇南风而成,池中含有闻名天下的“大夏之盐”,令安邑也变得富庶。晋国众多大夫也因近盐多居于此地。
明明是无法沉水的盐之湖,却有一个讳莫如深的传说。相传上古有一对身份悬殊的爱侣,因无法携手相伴而于觧池沉石共赴黄泉,以求蚩尤之邪祟之力重生。三年前他与她路过觧池附近的村落,有感于此,可惜那时冰雪封路,并未成行。
而今早春三月,万物生苏,想必池边也是柳吐新芽,草色初青了。
要在往常,她恐怕会调笑,你是要和我共赴黄泉吗。可不知怎的,她不由自主就说出了好那样的话,就仿佛这个答案已是不容置喙的。
二人步出驿站,天上红日正当头,城里人来人往,竟与曲沃也不相上下。
安邑乃夏之旧都,昔日夏后启经甘之战平定有扈之乱后,阳城被毁,因此王都迁到了安邑。如今这里则是晋之属地。
“夏后启如果知道当年的都城安邑如今是这般光景,会作何感想?”祁央环顾四周,有些唏嘘,“可惜'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士师高阳氏皋陶先禹而死,主虞的伯益又佐政帝禹日浅,天下未洽不能服众。据传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启遂即天子之位,开钧台之享,废禅让改世袭。如若天下都如尧舜禹般谦让贤明,这世上可还有改朝换代之说?”
“世人皆传'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祁修目中暗沉,透着凉意,“你所了解的,不过是胜利者、当权者想要让你看到的罢了。我倒知晓另有一种说法:启党杀益而夺之天下,以承禹祀。”
祁央一愣,“此话当真?”
“你可知禹之父鲧?”
“崇伯鲧?治水不力而被帝尧流放至东方海滨的羽山?”祁央眼珠一转,“我记得《三坟五典》有载,帝尧叹,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共咨,有能使治者?佥曰鲧可。难不成你说他是遭人陷害?”
“禹之父崇伯鲧极力反对以天下让舜,与尧帝之子丹朱、舜争天下共主之位,欲以为乱,因而尧令祝融诛其于羽山。”
“你是在编故事骗我吧!”祁央笑道,却见他神情阴郁,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
“就算是贤明如舜帝,苗人尚不臣服。而他便命禹伐苗,誓曰苗人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所以要'天降之咎'。可过了三旬苗人依不臣服。这时他又讲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遂施以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苗人终于臣服了。如果说以武力是天降之咎,缘何失败?以文德感化,岂不前后矛盾?文德之舞便让苗心悦诚服,岂不令人难以置信?”
祁央瞪大眼睛,一副分外吃惊的表情。
“再说帝禹,又何尝不是于会稽朝会之上,斩了迟到的防风之君以树立威望。涂山会盟,执玉帛者万国,迫于军威而臣服的又有多少?”祁修语气中带了丝兴味,“启帝启钓台之会时,有扈氏不服而未出席,启伐之,称要以行其教、行天之罚。甘誓所列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初始未能得胜,还称'吾地不浅,吾民不寡',自己是'德薄而教不善'。最后'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天下咸朝',把帝舜伐苗的故事又重新上演了一遍。然而在这斗争过程中,王都阳城都被毁了,不得已才迁都安邑。真可谓大贤大德!”
“怎么,这倒是像你亲历一样,你能断定史上所载便是粉饰?”祁央不由得有些好奇,“难道夏桀、商纣亡国也另有说法啦?”
“真正的真相,只有死人最清楚。”祁修笑的有些阴森。
“不说了不说了,我可不想身首异处。难得这么好的天气,安邑自然是逛够了再走。”她轻轻一踮脚,一溜烟便跑到小摊小贩边上,“我记得欧阳家的府邸就在不远处,也好久没去他们家做客了,说不定还可以管他们家借几件兵器呢。”
“那个欧阳老头我可不想再见到了。”他看似在她身后慢慢走着,却一点也不逊色于她脚底如风的跑来跑去,没落下她半步。
“那怎么行,没有你,别说兵器,估计让他吐出根骨头来给我,都难过的要死。”她停住转身叫嚷起来,“你不是救过他们家三子欧阳观嘛?”
“救?”他仿佛想起了什么久远的回忆,“我何时救过他?”
“天啊,这你都忘干净了。以后可怎么行走江湖。”她绕着他转了一圈,不满的瞪着他道,“我听说走镖的万家被灭门的时候,他不正在调戏万家小姐嘛,不是你路过把他捞出来扛回欧阳府的?”
他歪头眯眼似回想了一下,“啊,是那个时候啊。”
“你想起来了?”她立即神采飞扬起来,“那赶紧走吧!我还在他们家做过几个月的工,工钱还没给我呢!”
二人拐进一个没有人烟的小巷。
“其实我并不是路过。”他如耳语般的声音突然飘来,仿佛在谈论天气一般,“万家就是我杀的。”
她陡然瞪大眼睛望着他,“怎么回事?”
“自然是有来有往了。”他轻飘飘一句,全然看不出几十口人命丧生于他手下,“你和我不同,我出身邪教,难免会有仇家。若不是早在几年前中原清理的差不多干净,我们这次在外也不可能太平。”
“难怪前几年有传言说邪教再出江湖。”她的关注点却在别的上面,“原来是你!难怪那几年在外面玩总会有人刺杀我们!亏我还以为偷学功夫的事情败露了呢!”
“这双手。”他挨近她身边,“你亲眼目睹过它们沾满血的样子,我诧异你对此不置一词。你,当真不在乎吗?”
一些画面陡然闪过脑海,每每想起都仿佛是噩梦,她定了定神,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向前走去。
他看着她的背影,没有跟上去。只是面色渐渐阴沉下来,周身的空气都骤然变冷,他微微闭目,抑制住那样难以平复的情绪。是怨愤,失落,抑或是不甘?
他无法说出口的那些事,如若让她知道了,又会如何呢?
“修,我的这双手,又干净到哪里去?”她忽而扬声道,微微偏了头颇为傲然的瞥了他一眼,“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他一怔,良久轻笑一声,似是在嘲笑自己一般,心中的诸多思绪竟在一瞬间烟消云散。
“这个时候,身为姑娘家,不都应该劝人改邪归正的么?”他微勾了唇角,黑不见底的双眸却似藏了一抹异样的光辉。
“你难道不知道做好人和恶人一样不易吗,你既然选择做恶人,就得一做到底,否则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那回眸的一笑,一时间竟带了种说不出的蛊惑。眼见他眼中笑意加深,她急忙脚下如风远远跑到前面。
“你又想做什么了吧?我绝不让你得逞,哼!”
“你又想跑到哪里去?”他的笑里是满满的得意,“你以为闯入我这一生后,我还会让你从我身边逃走吗?”
“想要留住谁,各凭本事吧!”
她一溜烟儿的跑没了影,只留下脆生生的一句话在巷子里回荡。
“本事嘛……”他不紧不慢迈开步子,“那我们便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