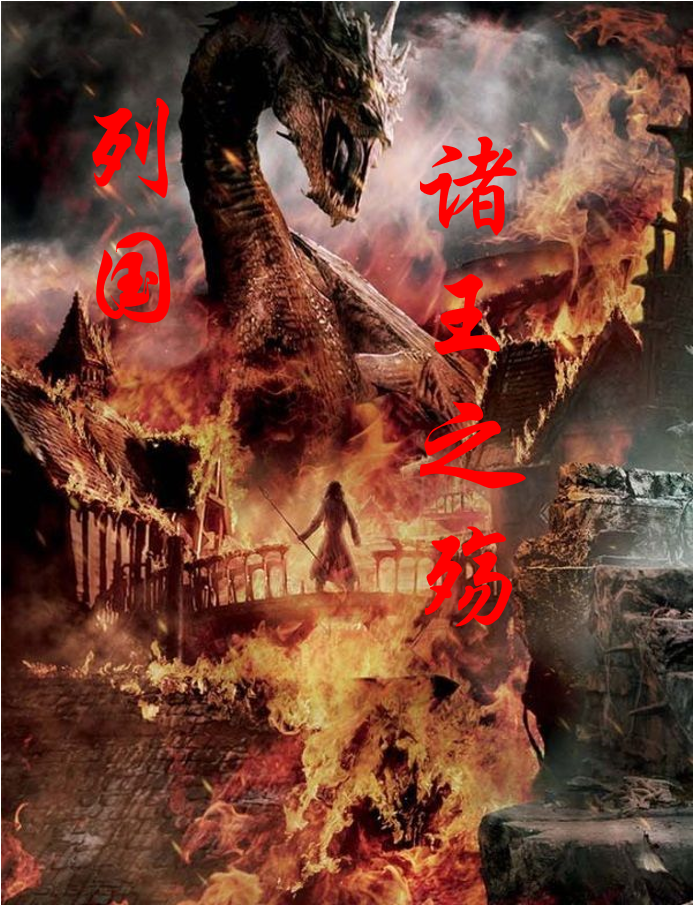这个暗道,其实边小禾也是第一次用,娘亲指给她看的时候,她惊异的,问怎么会有这么个所在,娘亲脸色分外脸看,到现在她还记得,似悲痛又似衔恨。
所以这暗道到底通向哪里,她也并不清楚。一路上领着众人弯弯折折,最后顺利到了出口,那青崖当人不让地上前去推开了盖子。当然这是个精细活,首先你不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地方,万一转了这大半天,却只是兜了一个圈子,还在自家附近,一涌而出岂不被寻仇的和尚们抓个正着么。再者说,上面有人没人,没人也便罢了,要是有人,你又知道是什么人,这样冒撞的出去,岂不吓着人家。吓着了也无大关碍,怕就怕这人叫起来,走露了消息,他们依旧是白逃了这一遭。
边小禾自然在那青崖推盖子之前好生交待了一番,其实那青崖本就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些关节不用她特意交待也明白的很。当下他小心地把盖子推开一道小缝,倒并没有想像中的尘土飞扬,只看到一双鸭蛋青色缎的秀鞋,其上暗红锦纹,鞋面曲秀白梅,艳丽不可方物。
那青崖哪敢造次,小心地把盖子放下,悄悄地对下面几人道:“好像,出口正设在一个大户人家小姐的闺房里。”
这话听在旁人耳里还好,唯独入了边小禾的耳朵,就觉得一阵刺心,她才明白当年娘亲为何是那番表情,原来这个暗道,竟是爹专用来与女人私会的。
下面四人正在做难,就听急切的脚步声在头上响起,跑马一般,紧接着“嗵”地一声,似乎有人跪了下去,正跪在出口盖子正上方,听一个细细的女子声道:“夫人,小姐因奴婢失手打破了一个杯子,便要杀了奴婢,求夫人救救奴婢!”
“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做事为什么还像从前跟我一样的不经心?”这位夫人的口气极为漫不经心,“她要打死了你,我也是没有法子!”
几人都听得云里雾里,只有边小禾脸色更难看了些,这两个声音她都太熟悉了,辛欣曾给她引见过,这位夫人,正是辛老太爷的第十房姬妾,闺名唤做珍珍,而这个丫头,是长随在辛欣身边的绡凤。
她心里正胡思乱想,不知道爹曾与这位珍珍夫人是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心里一阵恨,又听绡凤哭叫道:“夫人,看在绡凤曾伺候您一场的份上,您救救奴婢吧!”
“咱们的主仆情份早尽了,”珍珍夫人声音里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感情,平静如一谭死水,“当初你勾引老爷那会子,趾高气扬,心里眼里又哪有我这夫人,这时候你倒来求我,与其求我,何不去求求老爷!”
绡凤哭得简直惊天动地:“夫人,你明知道老爷是最怕小姐的,别说小姐叫我死,就算小姐把整个辛家的人都杀了,他也是不敢吱声的!”
“老爷的话不管用,我的话又怎么管用?”
“您怎么一样,在小姐心里,只有您是肯往心上放一放的,她一直把您当亲娘!”
这话才落,地板上突地“哐啷啷”一阵响,似乎是珍珍夫人把桌上瓷杯狠掷在地上,听她恨声道:“你别跟我提这事儿,你不提也便罢了,提起来我就恨——若非是我长了与她娘亲如此相像的一张脸,又怎会被她强逼着嫁给了她爹!”
“夫人,若非小姐在您那样穷苦的时候拉了您一把,您又如何享得这样的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哈哈……你别在这里拿话挤对我,我才不稀罕这荣华富贵,有本事叫老爷子休了我!”
这正闹着,门蓦地被人踹开,就听一个尖厉的女声气势汹汹地质问珍珍夫人道:“你刚才说什么,现在再给我说一遍!”
边小禾已然听出这是辛欣。
半晌无人言语,只有粗重的呼吸,另一个小丫头的声音响起来,是辛欣的另一个贴身丫头,名雪勺的。
“小姐做什么生这样大气,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值得了——小姐您快坐,喝口参茶润润喉,消消气!”
辛欣却还不肯罢休,一掌把桌子拍地山响:“珍夫人,你倒是把当才那一番话,再说一遍来叫我听听,也好教辛欣明白明白,当初是做了一件怎么样的大恶事,强抢民女还是逼良为娼!”
“小姐,刚才珍夫人说……”绡凤刚要插嘴,却不知被哪个赏了一计耳朵,辛欣喝她闭嘴,向珍珍夫人道,“你把刚才的话,一字一字,从头至尾,给我细细地再讲一遍,少一个字儿,我就要你好看!”
地板上又是“扑嗵”一声,想是珍珍夫人跪了下去,听她哀哀哭道:“我也不想活了,你索性一并杀了我,嫁了不想嫁的人,恨了一辈子,我早活得够了,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你那些个事儿,当我不知道么,别叫我说出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辛欣疾言厉色,语调极尖厉地,“你忘了当年那个给我做西席的穷秀才了么,难不成你就想嫁给他,可惜他对你并不看重,在与你要好的时候,不是又娶了那个鱼桑楼的名妓,叫什么婉娘的。索性他七年前便死了,死得好,死得真好呀!”
“你既知道这事儿,又怎么,又怎么同她女儿那样要好?”
“这也是你管得的!”辛欣对珍珍夫人大吼一声,似乎气得不轻,就听一旁的雪勺劝道,“小姐,快消消气,家里这些人,一个一个全这样的叫人不省心,没一个会办事的人,您要是被她们气倒了,这个家可要怎么办呢!”
暗道里,边小锋终是听出了端倪,一拉边小禾的手,把她拽到一边悄声道:“姐,上面的是辛欣姐吧,她们嘴里说得那个穷秀才,是不是爹?”
边小禾心里针扎的疼,看着边小锋隐在暗处,哀怨分明的一张脸,不知如何作答。边小锋把她的手抓得更紧了,她的表情已然告诉了他答案,可他不愿相信不肯相信,要听她亲口说出来,或者写出来,更希望她能够矢口否认。他急切地问:“你说,到底是不是,是不是,爹?”
边小禾咬一咬牙,拿过他的手摊开,在其上轻划。边小锋的心一抖,感到掌心里错络的笔化,分明组成一个“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