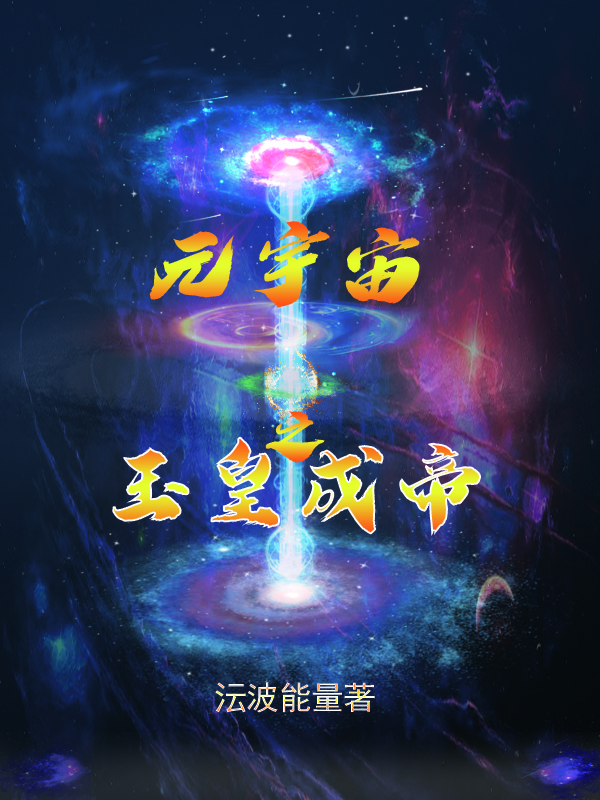来人并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开枪射击,我一把拽出爪刀,就地一滚靠到墙角边,劈手将爪刀冲进来那人甩了出去。
爪刀这东西是不适合当飞刀来用的,一般情况下也就是砸人而已。那人完全反应不过来,被爪刀狠狠砸到了胳膊上,枪口一歪,将躺在地上**的怒打的一个弹跳。更多的血流了出来,淌到我的脚边。
我重重踩到那一滩血液中,身子弹射开来,在那人调整好枪口之前,定光剑划过了他的脖子,鲜血喷射出来,溅了我一脸。
我没有多看他,甩了下剑上其实并不存在的鲜血冲了出去,刚出门又转头回来,将那家伙手里的枪捡起来。外面还不知有多少人,我一人一剑恐怕不好混。
熟悉的感觉从手上传来,我不用看到那块颜色奇怪的金属也能知道手上的是什么枪。这时候门外的声音已经非常杂乱了,我隐在门边,快速探头看了一眼。一片子弹扑面而来,虽然准头差了点,但是声势还是非常吓人的。我快速撤进房门,避开可能的跳弹,待一波射击停止之后才开始还击。
外面是一条笔直地通道,除了那些锁着的门框之外,根本就无处躲藏,所以这帮人对我来说就像个靶子一样。虽然肿胀的眼睛有些影响视线,但我还是轻松地将他们干掉了。
沿着这条通道跑到头然后左转,我努力回忆着脑中的记忆,数着脚下的缩涨缝和台阶,这条路是通往那个所谓圣殿的地方。我记得那地方对面的小房间就通往我从外面进来的路。但是之前的路我实在是记不得了,只能到时再想办法。
沿途比较顺利,这里可能并没有多少人,也没有像样的警报系统,几个零星赶来的光着膀子的疫人也被我顺手干掉了。
我已经冲到了那个破烂而且寒冷的圣殿门口,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我顺手抛下它,快速向前跑。突然,眼前横担出一条粗壮的胳膊,肯定是身上的伤让我的反应变慢了,定光剑出了一半脸就撞了上去,整个身子腾空重重摔倒在地上。
这一下摔得极重,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这一下从我体内摔了出去。
之前我来的时候给我开门的光头人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杠杆朝我的头部狠狠打来。我见这一击来势凶猛,没敢用剑硬格,一下子翻到旁边,杠杆头在我眼前狠狠凿到地上,溅起的水泥碎块砸的我脸生疼。
我浑身的关节都使不上力气,明明知道自己再不起来很难躲过接下来的一击,但却不能移动,只好伸手抓住那根杠杆,随着那根被抽走的杠杆用力站了起来。
那光头壮汉显然没有想到我有这么一招,用力晃动杠杆想把它从我手中抢过来,我没有撒手,用尽了全身力量抓紧那根杠杆。
其实我现在的状态就算是真的把那杠杆抢过来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那光头只要撒手过来,大约空手就能把我搞定。但他的脑子显然不是很灵光,只是大声咒骂着朝回夺那根杠杆。
我知道自己一撒手就死定了,也不敢撒手,两人就像拔河一样僵持不下。但是我心里清楚,跟这个壮汉相比,我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多了不说,再有两秒我就得松手。
跟我估计的差不多,那光头壮汉大吼一声发力一拽。我虽然还是抓紧了杠杆,但被这一拽脚下失根,竟然被硬生生拽了过去。再看那光头,已经狞笑着伸出手上的匕首在等着我了。
形势不妙,我急中生智,腾出一只手来抓住挂在手腕上的定光剑,剑尖冲前,借着他的力量冲了上去。
那光头十分托大,狞笑着拿匕首来格,但这等凡铁怎能敌得过定光剑?只听叮的一声轻响,定光剑擦过那柄匕首,撩开了那壮汉的胸膛,心脏如同气泡般破开,冒着热气的血泼在了地上。
我扶着墙,快速喘息着。这一番打斗对我的体力消耗极大,脑中不禁有一种极度眩晕的感觉。
但是我心里清楚,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虽说这一路走来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但是这里毕竟是这个疫人组织的重地,怎么可能就这么几个人几条枪?眼前这种情况,无非就是情况太突然有点反应不过来罢了。
我看清楚进入圣殿的那个小门方向,朝我的来路走去。这一段路是我不熟悉的,而且非常的错综复杂。当时行走其中可能不觉得什么,但是各个岔口却都像是为了混淆我的记忆而设计的一般。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很多脚步声,我知道追兵终于赶到。看了看地下鲜血淋漓的脚印,我赶忙脱下鞋子在手里提着,赤脚往回返,推开那扇通往圣殿的小门,躲了进去。
几乎是刚刚掩上门,门外就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我趴在门上,极力压制着自己的喘息,估计着外面的人究竟有多少。
至少有二十个人在通道里,我听到他们停了一下,低声讨论了几句什么,又朝着我走的方向跑了过去。
我暗暗松了口气,心中十分后悔刚才冲出来的时候没有从那些被我打死的人手里弄把枪出来,就凭这手中的一把剑,想要冲出去跟扯淡差不多。
正琢磨着,后腰突然被一个硬物给顶住了,我全身一紧,接着就陷入了一片凸凹有致的温暖之中,一只柔软的手从我肿胀不堪的掌背上拂过,坚定地将定光剑握入手中。
我没敢反抗,任由她将定光剑拿了过去,轻声问道,“是谁?”
“是我!”回答的声音非常轻柔,口吻像是每天都要见面的人敲门时的回答,而且这个声音却货真价实地让我感到非常熟悉,就像是昨天刚刚听到过的一般。
“你是谁?”我声音稍微大了点,心中盘算着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你忘记了?神使大人?”那个声音哼笑着向后退去,顶在我后腰上的硬物也离开了。
我微微张开双手,慢慢转过身来,眼前站着一个高个子女人,一头长发仿佛未经过梳理一般随意披散在身上,一袭白色长袍加身,左手提着我的定光剑,右手一支手枪从宽大的袖口露出来,还在指着我。
“喜?”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但是她的声音却和喜长老对不上号。
“不光是喜,助理大人。”喜长老躲在头发下面轻笑。
“你是……田甜?”这句助理大人引起了我的回忆,我不无惊骇地说。
“不错,就是我!”
“你怎么会……”我震惊了,谁能想到那个我都不认识的下属的下属,一个我认定年轻有为的得力助手,竟然是这疫人地下组织的四长老之一!
“你们那个苦长老呢?”我迅速冷静下来,眼前的情况不是现在的我能够解决的,多一个少一个并无甚区别,但是我却不想再不知不觉的被人算计了。
“他?他不愿跟我们一起,早就变成冰雕了!”田甜笑了笑,“您不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想说的话你就说了,还用得着我问?”我看她没有开枪也没有示警,知道她暂时没有对付我的想法,索性也光棍一点,增加些自己的筹码。
喜却不说话,笑了起来。
“笑什么?”我最讨厌有人跟我装高深莫测,可是每个跟我说话的人都喜欢来这一套,这让我非常烦躁。
“我笑了很多东西,您想知道哪一样?”田甜用手中的枪把长的有些渗人的头发拨到肩后。
我突然有些恶搞的想法,开口问道:“我记得你头发没这么长,是假发?”
田甜一愣,估计没有想到我会问她这个,但很快又笑道:“不错,作为长老,总得有点造型吧!”
这姑娘倒是坦诚。
“这造型还成,就是有点难看。”我随口评论了一句,“当时你能找到我,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些理由吧?”
“当然不是,以我手下的情报网,那还用得着猜?”甜甜笑着说, “您不会因为这个感到失望吧?”
“我是感到失望!”我答道,“本来你能跟着我做一些好事,没想到你本来就是个祸害!”
田甜丝毫不见气恼,“是不是祸害不是您说了就算的,城里的祸害到处都是,哪一个都比我要可恶一些。”
“是吗?”我紧紧盯着她,“组织这个组织想把全城都陷入水火之中,为了达到目标杀害了常诚还嫁祸于我,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但是这些事从哪里看都不是个人能干出来的。恕还算是为了拯救疫人而做事,我觉得你要比他可恶一些。”
“常诚是我杀的,我没想到你竟然能猜出来……”
我听她承认了,难耐心中怒火,哼了一声,“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自然不是傻子。”
田甜没有接我的话,径自说下去,“恕?你觉得恕能比我好多少,你别以为他是个宗教狂认定了你是神使说的话就全是真的,这所有的计划,本来就是他想出来的!”
是他?我心中一惊,感到眼前的真真假假完全不能看透,恕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用哪种匪夷所思的手法想给我争取一个机会,若说他是整个阴谋的主谋,说什么我都不敢相信。
“你这样做为了什么?”我脑子里很乱,不知道该问什么好。
“我?”田甜终于笑不出来,“封严,你该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