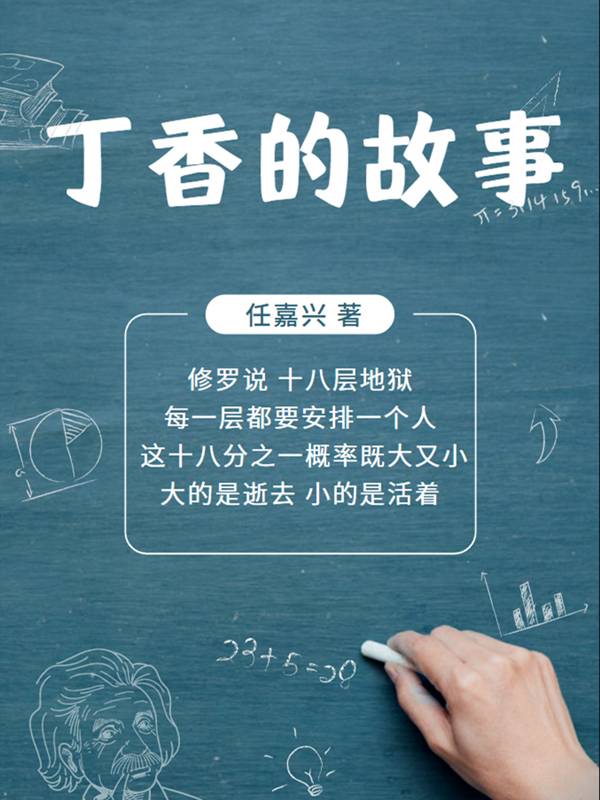“神明永远在注视着你。”
这是一句帝都流传了很久的谚语,意思大概是劝解人们别做坏事。
但余良一直搞不懂,这个新月坊——帝都西区第三大的青楼,它的房间里贴这种东西的用意所在,神明真的有这么无聊吗。
雨天她的房间还是那样,支着窗户亮着灯,余良熟练地从一楼围墙上借力起跳,乌鸦一般轻巧地落在窗沿上,里面只有一个女人,端着一支纤长的银制烟斗,注意到了余良的到来,她只用她那一双漂亮的丹凤眼斜了他一眼,似乎是早已习惯了余良的登场方式。
“您怎么来了,让我猜猜你有什么理由,”她起身轻轻插上门销,“雨太大了没带伞,还是没钱交房租了?”
余良不好意思地笑着,顺手拿起女人的毛巾擦起头发,“回我那窝太远了,我寻思着上你这凑合一晚得了。”
“毛巾放下,你去床底,我还有客人要接呢。”
“又没钱了?我这还有点,你要是急用就先用着,别干那勾当了,”余良叹了口气,把钱夹在女人藏钱的书中,“太困了,直接熄灯睡吧。”
“直接睡觉?”女人眯起眼笑,“那你的钱可给的有点多了。”
“那你退给我。”
“还是睡吧。”女人吹灭了灯,轻轻躺在余良身边,“难得收到烛龙卫大将军的钱。”
“到朝廷里还混得下去吗?”
“混的还行吧。”
“那想必是不怎么样了吧。”女人拖了一个长长的尾音,“我记得之前你是和楚信平级的吧,几年过去了,楚信都当上应龙卫的指挥使了,你怎么还···”
余良把手搁在脸上,只默不作声,他突然有些理解那些下了班也不回家躲在城墙根下抽烟的中年官员了。
“你现在多大了?十九了吧。“女人思考了一会接着说,”去找个老婆吧,你这人看着除了死气沉沉之外也没什么大缺点。”
“苏月你找不到话题就好好睡觉,也才二十出头怎么话比大妈还多了。”余良打断她道,“还有,你先把烟戒了,别连大妈的岁数都活不到。”
“那你也答应我一个要求好不好。”女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余良心里突然萌生不安。
“你说。”
“以后别来了,也不用给我带钱了。”
雨越下越大了,一层油纸做的窗户挡不住外面连绵的雨声,在雨声中整个世界好像都在沉睡。
“苏月你又怎么了?”
“早就想和你谈谈这件事了。”
“现在这样不好吗?你不用接客,不用再喝酒喝到吐血,不用每十天半个月就要检查一次身体。”余良坐起身来托起女人,几乎是脸贴着脸问,“你告诉我到底又是哪里不如意了。”
“你爱我吗?”
“什么玩意儿?”
“你敢说你爱我吗?”女人眼里好像泛着泪光,余良第一次见她这样,也不由得慌了神。
以前她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好像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余良哑了,十几岁的年级就在西部上军校,打仗的几年甚至没见到过三个以上的女孩同时出现的场景,甚至到了十八九岁的年级连女孩手都没牵过。
懂女人可比会打仗难多了。
“你只是习惯了我的存在,可我要的不是这个。”
“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不就行了?”
“我要的你给不了我。”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余良几近气急败坏,对整个局势急转直下的无法控制让他无比焦虑,“你就是在无理取闹!”
“别吼我。”女人别过脸去。
余良突然噤了声,轻轻放下她转而像潜行的猎豹一般摸到门边。
女人不屑,“你又装神弄鬼什么,不想和我说话就别来可以吗?”
门销轻响,门外同时传来磕碰声,下一秒大门洞开余良箭一般射出将门外那人扑倒在地,银光闪烁,一柄精致的折刀架在了那人的脖颈上。
“你是谁?”
“陈十七!我是烛龙卫第三课的陈十七!江帆手下的人!”陈十七一边尽力地偏着头躲避着锋芒一边慌张的叫喊,他知道余良手上有多少人的血。
“声音小点,来干什么的。”余良握刀的手渐渐用力,“刚刚手里的符阵是紧急呼叫阵,发给谁了?”
陈十七的喉结跳动着,冷汗从额头滚落。
“江帆,发给江帆了,烛龙卫接到命令说要逮捕你。”
“哪一课来了?”
“全···全部都来了,还有应龙卫和中央军的一部分人。”
余良眯起了眼,这个阵容不是十恶不赦是不至于被放出来用的,“那你们的总指挥官是谁?”
“烛龙卫指挥使边野。”
“知道为什么抓我吗?”
“上面没通知。”陈十七连眼睛都不敢眨,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余良突然笑了,骂道,“以前我手底下怎么有你这种玩意儿。”
解下手腕上的铁索,余良熟练地将他反绑,嘴里塞上毛巾。不理会一边呜咽一边学毛毛虫一样扭动的陈十七,他转身回房,苏月坐在床边倚床栏看着他。
“你要走了?”
“是的,”余良走到女人身边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而后俯身从床底抽出一个落了灰的铁皮箱,“可能是做了点错事,虽说逃出去有点难,但我还是想先跑着意思意思。”
“所以就是,要说再见的意思了呗。”
“嗯,那我交代后事了,认真听,”余良用手抹去浮尘,露出箱子原本的面目,“和这箱子没关系,我在鱼嘴巷三号的房子里留了一笔钱给你,还有去江南的路籍和驿牌,都是应龙卫指挥使楚信签的名,只要他没出事就能用,记住了吗,记住了就重复一遍给我听。”
“鱼嘴巷三号,钱和牌,”女人概括道,“你的意思是不用我等你了是吗?”
她好像还在赌气。
“对,钥匙后面会有人送给你,除了这些东西,所有有关于我的事情你都可以和烛龙卫的人交代。”
铁皮箱被余良小心翼翼地打开,蓝色的光芒从缝隙中涌出,完全打开后更是照亮了整个房间。
管制级别的高纯度灵石被整齐的码在一起,这个数量如果被误触激活基本可以保证夷平包括这里在内的连续三个街区。
“这发光的是什么?”
“用来照明的杂灵石。”余良敷衍,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了。
拉开相连的夹层抽出两把长刀,一把横刀用来破甲,一把倭刀用来斩人。
打开下一层,五个符具安静的等待着,余良扫视着其上凌厉的线条的样子像是遇见了老友,缓冲模块,充能模块,冲击模块·······
他耐心且安静地将他们一个个激活。
“被关一辈子就被关一辈子吧,比死了好。”苏月突然开口,她好像对这件事不是全无心理准备。
“好。”
余良把最后一个符具卡在自己身上后一步步走到窗边,推开窗,外面是一片茫茫雾雨。
“还真是个逃亡的好天气。”
一阵斜雨吹进,下一秒余良已不见踪影。
%
%
临时指挥部设在北鼓楼,巨大的作战地图铺在狭小的指挥室里,显得很是局促。
而站在地图旁的男人好像更加局促。
边野,时年五十二岁,现任烛龙卫指挥使,也就是余良原来的老上级。
烛龙卫的框架是余良建的,训练是余良抓的,除了每个位置上的人是他边野安排的之外他几乎没做过什么贡献,他原本的计划是隐退后把烛龙卫交给真正创造他的人。
可世事难料,真的难料,接班人可能今天就要进大牢了。
而他,十几年没看过兵书,也吃不透年轻一辈的指挥方式,混迹官场的经验在这完全用不上,自然而然萌生出无力感。
“大人,新情报。”
“念。”
“第四课的一名探员在鱼尾巷新月坊发出遇敌信号后失联。”
“方圆三里内有多少我们的人?”
“一台航空符甲和六名巡警。”
“半小时内能在那集合多少人。”
“三十台符甲二十名巡警。”
“所有机动部队向那里靠拢,方圆十里内应急组全员集合。”
“收到。”
边野捏了捏鼻梁,说实话他真的希望余良从此销声匿迹从此不再出现,有惜才的意思,也有畏惧的意思。
副官靠近耳语道,“对一个双二阶的这么谨慎是不是···”
“下次说话先过脑子,”边野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想一想能在西线战场活七年是什么概念。”
“卑职明白了。”
副官颔首后转身离去,“半小时后围捕开始,祝您好运。”
他在走廊朝衣领下的传声符阵低语,语气毕恭毕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