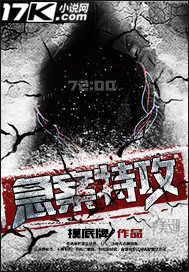许文斌一来就问钟俊堃昨天夜里怎么了。那种怪怪的眼神令他颇为不快。好像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或者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有那么严重么?为什么不想想,那个时候给他打电话,是出于对他的亲近和信任呢?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会给他打电话么?
钟俊堃觉得许文斌辜负了自己。
所以,有些人是可以依靠的,有些人是可以远离的。
钟俊堃寻思那或许真的只是一种幻觉,一个梦境,到现在连自己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说出来谅也没有什么意思,没准儿许文斌还得对他冷嘲热讽一阵,就支吾着搪塞过去了。
他试图找到昨夜那种感觉。
外面的风还在呼啸,但是白天和晚上的似乎很不一样,既不凶猛也不强劲,浪拍船舷的声音也没有昨夜那么夸张。从这方面来找感觉,这就跟昨夜有点挂不上钩。许文斌的眼神有点不怀好意,甚至包含着一点幸灾乐祸,而又不明说,就那么一分一秒地跟你较劲。与这样的人同处一室无聊透顶。还不如让雷荭来呢。
尽管如此,钟俊堃此时全无了走出房间的欲望。
他开始努力使自己的脑子离开昨夜那点事儿,想点别的什么。可是不行,思维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是要往那个方向想,昨夜的景象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
许文斌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又开始上网了。躺在隔间床上的钟俊堃的耳朵里充斥着他断断续续的打字声。这种声音必定有一种催眠的作用,钟俊堃的注意力不知不觉被这种声音完全吸引,听了一阵子,便呼呼睡了过去。
让他难以理解的是,他分明是睡着了的,意识却依然清醒着;而且,仿佛昨夜的梦境再次浮现出来,让他看到了一些几乎不可能的景象。
他开始高度兴奋起来。
琥珀号在大风中颠簸,由下而上的巨浪足有五六米高,一波又一波地撕咬着琥珀号,情景异常恐怖。这恐怖又好像是某种劫难的延续。琥珀号自从进入大洋以后,似乎就没有真正惬意过,总让人感到有一种沉闷的气氛萦绕其上,谁若是胆敢出来就会沾染上这种气氛,所以人们有意无意地把活动范围限定在自己的房间里,很少互相来往,好像彼此是陌生的乘客一样。到了晚上气氛就更加沉闷。
如果不是客轮上的桅灯频繁闪烁,整个客轮看上去酷似一只没有生命的巨大浮箱。现在大部分房间的灯光都熄灭了,只有少量的房间窗户上还透出朦朦胧胧的光亮。相比之下,太平洋上汹涌的波涛反而显得更明亮一些,放眼看,全是一幅幅此起彼伏、跳跃不息的水帘,这些水帘在夜幕下释放出断断续续的、蓝幽幽的光芒。
他走出自己房间的时候,脚步多少有些踉跄。好奇心驱使着他,天气再恶劣也不能让他退缩。他相信自己的感觉没有错,刚刚的确有一个影子从面前闪过,虽然在黑暗中看不分明,但那影子是运动着的,影子挡住了它后面透进来的微弱的光亮,因此使它看上去更暗一些,也更有质感,只是它转眼又不见了。他猜想这不会是幻觉,稍稍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出来看个究竟。
充满了海腥味的凉爽在瞬间帮他提足了神。他伸出手抓住一人多高的栏杆,然后让身体斜靠在上面,如此便可站得稳一些。这时他看见前面果然出现了人影,不是一个,是两个,两个人影轻捷如燕,正朝船头的方向急奔。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迅速腾出一只手来揉了揉眼睛,想弄清楚是否看花了眼,结果断定确实有两个人在前面奔跑。他不假思索地跟了过去,他想跑得快一些,无奈他无论如何也跑不快,等他跌跌撞撞到达船头时,发现阒无一人。
抬头向舷梯那边看了看,也是空空如也。如果有什么人要朝这个位置跑,应该不会再折回去绕着整个二层转圈,极有可能登上舷梯上了三层。他拔腿沿着舷梯拾级往上爬,刚爬了两三级台阶耳朵里面已灌满了巨大的声响,风声涛声被放大了一样,这些声响回旋在耳朵里,震得耳膜又痒又痛。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他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啪啪、啪啪”,许文斌的打字声重新将他拖离了梦境。他拍拍自己的后脑勺,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不禁暗自高兴。现在越来越对自己的感觉有信心了。那么,脑海里的那些景象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个人好端端的,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被植入这些东西。那些景象应该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只是,假如自己昨天夜里从房间只身来到舷梯附近,那么为何醒来后人却在自己的房间里呢?
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呀。
这应该是什么环节出了差错,才使他如此狼狈。
再清楚不过,他一定是把某个关键的细节给遗漏了。
他用手捂住耳朵,紧闭双目冥思苦想,拼命把注意力集中在舷梯那个位置。
“喂,大学毕业生,你不好好睡你的觉,这又是在搞什么名堂啊?”许文斌察觉到隔间的异常,走过来问。
“早不过来迟不过来。”钟俊堃生气地嘟囔,“真烦死人了,我正在搜索一个细节,我觉得差不多就要大功告成了,这下全被你给搅了。”
“噢?”许文斌乐坏了,“你该不至于说自己正在证明相对论吧,我的大学生朋友?”
“瞎扯!”钟俊堃不耐烦地说,“别总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我又不是小孩子。说正经的,你还记得昨天夜里我给你打过一通电话吧?”
“嘿,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正等着你向我道歉呢!”许文斌耸耸肩。
“你少来这一套。”钟俊堃说,“你仔细想想,我昨夜已经给你道歉过了,我才不会为同一件事情道歉两回呢。”
“好吧,就算你道歉过了。”许文斌说,“那你告诉我,又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么,是不是感到身体不舒服了?”
“怎么说呢,”钟俊堃说迟疑道,“反正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算了,还不如不说。”
“我就知道你神经兮兮的。一会儿就叫安代再来给你打一针,免得你老是这么一惊一乍的。”许文斌说。